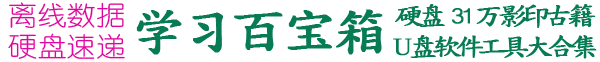在线文库
| 帝紀一 ◄ | 東觀漢記 卷二 帝紀二 |
► 帝紀三 |
|
|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1]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2]建武四年五月甲申,[3]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4]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5]年十歲通《春秋》,[6]上循其頭曰「吳季子」。[7]陽對曰:[8]「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9]三歲進爵為王。[10]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11]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12]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為宜承先序。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13]立陰貴人為皇后,以上為皇太子,[14]治尚書,[15]備師法,兼通四經,[16]略舉大義,博觀群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17]中元二年二月,[18]世祖崩,皇太子即位。[19]帝即祚。[20]長思遠慕,至踰年,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原陵,[21]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22]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長水校尉樊鯈奏言,[23]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子慶為鮦陽侯,[24]子博隱強侯,[25]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永平二年正月,[26]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登靈臺。[27]三月,[28]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29]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30]「十月元日,[31]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32]安車輭輪,朕親袒割牲,祝哽在前,祝噎在後。[33]三老常山李躬,[34]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五更沛國桓榮,[35]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甲子,上幸長安,[36]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37]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38]「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容儀,類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帝令上殿,[39]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上曰:「屬者所言我堯,削章不如飽飯。」十一月,[40]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百里內者,悉令侍祠。[41]永平三年詔曰:[42]「登靈臺,正儀度。」春二月,[43]圖二十八將於雲臺,[44]冊曰:「部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45]詔曰:「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予樂,[46]正樂官曰太予樂官,以應圖讖。十月,[47]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48]不用輦。[49]甲夜讀眾書,[50]乙夜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四年,[51]詔書曰:「朕親耕於藉田,[52]以祈農事。」五年十月,上幸鄴,趙王栩會鄴,[53]賜錢百萬。六年,[54]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納於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55]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56]以備器用。」七年,[57]公卿以芝生前殿,奉觴上壽。八年十月,[58]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赦令,[59]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60]九年,詔為四姓小侯置學。[61]十年閨月,[62]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63]復祠於舊宅。[64]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65]奏鹿鳴,[66]上自御塤箎和之,[67]以娛嘉賓。[68]至南頓,[69]勞饗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被野。[70]十二年,[71]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眾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十三年二月,上耕藉田畢,[72]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有司奏楚王英聚姦猾。[73]十四年,[74]帝作壽陵,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出外為小廚,財足祠祀。明帝自制石槨,[75]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十五年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於下邳。[76]三月,幸孔子宅,[77]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78]御講堂,[79]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80]上憐廣陵侯兄弟,[81]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82]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83]芝生前殿,[84]神雀五色,翔集京師。[85]是夜,上夢見先帝、太后,[86]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87]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會,太常丞上言陵樹華有甘露,上令百官採甘露。受賜畢,罷,上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88]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89]下危臣子,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90]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91]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92]什減三四,[93]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謙儉如此。[94]八月,[95]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96]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日而祠,祫祭於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97]即位,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98]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99](《御覽》卷九一)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炟,[100]孝明皇帝太子也。[101]永平三年二月,[102]以皇子立為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103]多識世事,動容進止,[104]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105]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106]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107]無所不觀。於是上敬重之,[108]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膝下。[109]永平十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即位。(《御覽》卷九一)
詔曰:[110]「行太尉事趙憙,[111]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為太尉。」[112](《書鈔》卷五二)
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也。[113](《御覽》卷八一九)
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114](《初學記》卷二一)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115](《御覽》卷八九〇)
章帝行幸,[116]敕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歷樹木,[117]今方春月,[118]無得有所伐,[119]輅車可引避也。(《御覽》卷一九)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120]至於岱宗,柴望畢,[121]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東過於宮,翱翔而上。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122]祀五帝於汶上明堂,[123]耕於定陶。[124](《稽瑞》、《初學記》卷一三、《御覽》卷九一六、范曄《後漢書》卷三〈章帝紀〉李賢注)
祠禮畢,命儒者論難。[125](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中劉昭注)
章帝東巡狩,祠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御覽》卷四八八)
章帝元和二年,鳳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鷰、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126](《類聚》卷九八)
鳳凰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127](范曄《後漢書》卷三〈章帝紀〉李賢注)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五月戊申,詔曰:[128]「乃者白烏、神雀、甘露屢臻,[129]降自京師。」[130]又有赤烏、白燕。(《永樂大典》卷二三四五)
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131](《玉海》卷一九八)
章帝章和元年,嘉穀孳生。[132](《稽瑞》)
章和中,有華平生也。[133](《稽瑞》)
章帝時,白狐見,群臣上壽。(《稽瑞》)
章帝時,[134]美陽得銅酒樽,采色青黃,有古文。(《御覽》卷七六一)
章帝賜尚書劍各一,[135]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136]郅壽蜀漢文,[137]陳寵濟南鍛成。[138]一室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文劍。[139]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初學記》卷一一)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鬥,上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命欲相殺於殿下,不避門內,畏懦恣縱,始不逐捕,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致也。」[140](《御覽》卷二四一)
章帝時,嘉禾嘉麥,日月不絕。(《御覽》卷八七三)
章和元年詔:「芝草之類,歲月不絕。」[141](《合璧事類》卷一九)
序曰:[142]孝乎惟孝,友于兄弟,[143]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144]寅畏皇天,[145]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146]密靜天下,[147]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御覽》卷九一)
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148]章帝之中子也。[149]母曰梁貴人,早薨。上自岐嶷,[150]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151]孝章由是深珍之,[152]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153]好古樂道,[154]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永元元年,[155]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也。二年二月壬午,[156]日有食之,史官不覺,涿郡言之。三年春正月,[157]帝加元服。[158]時太后詔袁安為賓,[159]賜束帛、乘馬。詔曰:[160]「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誼。[161]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162]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163]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祠,[164]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165]以彰厥功。」[166]四年春正月,[167]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六月,[168]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169]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瑝,[170]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171]恣得收捕,[172]不收其稅。六月,[173]郡國大雨雹,大如鴈子。六年六月,和帝初令伏閉晝日。[174]七月,[175]京師旱。幸洛陽寺,[176]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177]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擅國重譯奉貢。[178]改殯梁皇后於承光宮,[179]儀比敬園。[180]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十年五月丁巳,[181]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十一年,[182]復置右校尉官,置在西河鵠澤縣。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183]秭歸山高四百餘丈,[184]崩填谿水,厭殺百餘人。[185]十一月癸酉夜,[186]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十日。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十三年春正月上日,[187]上以五經義異,[188]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189]十六年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坯山。[190]元興元年五月,右扶風雍地裂。[191]朝無寵族,[192]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193]外憂庶績,內勤經藝,[194]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195]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方國協和,[196]貞符瑞應,[197]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記。元興元年十二月,[198]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御覽》卷九一)
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199]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讌,[200]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玄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201](《御覽》卷九一)
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諱隆,[202]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於民。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殤帝時生百餘日,乃立以為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鄧氏為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殤帝詔省荏弱平簟。[203]延平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御覽》卷九一)
孝殤襁褓承統,[204]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205]賴皇太后臨朝,[206]孔子稱「有婦人焉」,[207]信哉!(《御覽》卷九一)
| ↑返回頂部 |
- ↑ 「孝明皇帝」,事詳范曄《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袁宏《後漢紀》卷九、卷一〇。汪文臺輯薛瑩《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卷一、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華嶠《後漢書》卷一亦略載其事。《類聚》卷一二引袁山松《後漢書》云:「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四庫全書》考證云:「明帝本名陽,建武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始改名莊。范書《明帝紀》直作諱莊,蓋舉後以概前,觀光武建武十九年詔書可見。」
- ↑ 「世祖之中子也」,《初學記》卷一七、《御覽》卷四一一引云:「明帝,光武第四子。」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
- ↑ 「建武四年五月甲申」,此句至「師傅無以易其辭」諸句原無,《御覽》卷九一引,今據增補。
- ↑ 「顏」,《類聚》卷一二引同,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作「項」。
- ↑ 「以」,《御覽》卷九一引作「曰」,《類聚》卷一二引作「以」,今據改。
- ↑ 「年十歲通《春秋》」,原誤作「至十三年通《春秋》」。《類聚》卷一二引作「年十三通《春秋》」,「三」乃「歲」之訛。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十歲能通《春秋》。」可證。
- ↑ 「循」,撫摩。《漢書·李陵傳》云:「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顏師古注云:「循謂摩順也。」「頭」,《類聚》卷一二引作「頸」。「季子」,即季札。
- ↑ 「陽對曰」,《四庫全書》考證云:「按東觀為本朝之史,不應稱帝名,當屬後人所加。」
- ↑ 「年」,此字原無,《類聚》卷一二引有,今據增補。
- ↑ 「三歲進爵為王」,原無「進」字,《類聚》卷一二引有,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 ↑ 「容貌壯麗」,《書鈔》卷一引此一句。
- ↑ 「親密九族」,《書鈔》卷六引此一句。
- ↑ 「詔廢郭皇后」,原無「詔」字,《類聚》卷一二引有,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七年載:「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 ↑ 「以上為皇太子」,此句《類聚》卷一二引作「上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九年載:「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 ↑ 「治尚書」,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桓榮傳》云:「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
- ↑ 「四」,原作「九」,聚珍本同。《書鈔》卷一二、《類聚》卷一二、《唐類函》卷二五引作「四」,今據改。
- ↑ 「無所不照」,此句以上一段文字,聚珍本據各書所引連綴為「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於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為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為皇后。帝進爵為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略覽群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其中「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至「具知姦狀」一段文字,係綜合《類聚》卷一六,《御覽》卷一九五、卷六〇六所引輯錄。據范曄《後漢書·劉隆傳》,此段文字當出《東觀漢記·劉隆傳》,今從《顯宗孝明皇帝紀》中刪去,移入《劉隆傳》。
- ↑ 「中元二年二月」,「元」字原誤作「平」,聚珍本尚不誤,今據改正。「年」字下聚珍本有「春」字。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世祖光武帝卒於中元二年春二月戊戌。
- ↑ 「皇太子即位」,「皇」字下原有「后」字,顯係衍文,今刪去。
- ↑ 「帝即祚」,此句至「莫能仰視」,諸句原無,《御覽》卷四一一引,今據增補。原無「帝」字,據文義補入。《初學記》卷一七引云:「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朝率百官上陵,上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字句稍略。
- ↑ 「上謁原陵」,《通鑑》卷四四云:「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原陵」,光武帝葬此。
- ↑ 「其日降甘露」,《書鈔》卷六引「甘露降」一句,即出於此。
- ↑ 「長水校尉樊儵奏言」,此句至「講議五經同異」諸句原無,聚珍本有,不知輯自何書,今據增補。《書鈔》卷一二僅引「會儒白虎觀」一句,《唐類函》卷二五引同。
- ↑ 「明帝封太后弟陰興子慶為鮦陽侯」,此句至「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諸句原無,聚珍本有,《類聚》卷五一亦引,今據增補。原脫「子慶」二字,范曄《後漢書·陰興傳》云:「永平元年詔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濦強侯。』」袁宏《後漢紀》卷九云:「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為鮦陽侯,博為隱強侯,楚王舅子許昌為龍舒侯。」今據校補。
- ↑ 「博」,原誤作「傅」,今據范曄《後漢書·陰興傳》、袁宏《後漢紀》卷九校正。
- ↑ 「永平二年正月」,此句至「登靈臺」諸句原無,《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臺。」又引云:「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武皇帝於明堂,禮畢,升靈臺。」「三年」乃「二年」之訛。又引云:「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此段文字即據以上各處所引增補。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袁宏《後漢紀》卷九云: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禮畢,登靈臺,觀雲物,大赦天下」。
- ↑ 「登靈臺」,據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遂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云云。《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即係括引詔文大意。此二句不便連綴於本書《明帝紀》中,姑置於注中。「五帝」,范書《明帝紀》李賢注引《五經通義》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炬,黑帝協光紀。」
- ↑ 「三月」,此句原作「永平二年二月」。「永平二年」四字,為避免與上文重出,今刪去。「二月」乃「三月」之訛,《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有一處引作「三月」,卷三張衡〈東京賦〉李善注亦引作「三月」,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載:「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通鑑》卷四四同,今據改正。
- ↑ 「大」,此字原脫,《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兩引皆有「大」字,又卷三張衡〈東京賦〉李善注引亦有「大」字,今據增補。
- ↑ 「詔曰」,此二字原無,據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下文「元日」云云為明帝詔文,此當有「詔曰」二字。聚珍本已補入,今從之。
- ↑ 「十月元日」,此句至「祝噎在後」諸句原無。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於明帝詔「令月元日」句下引《東觀漢記》注云:「十月元日。」《書鈔》卷六七引云:「永平二年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祝哽在前,祝咽在後。」又引云:「明帝永平二年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又引云:「永平二年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李善注引云:「永明二年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永明」乃「永平」之訛。此段文字即綜合以上諸書所引增補。
- ↑ 「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云:「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鄭玄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漢書·禮樂志》云:「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 ↑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云:「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載養三老、五更之儀云:「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自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
- ↑ 「三老常山李躬」,此下三句原無,《書鈔》卷六七引《東觀漢記》云:「《明帝紀》云:『永平二年詔曰:「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又《唐類函》卷四九引云:「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此下三句即據二書所引增補。聚珍本有《李躬傳》,輯入「三老常山李躬」云云三句。《書鈔》卷六七已明言此為《明帝紀》語,聚珍本不編於《明帝紀》,而置於《李躬傳》,失之。
- ↑ 「五更沛國桓榮」,此下四句原無,《書鈔》卷六七引云:「明帝永平二年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今據增補。本書《桓榮傳》亦載此詔,文字大同小異。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載:「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是此所輯詔語多所脫佚。
- ↑ 「甲子,上幸長安」,《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與此略有不同。卷三張衡〈東京賦〉李善注引云:「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永明」乃「永平」之訛。
- ↑ 「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此句《御覽》卷四六七引作「歷覽宮館舊處」。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十月載:「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 ↑ 「有縣三老大言」,此句惠棟《後漢書·明帝紀》補注卷二引作「時有縣三老上章云」。此句至「臣七驩喜」諸句原無,《御覽》卷四六七引,今據增補。聚珍本亦輯錄此段文字,字句全同。
- ↑ 「帝令上殿」,此句至「削章不如飽飯」諸句原無。《書鈔》卷一二九引云:「明帝時,至長安,有縣三老上章云:『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又卷一四四引云:「顯宗西巡,三老懷章大言。上曰:『屬者所言我堯,削章不如飽飯。』」今據二處所引增補。
- ↑ 「十一月」,此句至「悉令侍祠」諸句原無,《類聚》卷三八引,今據增補。此段文字《御覽》卷五二六亦引,字句微異。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
- ↑ 「祠」,《御覽》卷五二六引同,聚珍本作「祀」。
- ↑ 「永平三年詔曰」,「三年」原誤作「二年」,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云云。是此詔在永平三年,今據改正。聚珍本把此詔輯入永平二年,不可信。
- ↑ 「春二月」,此句至「或以德顯」諸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文選》卷四〇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李善注引云:「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疑聚珍本即據此輯錄,又依文意略有增補。
- ↑ 「圖二十八將於雲臺」,《通鑑》卷四四明帝永平三年二月載:「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肜、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胡三省注云:「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祜、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肜、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此序其次,不與前史合。」
- ↑ 「秋八月」,此句至「以應圖讖」諸句原無。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載:「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為大予樂。」李賢注云:「尚書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琁機鈐改之。」《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東觀漢記》云:「孝明詔曰:『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子樂,正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讖。」「雅」字乃「予」字之訛,「太子樂」乃「太予樂」之訛,「太子樂官」乃「太子樂官」之訛。今據《文選》李善注所引輯補,又參酌范書《明帝紀》增補「秋八月」三字。《文選》卷四六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云:「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字句較略。此段文字聚珍本輯作「秋八月,詔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所輯字句多有改易。
- ↑ 「郊廟樂曰太予樂」,《通鑑》卷四四胡三省注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
- ↑ 「十月」,此句上原有「三年」二字,與上復出,今刪去。
- ↑ 「步行觀部署」,「行觀」二字原誤倒,姚本、聚珍本作「行觀」,又《書鈔》卷一四〇引云:「明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亦作「行觀」,今據改正。《書鈔》卷一六引云:「歷覽宮觀,步觀部署。」與此有異。
- ↑ 「不用輦」,此句下聚珍本尚有「車」字。《御覽》卷四三一引云:「明帝行部署,不用輦晝,甲夜乃解,偃讀眾書,乙夜盡寢,先五鼓起,率常如此。」「晝」乃「車」之訛。
- ↑ 「甲夜讀眾書」,「讀」字,晏元《獻公類要》卷九引作「觀」。《書鈔》卷一二引「甲夜讀書」一句。
- ↑ 「四年」,此句至「以祈農事」諸句原無,《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李善注引,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群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此所引刪削頗多。
- ↑ 「藉田」,范書《明帝紀》李賢注引《五經要義》云:「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
- ↑ 「趙王栩會鄴」,此句原誤作「徽趙王會鄴」。聚珍本不誤,今據改正。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五年「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此句下聚珍本有「常山」二字,係衍文。
- ↑ 「六年」,此句至「以備器用」諸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僅引「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三句,又引「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四句。「初祭」乃「礿祭」之訛。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六年載:「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 ↑ 「易鼎足象三公」,《通鑑》卷四五胡三省注:「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按《易·鼎卦九四爻》辭云:「鼎折足,覆公餗。」又《繫辭下》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即括引易文大意,非出易緯。
- ↑ 「礿祭」,《爾雅·釋天》云:「夏祭曰礿。」
- ↑ 「七年」,此句至「奉觴上壽」三句原無,《御覽》卷九八五引,今據增補。
- ↑ 「八年十月」,袁宏《後漢記》卷一〇云「八年冬十一月」,月份有誤。
- ↑ 「赦」,聚珍本作「詔」。
- ↑ 「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持」字原誤作「待」,聚珍本不誤,今據改正。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載:「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悉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 ↑ 「九年,詔為四姓小侯置學」,此二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六一三亦引,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載:「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張酺傳》載:「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通鑑》卷四五明帝永平九年載:「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以非列侯,故稱「小侯」。《東漢會要》卷一八「小侯」條注云:「顏氏家訓謂以小年獲封,故曰『小侯』。」可備一說。
- ↑ 「十年閏月」,此年閏四月。聚珍本作「十年夏閏四月」。
- ↑ 「以日北至」,原無「北」字,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日北至。」今據增補「北」字。范書《明帝紀》李賢注云:「北至,夏至也。」
- ↑ 「祠」,《水經注》卷二八引作「祀」。
- ↑ 「弟子」,聚珍本作「子弟」,《御覽》卷五八〇引同。
- ↑ 「鹿鳴」,《詩·小雅》中的一篇,為宴群臣嘉賓之作。《毛詩·鹿鳴》序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 ↑ 「上自御塤箎和之」,明帝幸南陽,自御塤箎事,《書鈔》卷一二、卷一六、卷八二,《御覽》卷五八〇亦引,又《書鈔》卷一一一兩引,字句或詳或略。「塤」,《風俗通義·聲音篇》云:「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箎。』塤,燒土為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箎」,《風俗通義·聲音篇》云:「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箎。』」
- ↑ 「嘉賓」,《水經注》卷二八引作「賓客」。按「嘉賓」二字義長。
- ↑ 「至南頓」,原誤作「至頃」,聚珍本不誤,今據改正。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年夏四月閏月載:「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 ↑ 「牛被野」,「牛」字下聚珍本有「羊」字。
- ↑ 「十二年」,此句至「置永昌郡」諸句原無,《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今據增補。「十二年」三字李善注引原無,係據聚珍本補入。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西南夷傳云:「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
- ↑ 「上耕藉田畢」,此事《書鈔》卷九〇、《類聚》卷三九亦引,字句大同小異。
- ↑ 「有司奏楚王英聚姦猾」,《書鈔》卷七〇引《東觀漢記》云:「明帝紀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英聚姦猾。』」楚王英謀反在永平十三年十一月,敗後,國除,遷於涇縣。「有司奏楚王英聚姦滑」當在永平十三年或以前。因有司上奏具體年月不可確考,姑附置於此。姚本、聚珍本皆未輯此段文字。
- ↑ 「十四年」,此句至「財足祠祀」諸句原無。范曄《後漢書·明帝紀》十四年載:「初作壽陵。」十八年又載:「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李賢注引《東觀漢記》云:「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出外為小廚,財足祠祀。」今據李賢注增補,又參酌范書增入「十四年,帝作壽陵」二句。此段文字姚本輯作「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廚,財足祠祀」。聚珍本與姚本同,惟首句前增入「十四年」三字。
- ↑ 「明帝自制石槨」,此下三句原無,《御覽》卷五五二引,今據增補。聚珍本作「帝自置石槨,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 ↑ 「癸亥,帝耕於下邳」,此二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癸亥,帝耕於下邳。」
- ↑ 「幸孔子宅」,《書鈔》卷一六僅引「祀孔子宅」一句。
- ↑ 「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二弟」二字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明帝紀》云:「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今據增補。
- ↑ 「御講堂」,《書鈔》卷一二僅引此一句。
- ↑ 「幸東平王宮」,「東平王」,謂劉蒼,光武帝子,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范曄《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
- ↑ 「上憐廣陵侯兄弟」,光武帝子劉荊於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明帝時因罪徙封廣陵王,後自殺。永平十四年,封荊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荊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見范曄《後漢書·廣陵思王荊傳》。
- ↑ 「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以」字原誤作「聖」,今據聚珍本校正。范曄《後漢書·廣陵思王荊傳》云:永平十五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
- ↑ 「內附」,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云:「內附謂木連理也。」
- ↑ 「芝生前殿」,《合璧事類》卷一九引云:「明帝永平十七年,芝草生殿前。」
- ↑ 「翔集京師」,此句下聚珍本有「正月,當謁原陵」二句。《通鑑》卷四五明帝十七年載:「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云云。
- ↑ 「上夢見先帝、太后」,《類聚》卷九八引作「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御覽》卷一二引作「明帝永平十七年,夢見先帝、光烈皇后」。
- ↑ 「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書鈔》卷六僅引「真覺不能寐」一句,「真」字又誤,當作「喜」。
- ↑ 「遵奉建武之政」,《書鈔》卷六有「奉建武王之政」句,即出《東觀漢記·明帝紀》。「王」字係衍文。
- ↑ 「上濁明主」,此下二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東漢會要》卷二三引亦有,今據增補。
- ↑ 「勢」,此字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二、《合璧事類》卷二三、范曄《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皆作「榮」。
- ↑ 「嘗案輿地圖」,此句至「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李賢注引亦有,今據增補。范書《明德馬皇后紀》云:永平「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 ↑ 「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原無「小」字,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李賢注引亦有,今據增補。
- ↑ 「什減三四」,《書鈔》卷七〇引《東觀漢記》云:「《明帝紀》云:『十八年,食租且餓。』」疑「食租且餓」句當在此句下。姚本、聚珍本皆未輯錄。
- ↑ 「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謙儉如此」,此二句王先謙《後漢書·明帝紀集解》載惠棟說引《東觀漢記》作「又國遠而小,易於為善,節儉謙約如此」。
- ↑ 「八月」,此為永平十八年八月。
- ↑ 「顯節陵」,《通鑑》卷四五永平十八年胡三省注引《帝王世紀》云:「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 ↑ 「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書鈔》卷一二僅引「垂意經學」一句,即出於此。此句以下一段文字聚珍本繫於永平二年「食邑五千戶」句下。
- ↑ 「正坐自講」,《書鈔》卷一二引「正坐自講,稽合圖讖」二句,即出於此。
- ↑ 「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萬」字原脫,聚珍本有,今據增補。《漢書·儒林傳》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 ↑ 「孝章皇帝」,事詳范曄《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袁宏《後漢紀》卷一一、卷一二。汪文臺輯司馬彪《續漢書》卷一、華嶠《後漢書》卷一、袁山松《後漢書》、薛瑩《後漢書》亦略載其事。
- ↑ 「太子」,聚珍本作「第五子也」。范曄《後漢書·章帝紀》云:「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
- ↑ 「永平三年二月」,聚珍本無「二月」二字。下文「年四歲」移至此句下。
- ↑ 「幼而聰達才敏」,《書鈔》卷七引「幼而聰達」一句。
- ↑ 「止」,原誤作「正」,《書鈔》卷八、《晏元獻公類要》卷九引作「止」,今據改正。
- ↑ 「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文選》卷五七顏延年〈陽給事誄〉李善注僅引「章帝壯而仁明」一句,《書鈔》卷五僅引「溫茲惠和」一句,卷七引此二句,又脫「壯而」二字。
- ↑ 「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書鈔》卷八僅引此二句,文字全同。
- ↑ 「周覽古今」,《書鈔》卷一二僅引此一句,文字全同。
- ↑ 「於是上敬重之」,此句聚珍本作「由是明帝重之」。
- ↑ 「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此二句原無,姚本、聚珍本有,今據增補。《初學記》卷一七引云:「章帝殂,明帝子,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殂」字係衍文。姚本、聚珍本即據此輯錄。
- ↑ 「詔曰」,明帝於永平十八年八月卒,章帝即位,十月即下此詔。
- ↑ 「趙憙」,原作「趙喜」,下同。按字當作「趙憙」,范曄《後漢書·趙憙傳》作「趙憙」,《文選》卷一〇潘岳〈西征賦〉李善注引趙憙他事,字亦作「趙憙」,今據改正。
- ↑ 「其以憙為太尉」,本書《趙憙傳》、范曄《後漢書·趙憙傳》亦載此詔。但此條文字當繫於《章帝紀》,《書鈔》卷五二明言此條文字出「東觀章帝紀」。
- ↑ 「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也」,此條《御覽》卷八一六亦引,卷八一九又一處引徵,字句皆較簡略。范曄《後漢書·章帝紀》李賢注云:「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漢書·貢禹傳》載禹奏言:「故齊時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顏師古注云:「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東漢亦然,故詔齊相止送冰紈等物。
- ↑ 「講五經同異」,此條《御覽》卷六一五亦引,字句稍略。范曄《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四年十一月,下詔命「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通鑑》卷四六建初四年載:「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羡皆與焉。」
- ↑ 「日南獻白雉、白犀」,范曄《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春正月載:「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南蠻傳》載:「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雍。」
- ↑ 「章帝行幸」,《書鈔》卷一三九引無此句,而有「元和三年」一句。「三年」乃「元年」之誤。據范曄《後漢書·章帝紀》,此為元和元年事。
- ↑ 「樹」,《書鈔》卷一三九引作「林」。
- ↑ 「今」,此字原無,《書鈔》卷一三九引有,今據增補。
- ↑ 「無得有所伐」,此句《書鈔》卷一三九引作「毋得斫伐」。
- ↑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此為元和二年二月事。
- ↑ 「柴望畢」,此句姚本作「柴,望秩山川群神」。聚珍本同,惟「神」下有「畢」字。
- ↑ 「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此句下聚珍本有「大赦天下」一句。
- ↑ 「祀五帝於汶上明堂」,《漢書·郊祀志》云: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章帝祀五帝於汶上明堂,仍沿武帝舊制。
- ↑ 「耕於定陶」,《稽瑞》引云:「章帝元和二年巡狩至岱宗,燔柴望祀畢,有黃鵠從西南來壇上,東北過於宮,翱翔而上。」《初學記》卷一三引云:「章帝東巡狩,至于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耕於定陶。」《御覽》卷九一六引云:「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范曄《後漢書·章帝紀》李賢注引云:「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此條即據以上諸書所引輯錄。又《類聚》卷三九、卷九〇,《事類賦》卷一八亦引,字句較略。范曄《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載:「丙辰,東巡狩。己未,鳳凰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
- ↑ 「命儒者論難」,范曄《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載:「三月己丑,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命儒者論難」即在此時。
- ↑ 「不可勝紀」,此條他書引徵較多,皆略於此,而且間有異同。《稽瑞》引云:「章帝元和中,有嘉瓜生。」《類聚》卷九九引云:「章帝時,鳳凰百三十九見。」《御覽》卷九一五引云:「章帝時,鳳凰三十九見。」《類聚》卷九八引云:「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御覽》卷八八九、《事類賦》卷二〇引同。《玉海》卷一九八引云:「麒麟五十二。」《類聚》卷九八引云:「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玉海》卷一九八引同,僅無「章帝」二字。《類聚》卷九九引云:「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卷九九又引云:「章帝元和二年,白兔見。」又引云:「章帝元和二年,白鹿見。」《玉海》卷一九八引同,僅無「章帝」二字。《玉海》卷一九七引云:「章帝元和二年,芝英、華平,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范曄《後漢書·賈逵傳》李賢注引云:「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玉海》卷一三、卷二〇〇引同。《玉海》卷二〇〇引云:「又有青龍、黃鵠、鸞鳥、神馬、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疑此條係彙集符瑞之文而成。
- ↑ 「鳳凰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玉海》卷二〇〇亦引此條,「樹」作「木」。據范曄《後漢書·章帝紀》,此為元和二年事。
- ↑ 「詔曰」,原脫「曰」字,《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今據增補。
- ↑ 「乃者」,此二字原無,今據《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增補。
- ↑ 「降自京師」,此句原無,今據《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增補。范曄《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云云。則此所載章帝詔文刪削頗多。此條《六帖》卷九四、《御覽》卷九二〇、《合璧事類別集》卷七二、《玉海》卷九八亦引,字句稍略。
- ↑ 「白虎見彭城」,此條姚本、聚珍本皆未輯錄。
- ↑ 「孳」,與「滋」字同,蕃也。
- ↑ 「華」,與「花」字同。
- ↑ 「章帝時」,具體年代無考。聚珍本繫於代郡高柳烏生子事後,今從之。《玉海》卷八九引此條,亦云「章帝時」,未言確切年代。
- ↑ 「章帝賜尚書劍各一」,此事不知確切年月,姑繫於此。
- ↑ 「韓稜楚龍泉」,《書鈔》卷一九引「賜龍州」一句,即出此。「泉」字范曄《後漢書·韓稜傳》作「淵」,「州」乃「泉」或「淵」之訛。
- ↑ 「壽」,原誤作「燾」,下同,姚本亦作「燾」。聚珍本作「壽」,《書鈔》卷一二二、《御覽》卷二一二、《萬花谷後集》卷九、《合璧事類後集》卷二六、《翰苑新書》卷一四皆作「壽」,與范曄《後漢書·郅壽傳》合,今據改正。
- ↑ 「鍛成」,《書鈔》卷一二二引作「椎成」。范曄《後漢書·韓稜傳》云:稜「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持以寶劍,自手書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李賢注云:「《漢官儀》『椎成』作『鍛成』。」姚本、聚珍本皆作「鍛成」,《御覽》卷二一二、《萬花谷後集》卷九、《合璧事類後集》卷二六、《翰苑新書》卷一四亦皆作「鍛成」。
- ↑ 「文劍」,此二字聚珍本作「漢文劍」,《書鈔》卷一二二引作「漢文」,《御覽》卷二一二引作「蜀漢文劍」。
- ↑ 「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致也」,范曄《後漢書》未載此事,章帝下詔的具體時間無從確考。今參考聚珍本,姑將此條編置於此。
- ↑ 「歲月不絕」,范曄《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載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啟□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則此所引章和元年詔,刪削頗多。
- ↑ 「序曰」,此句下聚珍本有「書曰」二字。
- ↑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論語·為政篇》云:「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作偽古文尚書者把「惟孝,友于兄弟」二句採入君陳篇。
- ↑ 「乾乾夕惕」,《書鈔》卷九引作「朝乾夕惕」。《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
- ↑ 「寅畏皇天」,《尚書·無逸篇》云:「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云云。「寅畏」,敬畏。此序所言即本《尚書·無逸篇》。
- ↑ 「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書鈔》卷五僅引「明德慎罰」一語。《尚書·康誥篇》云:「王若曰:『孟侯,朕之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云云。《左傳》成公三年載申公巫臣言云:「《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此序所言即本《尚書·康誥篇》。
- ↑ 「密靜天下」,《書鈔》卷一五僅引此一句。
- ↑ 「孝和皇帝」,事詳范曄《後漢書》卷四〈孝和帝紀〉,袁宏《後漢紀》卷一三、卷一四。汪文臺輯司馬彪《續漢書》卷一亦略載其事。
- ↑ 「章帝之中子也」,據范曄《後漢書·和帝紀》,和帝為章帝第四子。
- ↑ 「自」,姚本、聚珍本同,《類聚》卷一二引亦同。王先謙《後漢書·和帝紀集解》載惠棟說引作「幼」。「岐嶷」,謂幼年聰慧。《詩·大雅·生民》云:「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毛亨傳云:「岐,知意也。嶷,識也。」鄭玄箋:「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
- ↑ 「篤仁」,此二字《書鈔》卷六引同,姚本、聚珍本作「仁孝」,《類聚》卷一二亦引作「仁孝」。
- ↑ 「孝章」,此二字王先謙《後漢書·和帝紀集解》載惠棟說引同,姚本作「帝」,《類聚》卷一二引亦作「帝」,聚珍本作「章帝」。
- ↑ 「兼覽書傳」,《書鈔》卷一二屢引本書,其中一條僅引此四字。
- ↑ 「樂」,《書鈔》卷一二引作「學」。
- ↑ 「永元元年」,此下三句原無,姚本、聚珍本有,《初學記》卷二四亦引,今據增補。「永元」二字姚本、《初學記》卷二四引皆作「孝和」,聚珍本作「永元」,今從之。按此事不見范曄《後漢書》和袁宏《後漢紀》。范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載:「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事又見袁宏《後漢紀》和本篇下文。疑此所載即永元五年事。
- ↑ 「二年二月壬午」,此下四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二年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李賢引《東觀漢記》注云:「史官不覺,涿郡言之。」今據李賢注,又酌取范書文句增補。此段文字姚本作「和帝二年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聚珍本改「和帝二年二月」為「二年春二月」,餘與姚本同。二本所輯,亦係據李賢注所引,又參酌范書。
- ↑ 「三年春正月」,此句上原有「永元」二字。按上文已出「永元」年號,依修史體例,此不當重出,今刪去。此下二句聚珍本漏輯。
- ↑ 「元服」,《儀禮·士冠禮》云:「令月吉日,加爾元服。」《漢書·昭帝紀》顏師古注云:「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
- ↑ 「時太后詔袁安為賓」,此下二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引,今據增補。此二句又輯入《袁安傳》。
- ↑ 「詔曰」,此句至「以彰厥功」諸句原無,《類聚》卷五一引,今據增補。《類聚》所引,原無「詔曰」二字,聚珍本輯作「三年詔曰」云云,《御覽》卷四七四引云:「和帝永元三年,詔曰」云云,《文選》卷三八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云:「和帝詔曰」云云,今據以上各書增補。姚本把此段文字未輯入《和帝紀》,而編入末卷散條中。
- ↑ 「誼」,姚本、聚珍本同,《御覽》卷四七四引作「義」。按二字古通。
- ↑ 「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王先謙《後漢書·和帝紀集解》引錢大昕云:「顧淞云:『此詔蕭、曹並舉,而獨云曹相國無後嗣,則酇侯有後矣。今據前書功臣表,酇侯九世孫禹,王莽建國元年,更為蕭鄉侯。莽敗絕,而平陽侯十世孫宏,光武建武二年,以舉兵佐軍紹封,傳子曠,表云今見,則孟堅修史時尚存也。此與詔文正相反,未知其審。』予按《韋彪傳》亦云,建初七年,詔求蕭何後,封何末孫熊為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及焉,則曹之有後審矣。而一云建武所封,一云建初所封,其名又互異。且班表、韋傳皆云平陽侯,而此詔稱容城侯,皆事之可疑者也。」
- ↑ 「見二臣之墓」,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引《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又引《廟記》云:「曹參冢在長陵旁道北,近蕭何冢。」「墓」,姚本、聚珍本同,《御覽》卷四七四引亦同,《文選》卷三八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作「隴」。
- ↑ 「遣使者以中牢祠」,此句上《御覽》卷四七四引有「可」字。「祠」,原作「禱」,姚本同。聚珍本作「祠」,《御覽》卷四七四引同,今從改。
- ↑ 「須」,原誤作「頃」,姚本、聚珍本尚不誤,今據改正。「景風紹封」,「景風」,或云南風,《史記》律書云:「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或云東南風,《淮南子·墜形訓》云:「東南曰景風。」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
- ↑ 「以彰厥功」,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三年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與此字句大同小異。
- ↑ 「四年春正月」,此下五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云:永元「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李賢引《東觀漢記》注云:「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此下五句即據李賢注,又參酌范書增補。姚本、聚珍本輯有「單于乞降,賜玉具劍」云云四句,但聚珍本把此段文字誤繫於永元二年下。據范書《匈奴南單于傳》。持節衛護者為任尚。
- ↑ 「六月」,此句上原有「四年」二字,因與上文複出,今刪去。
- ↑ 「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此句下聚珍本有「庚申」二字,與范曄《後漢書·和帝紀》同。
- ↑ 「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瑝」,原無「射聲校尉郭瑝」六字。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六月載:「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李賢注云:「《東觀記》『璜』作『瑝』,音同」是《東觀漢記》載及郭璜,且名作「瑝」字,今據李賢注,又參酌范書增補。
- ↑ 「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六帖》卷三八引云:「詔有司京師果園悉以假貧人。」字句較略。此為永元五年二月事,見范曄《後漢書·和帝紀》、袁宏《後漢紀》卷一三。
- ↑ 「收」,聚珍本脫,范曄《後漢書·和帝紀》作「采」。
- ↑ 「六月」,此下三句原無,《御覽》卷一四引,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載:「六月丁酉,郡國三雨雹。」李賢引《東觀漢記》注云:「大如鴈子。」此段文字姚本作「六月,雨雹,大如鴈子」,係輯自李賢注,又酌取范書文字作了增補。聚珍本則與《御覽》所引同。
- ↑ 「六年六月,和帝初令伏閉晝日」,此二句原無,《史記》封襌書索隱引下句,今據增補。上句則參考范曄《後漢書·和帝紀》補 入 。范書《和帝紀》永元六年載:「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李賢注引《漢官舊儀》云:「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此段文字姚本、聚珍本皆未輯錄。
- ↑ 「七月」,此句至「未還宮而澍雨」諸句原無,《御覽》卷六四二引,今據增補。
- ↑ 「寺」,《初學記》卷二〇引無此字。按當有此字。「寺」謂官舍。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引《風俗通義》云:「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通鑑》卷四三胡三省注引《風俗通義》云:「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華嚴《經音義》卷四引《風俗通義》云:「寺,司也,延之有法度者也。今諸侯所止皆曰寺也。」
- ↑ 「未還宮而澍雨」,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載:「秋七月,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
- ↑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擅國重譯奉貢」,此二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云:永元「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李賢注云:「《東觀記》作『擅』,俗本以『襌』字相類或作『襌』者,誤也。」此二句即據李賢注,又摘取范書字句增補。
- ↑ 「改殯梁皇后於承光宮」,此句至「乃議改葬」諸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九年九月載:「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於西陵。」此下李賢引《東觀漢記》「改殯承光宮」至「乃議改葬」一段文字作注,今據李賢注所引增補。李賢注所引原無「梁皇后於」四字,聚珍本參酌范書增入,今從之。和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死,竇皇后養和帝以為己子。和帝即位,竇皇后為皇太后,控制了朝政。永元九年閏八月皇太后卒,於是和帝始有改葬其生母之舉。
- ↑ 「儀比敬園」,范曄《後漢書·梁貴人紀》云:和帝「以貴人酷歿,歛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李賢注云:「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 ↑ 「十年五月丁巳」,此句至「壞民廬舍」諸句原無,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三劉昭注引,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亦引,字句稍異。此段文字下,聚珍本輯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丕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此當出《魯丕傳》,今移入《丕傳》。姚本亦把此段文字輯入《和帝紀》。
- ↑ 「十一年」,此下三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四月載:「己巳,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引《東觀漢記》云:「置在西河鵠澤縣。」《玉海》卷一三三、卷一三七亦引此句。此下三句即據李賢注,又酌取范書文句增補。
- ↑ 「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此二句原無,《文選》卷五七潘岳〈馬汧督誄〉李善注引下句,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載:「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郡兵討破之。」又《南蠻傳》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十二年」一句則據范書增補。聚珍本有此二句。
- ↑ 「秭歸山高四百餘丈」,此下三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引,今據增補。據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四亦云:永元「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
- ↑ 「厭」,讀作「壓」。
- ↑ 「十一月癸酉夜」,此句至「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諸句原無,《御覽》卷一五引,今據增補。首句《御覽》卷一五原引作「和帝永和十二年癸酉夜」,「永和」乃「永元」之誤。今刪「和帝永和十二年」七字,又據《御覽》卷八七二所引增補「十一月」三字。
- ↑ 「十三年」,原誤作「十二年」,聚珍本作「十三年」,與范曄《後漢書·和帝紀》相合,今據改正。「上日」,朔日也。《尚書·堯典》云:「正月上日,受終於
- ↑ 「上」,此字原無,姚本有,《類聚》卷一二引亦有,今據增補。聚珍本作「帝」。
- ↑ 「覽書林,閱篇籍」,《書鈔》卷一二僅引此二句,文字全同。
- ↑ 「十六年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坯山」,此三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載:「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李賢注云:「《東觀記》作『坯』,並音平眉反,流俗本或作『杯』者,誤也。」可見《東觀漢記》載和帝至緱氏縣,登境內百坯山事。今據李賢注,又酌取范書文句增補此三句。
- ↑ 「元興元年五月,右扶風雍地裂」,此二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載:「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云:「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今據李賢注,又參酌范書增補。
- ↑ 「朝無寵族」,《書鈔》卷一五僅引此一句,「族」作「幸」。《御覽》卷九一所引此句與上文「閱篇籍」句相銜接,文義不相連屬,此句上有闕佚。
- ↑ 「篤」,聚珍本作「悅」。按「篤」字是。
- ↑ 「內勤經藝」,書鈔卷一二僅引此一句。
- ↑ 「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書鈔》卷一二僅引「左右誦書」一句,係括引大意。
- ↑ 「方」,姚本、聚珍本作「萬」,《類聚》卷一二引同。
- ↑ 「貞符瑞應」,此句姚本、聚珍本作「符瑞」,類聚卷一二引同。按如作「符瑞」,則當與下句連讀。
- ↑ 「元興元年十二月」,此下一段文字聚珍本移置於上文「朝無寵族」句前。
- ↑ 「以奉大業」,《書鈔》卷一七僅引此一句。
- ↑ 「宮無嬪嬙鄭、衛之讌」,此下二句《書鈔》卷八引作「宮無嬪嬙之燕,囿無盤樂之豫」,文有節刪。「鄭、衛」謂春秋戰國時的鄭國和衛國的民間俗樂。因與雅樂不同,故被排斥,視為淫靡之樂。《禮記·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 ↑ 「遠近承風云爾」,此條文字姚本、聚珍本皆未輯錄。
- ↑ 「孝殤皇帝」,事詳范曄《後漢書》卷四〈孝殤帝紀〉、袁宏《後漢紀》卷一五。
- ↑ 「殤帝詔省荏弱平簟」,此句原無,《御覽》卷七〇八引,聚珍本連綴於「延平元年八月」句前,今從之。此詔范曄《後漢書·殤帝紀》失載。「平簟」二字疑有訛誤。
- ↑ 「孝殤襁褓承統」,從文字內容來看,此下諸句是《殤帝紀》序中語。
- ↑ 「敖」,聚珍本作「嗷」。按「敖」乃「嗷」的同音假借字。又作「謷」、「熬」、「嗷」。說文云:「嗷,眾口愁也。」
- ↑ 「臨朝」,此二字聚珍本脫。
- ↑ 「孔子稱『有婦人焉』」,《論語·泰伯篇》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所謂「婦人」,是指文王妃太姒。《列女傳·母儀傳》云:「太姒者,武王之母,……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