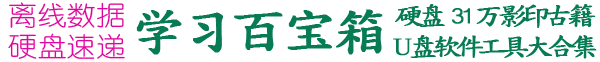在线文库
| 目錄 ◄ | 東觀漢記 卷1 帝紀一 |
► 紀2 |
|
|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1]高祖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2]出自長沙定王發,[3]王生舂陵節侯。[4]舂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考侯以土地下濕,[5]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6](《類聚》卷一二)
皇考初為濟陽令,[7]有武帝行過宮,[8]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9]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畫。[10]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11]「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12]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13]故宮中皆畫鳳凰。[14]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為人隆準,日角,[15]大口,美鬚眉,[16]長七尺三寸。在舂陵時,[17]望氣者言舂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蔥蔥。」仁智明遠,[18]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非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19]年九歲而南頓君卒,[20]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21]資用乏,[22]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23]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聞知,具為同舍解說。高才好學,[24]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闇稽疑議。嘗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25]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稿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福曰:「莊公寧視卿邪?」王莽時,[26]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盜發其廩,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群起,四方潰畔。荊州下江平林兵起,[27]王匡、王鳳為之渠率。時南陽旱餓,[28]而上田獨收。宛大姓李伯玉從弟軼數遣客求上,[29]上欲避之。
先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為醫,[30]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上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上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固始侯兄弟為上言:[31]「天下擾亂饑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為輔。」[32]上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為宗卿師,[33]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上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34]絳衣赤幘。[35]時伯升在舂陵亦已聚會客矣。上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36]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37]有頃不見,異之。[38]遂從南郭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39]將軍服,[40]乃驚曰:「以為獨伯升如此也,中謹厚亦如之。」[41]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鳳、王匡等,因率舂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上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42]光武起義兵,[43]暮聞塚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使劉終詐稱江夏吏,[44]誘殺湖陽尉。五威將軍莊尤擊下江兵,[45]上奉糗一斛,脯三十朐詣幕府營。進圍宛城。[46]
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將軍。[47]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48]二公兵到潁川,[49]莊尤、陳茂與合。[50]尤問城中出者,言上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為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眉目者耶?[51]欲何為乃如此?」初,莽遣二公,[52]欲盛威武,以振山東,甲衝輣,[53]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54]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55]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上邀之於陽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上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上乃笑,且去,唯王常是上計。會候騎還,言大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上,上到,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上,及迫急,上為畫成敗,[56]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57]留王鳳令守城,[58]夜出城南門。二公兵已五六萬到,[59]遂環昆陽城作營,[60]圍之數重,[61]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熛連雲,[62]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為地突,[63]或為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二公自以為功成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64]正晝有雲氣如壞山,[65]直營而霣,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66]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二公兵盛,皆怖。上歷說其意,為陳大命,請為前行諸部堅陣。上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67]二公遣步騎數千乘合戰,上奔之,斬首數十級。[68]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69]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70]上復進,二公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讀之,恐。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二公兵於是大奔北,[71]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溢。二公大眾遂潰亂,奔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為之不流。[72]王邑、莊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73]六月,上破二公於昆陽。破宛後數日,[74]收伯升部將劉稷,而伯升強爭之。更始遂用譖訴,復收伯升,即日皆物故。上降潁陽,[75]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擊馬著鼓者,[76]馬驚硠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上在父城,徵詣宛,拜上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77]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78]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擁䘿,[79]大為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走入邊郡。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威儀。」[80]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81]大司徒賜言上第一可用。[82]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上持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83]上至邯鄲,[84]趙王庶兄胡子進狗[月枼]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上灌赤眉。[85]趙王庶兄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為天子,[86]移檄購求公十萬戶。
光武為王郎所追,[87]至饒陽,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廚吏方進食,官屬從者饑,遮奪之。吏卒驚起聚語,乃椎鼓數十通,詐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懼失色。上臨升車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升,後有傳呼,寺門開之,是雒陽吏耳。上出,蒙犯霜雪。[88]光武大會真定,自擊筑。[89]上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90]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餐啗。時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上餐啗,[91]勞勉吏士,威嚴甚厲,於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92]世祖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持節詣軍門,[93]上遣棨戟迎,[94]延請入軍,見公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輿也。」公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戰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兵破邯鄲,誅郎。入王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95]公會諸將燒之,[96]曰:「令反側者自安也。」[97]上圍邯鄲未下,[98]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即立公為蕭王。[99]諸將議上尊號,上不許。又擊破銅馬,[100]受降適畢,封降賊渠率,[101]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102]上輕騎入,按行賊營。[103]賊將曰:[104]「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105]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106]卒萬餘人降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107]連破之。後反為所敗,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歿。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營門不覺。上破賊,[108]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上大笑。光武發薊還,[109]士眾喜樂,師行鼓舞,[110]鼓聲歌詠,[111]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112]諸將復請上尊號,曰:「帝王不可久曠。[113]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耿純說上曰:[114]「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上與伯升及姊婿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115]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116]上戲言:「何知非僕耶?」[117]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118]上未信,到鄗,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群臣復固請,上奏世祖曰:[119]「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120]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121]改元為建武,改鄗為高邑。[122]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123]光武破聖公,與朱伯然書曰:[124]「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
二年正月,[125]益吳漢、鄧禹等封。上封功臣皆為列侯,[126]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127]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128]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者也。」[129]乃遣謁者,即授印綬。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倪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水生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兆於城南七里,北郊四里,[130]為圓壇,[131]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132]明火德之運,徽熾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133]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為王。漢劉祖堯,[134]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135]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自感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還復於漢,宜脩奉濟陽成陽縣堯冢,雲臺致敬祭祀禮亦宜之。」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上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為寵兵掩擊破。浮軍遠,至不能救,[136]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137]南越獻白雉。[138]三年,光武征秦豐,幸舊宅。[139]十月,上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140]與舂陵父老故人為樂。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141]後改為章陵,因以舂陵為章陵縣。[142]隗囂上書,報以殊禮。[143]四年五月,上幸盧奴,為征彭寵故也。
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144]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145]或生瓜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146]採獲穀果,以為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147]建武五年,[148]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149]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野穀彌多。[150]六年二月,吳漢下朐城,[151]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152]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至掾史。[153]簡練臣下之行,[154]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155]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間講經藝,[156]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157]囂雖遣子入侍,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158]自事主未常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159]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事方略,量敵校勝。[160]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161]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162]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正月,詔群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163]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164]前後相塵,[165]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乃令上書啟封則用,[166]不得刮璽書,[167]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168]騶騎馳出召入,其餘以俟中使者出報,[169]即罷去,所見如神,[170]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浸以無限,詔誥天下令薄葬。[171]八年閏月,[172]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三萬迎上。[173]隗囂士眾震壞,皆降,囂走入城。[174]吳漢、岑彭追守之。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糒,[175]腹脹死。[176]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入犍為界,[177]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178]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為我縛賊手足矣。[179]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180]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人,不可輕也。[181]且堅據廣都城,[182]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183]十一月,眾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攻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於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上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184]「城降,嬰兒老母,[185]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186]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於放麑啜羹之義,[187]二者孰仁矣。[188]失斬將吊民之義。」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寶劍,[189]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190]苑囿池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191]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革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192]即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193]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閑,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194]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195]封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196]越裳獻白兔。[197]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198]十五年,詔曰:[199]「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200]十七年,[201]上以日食避正殿,[202]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幸章陵,[203]修園廟舊宅田里舍。鳳皇至,[204]高八九尺,[205]毛羽五彩,集潁川,群鳥並從,蓋地數頃,[206]留十七日乃去。商賈重寶,[207]單車露宿,[208]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209]光武下詔曰:「唯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210]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211]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上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二十年六月,上風眴黃癉病發甚,[212]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213]甘露降四十五日。[214]二十五年,[215]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乃自益其俸。」[216]自三公下至佐史各有差。初作壽陵,[217]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218]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219]迭興之後,[220]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上常自細書,[221]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222]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群臣爭論上前,常連日。皇太子嘗承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上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悔前徙之。[223]三十年,有司奏封襌。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224]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三十二年,[225]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也。」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為中元。[226]
中元元年,[227]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差。[228]有赤草生於水涯。[229]郡國上甘露降。群臣上言:「地祇靈應而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冬十月甲申,[230]使司空馮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於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呂太后於園,四時上祭。」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及北郊兆域。[231]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232]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為皇帝。群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233](《御覽》卷九〇)
序
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234](《文選》卷一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李善注)
上東西赴難,以車上為家,傳榮合戰,[235]跨馬操兵,身在行伍。[236](《書鈔》卷一三九)
帝即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237]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238]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239](《御覽》卷九〇)
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240](《文選》卷二三〈阮籍詠懷〉李善注)
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241](《御覽》卷二〇〇)
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遍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242](聚珍本)
光武封新野主子鄧泛為吳侯,[243]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244]追封外祖樊重為壽張侯,[245]重子丹為射陽侯,[246]孫茂為平望侯,[247]尋玄鄉侯,[248]從子沖更父侯,[249]后父陰睦宣恩侯,[250]子識原鹿侯,[251]就為信陽侯,[252]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253]弟由宜西侯,[254]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255]后父郭昌為陽安侯,[256]子流綿曼侯,[257]兄子竟新郪侯,[258]匡發干侯,[259]以姨子馮邯為鍾離侯。[260](《類聚》卷五一)
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御覽》卷三五九)
註釋
- ↑ 「世祖光武皇帝」,即劉秀,字文叔,事詳范曄《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袁宏《後漢紀》卷一至卷八。汪文臺輯謝承《後漢書》卷一、薛瑩《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卷一、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亦略載其事。
- ↑ 「承文、景之統」,此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四張衡〈南都賦〉李善注引亦有此句,今據增補。
- ↑ 「發」,此字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九〇引亦有,今據增補。
- ↑ 「舂陵節侯」,名買。
- ↑ 「考侯」,原作「孝侯」,《後漢紀》卷一同,皆誤。范曄《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云:「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為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又《文選》卷四張衡〈南都賦〉李善注云:「《東觀漢記》曰:『舂陵節侯,長沙定王中子買。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或為『孝』,非也。」今據校改。
- ↑ 「因故國名曰舂陵」,此條《御覽》卷六三、《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亦引,字句簡略。此句下尚有「上隆準日角」云云一段文字,因與下條重複,今刪去。
- ↑ 「令」,原脫,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論亦云:『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今據增補「令」字。
- ↑ 「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原脫「濟陽」二字。《文選》卷二〇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李善注引云:「濟陽有武帝行過宮。」《玉海》卷一五五引同,今據增補。
- ↑ 「開宮後殿居之」,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李賢注引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而生。」與此相合。《御覽》卷八七三,《合璧事類》卷一九、卷二二,《記纂淵海》卷四引云:「光武生於濟陽縣舍。」《類聚》卷八五、卷九九,《御覽》卷八三九、卷九一五引云:「光武生於濟陽。」
- ↑ 「有赤光,室中盡明」,此二句《類聚》卷一〇引同,《書鈔》卷一引作「赤光照室」,《初學記》卷二四引作「有赤光,堂上盡明如晝」,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李賢注引作「光照室中,盡明如晝」。
- ↑ 「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卜之長」三字原脫,不成文理。姚本、聚珍本有此三字,《類聚》卷一〇引同,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論云:「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亦可證當有此三字。《論衡·吉驗篇》云:「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蔡邕《蔡中郎文集》卷五光武濟陽宮碑云:「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生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空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赤光,室中有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月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為尊諱。」「初生」當作「初為」,「空」當作「宮」。
- ↑ 「是歲嘉禾生」,《水經注》卷七,《書鈔》卷一,《文選》卷二〇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晏元《獻公類要》卷四、卷九亦引此事。
- ↑ 「是歲鳳凰來集濟陽」,「是歲」二字姚本、聚珍本作「先是」,《類聚》卷九九、《御覽》卷九一五引同。「皇」字《玉海》卷一九九引同,《書鈔》卷一引作「凰」,二字同。《論衡·吉驗篇》云:「有鳳凰下濟陽宮,故訖今濟陽有鳳凰廬。」
- ↑ 「故宮皆畫鳳凰」,「宮」字下聚珍本有「中」字,《事類賦》卷一八引亦有「中」字,《類聚》卷九九、《御覽》卷九一五引皆無「中」字。
- ↑ 「日角」,額上之骨隆起如日,古人以為帝者之象。《御覽》卷三六七引云:「光武為人日角,大口,美鬚眉。」
- ↑ 「美鬚眉」,《書鈔》卷一引作「美鬚髯」。
- ↑ 「在舂陵時」,此句至「王氣鬱鬱蔥蔥」諸句原無。《書鈔》卷一五一引「望氣者蘇伯阿望舂陵城曰」以下三句。聚珍本有此數句,作「在舂陵時,望氣者言舂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蔥蔥。』」今據《書鈔》卷一五一引輯錄,并據聚珍本增補「在舂陵時」一句。
- ↑ 「遠」,姚本、聚珍本作「達」,《書鈔》卷六引亦作「達」。
- ↑ 「高祖兄」,「兄」字下聚珍本有「仲」字。仲為漢高祖劉邦兄,能治產業。《史記·高祖本紀》云:「未央宮成,……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 ↑ 「年九歲」,此上原有「伯升」二字,聚珍本無。按當無「伯升」二字,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可證,今刪去。
- ↑ 「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此句原作「受尚書經,師事廬江許子威」,今從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校改。《書鈔》卷一二僅引「師事子威」一句。
- ↑ 「資用乏」,此句至「以給諸公費」諸句原無,姚本、聚珍本和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有,今據增補。《文選》卷三八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李善注引亦有,「諸公」二字下有「之」字。
- ↑ 「以給諸公費」,《書鈔》卷三引「僦驢給費」四字,即括引此文。
- ↑ 「高才好學」,此句至「舍長安尚冠里」七句原無,姚本、聚珍本有,今據增補。
- ↑ 「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此句至「莊公寧視卿邪」諸句原無,而有「嘗訟逋租於大司馬莊尤,尤見而奇之」二句,今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增改。此段文字聚珍本作「嘗為季父故舂陵侯訟逋租於大司馬莊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祜。帝歸戲福曰:『莊公寧視卿耶?』」朱祜即朱福。據范曄《後漢書·朱祜傳》李賢注,《東觀漢記》「祜」作「福」,避安帝諱改。光武帝為舂陵侯訟租事,《書鈔》卷三亦引,字句甚簡。
- ↑ 「王莽時」,此句至「四方潰畔」諸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
- ↑ 「荊州下江平林兵起」,此下二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亦有,今據增補。
- ↑ 「時南陽旱餓」,此下二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地皇三年,南陽荒餓,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李賢注引《東觀漢記》云:「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今據增補。聚珍本亦有此二句,「上」字作「帝」。
- ↑ 「李伯玉」,聚珍本注云:「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
- ↑ 「先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為醫」,范曄《後漢書·李通傳》李賢注引《續漢書》云「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後漢紀》卷一云:「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為醫術,以其難使也,縯殺之。」《書鈔》卷一二三引《東觀漢記》亦云李通同母弟為申徒臣,與此不同。
- ↑ 「固始侯」,原誤作「因始侯」,聚珍本作「固始侯」,今據改正。范曄《後漢書·李通傳》云:「建武二年,封固始侯。」
- ↑ 「劉氏當復起,李氏為輔」,此二句讖語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八七二引亦有,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載此讖語,但無「當」字。
- ↑ 「父為宗卿師」,范曄《後漢書·李通傳》云:通父守,「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李賢注云:「平帝五年,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 ↑ 「市兵弩」,《書鈔》卷三引「市弓弩」三字,即出於此。
- ↑ 「絳衣赤幘」,此四字上《書鈔》卷一二七引有「皆著」二字,《御覽》卷六八七、卷八一四、卷八七二引無。
- ↑ 「若火光」,此三字上《御覽》卷八七二引有「有」字。
- ↑ 「赫然屬天」,此句《御覽》卷八七二引作「曈曈上屬天」。
- ↑ 「異之」,此句姚本作「上異之」,《御覽》卷八七二引同。
- ↑ 「大冠」,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董巴《輿服志》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之。」
- ↑ 「將軍服」,此三字上聚珍本有「服」字。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通鑑》卷三八胡三省注引云:「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將軍服」上亦無「服」字。
- ↑ 「中」,聚珍本作「仲」。按「中」字讀作「仲」。此指光武帝劉秀。《御覽》卷六九〇引云:「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御覽》卷六八七、《玉海》卷八一亦引,字句簡略。
- ↑ 「殺新野尉」,「殺」字下原衍「進」字,姚本、聚珍本無,《類聚》卷九三、《御覽》卷二六九引亦無,今據刪。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 ↑ 「光武起義兵」,此句至「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三句原無,《書鈔》卷一二八引此三句,今據增補。姚本作「光武起義兵,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聚珍本同,惟「光武」二字改作「帝」。二本所輯皆有「攻南陽」一句,係出陳禹謨刻本書鈔。聚珍本於「著大冠絳單衣」下注云:「此有闕文。考范書殺新野尉即在是時。」
- ↑ 「使劉終詐稱江夏吏」,此下二句原無,姚本、聚珍本有,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李賢注引《東觀漢記》云:「劉終詐稱江夏吏,誘殺之。」姚本、聚珍本即據此增改。
- ↑ 「五威將軍莊尤擊下江兵」,此下三句原無。《書鈔》卷一四七引作「上擢穀相,五威將嚴尤當擊江賊,上奉糗一斛,脯三十朐詣幕府營」。《御覽》卷八六〇引作「嚴尤擊江賊,世祖奉糗一斛,脯三十朐」。聚珍本亦有此三句,作「嚴尤擊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朐」。今綜合三處文字增補。《漢書·王莽傳》地皇三年載:「是時下江兵盛,……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
- ↑ 「進圍宛城」,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更始元年進圍宛城。更始元年即王莽地皇四年。
- ↑ 「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將軍」,《四庫全書》考證云:「按前漢書《莽傳》云:『莽地皇四年三月,漢立聖公為帝。四月,莽遣尋、邑發兵。』范書《光武紀》與《漢書》同,惟謂更始即位在是年二月,今尋繹本文,則似更始之立,又在王莽發兵之後,與班、范二書異。」
- ↑ 「入朝」,此二字原無,《御覽》卷六八三引亦無此二字。姚本、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亦有,今據增補。
- ↑ 「二公」,聚珍本作「尋、邑」。
- ↑ 「莊尤」,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桓譚《新論》云:「莊尤,字伯石,此言『嚴』,避明帝諱也。」
- ↑ 「美眉目」,聚珍本作「美鬚眉目」,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作「美須眉」。
- ↑ 「二公」,聚珍本作「尋、邑」,以下皆同。《御覽》卷三三六、卷三三九引作「王尋、王邑」。
- ↑ 「甲衝輣」,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三三六引亦有,今據增補。《書鈔》卷一三九引作「甲衝棚,戰攻之具甚盛」。《御覽》卷三三九引作「甲衝輣,干戈旌旗甚盛」。「衝」,橦車,是一種陷陣戰車。「輣」,樓車。
- ↑ 「虎」,此字原脫,姚本、聚珍本有,《書鈔》卷一一八、《類聚》卷一二引亦有,今據增補。
- ↑ 「巨無霸」,《漢書·王莽傳》云:「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壘尉」,即壘校尉,主軍壘之事。姚本、聚珍本作「中壘校尉」,《書鈔》卷一一八引同。《類聚》卷一二引作「壘校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作「壘尉」。
- ↑ 「為畫成敗」,《書鈔》卷一四引作「圖畫成敗」。
- ↑ 「時漢兵八九千人」,此句原無,姚本、聚珍本有,《類聚》卷一二引亦有,今據據補。
- ↑ 「留王鳳令守城」,此下二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亦有,今據增補。
- ↑ 「五六萬」,聚珍本同,《書鈔》卷一一七引亦同。姚本作「五六十萬」,《書鈔》卷一二一、《類聚》卷一二引與姚本同。
- ↑ 「作」,原無此字,聚珍本有,《類聚》卷一二、《御覽》卷三三六引亦有,今據增補。尋、邑圍昆陽事,《文選》卷五七潘岳〈馬汧督誄〉李善注亦引,字句較簡。
- ↑ 「數重」,《御覽》卷三三六引同,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云尋、邑「圍營數重」,《後漢紀》卷一亦云「圍之數重」。姚本作「數百重」,《類聚》卷一二引亦作「數百重」。聚珍本作「數十重」,與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同。聚珍本注云:「姚之駰本作『數百重』,參范書帝紀,則『百』字誤。」
- ↑ 「塵熛連雲」,此句《文選》卷七潘岳〈藉田賦〉李善注引作「埃塵連天」。
- ↑ 「地突」,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作「地道」,《後漢紀》卷一作「地窟」。
- ↑ 「尋」,此字原無,姚本、聚珍本有,《類聚》卷一二引亦有,今據增補。
- ↑ 「正晝有雲氣如壞山」,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云:「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劉昭注引袁山松書云:「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 ↑ 「壓」,聚珍本同,《御覽》卷八七七引亦作「壓」。姚本作「厭」,《類聚》卷一二引亦作「厭」。按二字通。
- ↑ 「前去大軍四五里」,此句聚珍本作「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作「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
- ↑ 「數十」,原脫「十」字,姚本、聚珍本有,與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相合,今據增補。《書鈔》卷一一八引云「斬首千級」。
- ↑ 「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書鈔》卷一四引此下二句,文字稍異。
- ↑ 「甚奇怪也」,此句姚本作「甚可怪也」,《書鈔》卷一一八引同。
- ↑ 「二公兵於是大奔北」,此下二句聚珍本作「尋、邑兵大奔北,於是殺尋」。
- ↑ 「滍水為之不流」,《書鈔》卷一三引「滍水不流」四字。
- ↑ 「齊武王」,即劉伯升,光武帝建武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
- ↑ 「六月」,此句至「收伯升部將劉稷」四句聚珍本作「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
- ↑ 「上降潁陽」,此句至「乃馬也」諸句原無,《御覽》卷三九四引有此段文字。聚珍本把此段文字連綴於上文「即日皆物故」句下。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據此,聚珍本所做連綴基本可信,今從之。
- ↑ 「擊」,聚珍本作「繫」。
- ↑ 「更始害齊武王」,此句至「枕席有涕泣處」諸句原無,聚珍本有,《類聚》卷三五,《御覽》卷三八七、卷四八八引亦有,今據增補。《文選》卷四〇任昉〈百辟勸進今上牋〉李善注引亦有此段文字,字句稍異。
- ↑ 「文書移與屬縣」,此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通鑑》卷三九胡三省注引亦有,今據增補。
- ↑ 「諸于」,《漢書·元后傳》云:「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顏師古注:「諸于,大掖衣,即褂衣之類也。」「于」即「衧」之省。「繡擁䘿」,原「擁」字為空格,聚珍本有此字,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諸于繡镼。」李賢注云:「或『繡』下有『擁』字。」李賢又注云「字書無『镼』字,《續漢書》作『䘿』,音其物反。楊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西謂之䘪䘿。』郭璞注云:『俗名䘿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繡䘿,如今之半臂也。」「擁䘿」即䘪䘿。
- ↑ 「粲然」,此二字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三〇謝朓〈五言詩〉始出尚書省李善注引亦有,今據增補。「復見漢官威儀」,《書鈔》卷一七引作「復見漢官儀」,《文選》卷三〇謝朓詩李善注引作「復見官府儀體」。
- ↑ 「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此下二句原無,《御覽》卷二〇九引,今據增補。聚珍本亦有此二句,惟下句「上」字作「帝」。
- ↑ 「賜」,劉賜,光武帝族兄,事見范曄《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傳》。
- ↑ 「安集百姓」,《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聖公為天子,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
- ↑ 「上至邯鄲」,此下二句原無,聚珍本有,《書鈔》卷一四六引有此二句,今據增補。又《書鈔》卷一四五亦引,惟「上」字作「光武」。
- ↑ 「故趙繆王子臨說上灌赤眉」,原無此句。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李賢注云:「《東觀記》『林』作『臨』字。」是知《東觀漢記》有臨說光武帝事,今撮取范書大意增補此句。「趙繆王」,即劉元,以刃殺奴婢,謚曰繆。事見《漢書·景十三王傳》。
- ↑ 「趙王庶兄胡子立邯戰卜者王郎為天子」,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光武帝「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為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胡子與臨是否為一人,無從確考。「天子」,原誤作「太子」,聚珍本不誤,今據改正。
- ↑ 「光武為王郎所追」,此句至「是雒陽吏耳」諸句原無,《書鈔》卷一三九引,今據增補。《書鈔》卷一三九所引無「光武為王郎所追」一句,此句係據《書鈔》卷一四四引增補。又「至饒陽」句上《書鈔》卷一三九引有「上發」二字,為使文義通順,刪此二字。此段文字聚珍本作「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姚本作「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其下各句與聚珍本同,惟聚珍本「帝」字姚本作「光武」。此段文字《書鈔》卷一四三引作「光武至饒陽,稱邯鄲使者,如傳合。廚吏方進食,官屬從者饑,遮奪之」。
- ↑ 「上出,蒙犯霜雪」,此二句原無。《文選》卷二〇應瑒〈五言詩〉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李善注引「蒙犯霜雪」一句,今連綴於此。為使文理通順,又增「上出」二字。聚珍本把「蒙犯霜雪」一句繫於《光武帝紀》篇末,當作年代不可考者。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所載,光武帝離饒陽傳舍後,「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是《文選》李善注所引「蒙犯霜雪」一句當編次於此,聚珍本失考。
- ↑ 「光武大會真定,自擊筑」,此二句原無,《書鈔》卷一一〇引云:「光武大會真定,王制楊自擊筑。」今據增補,刪「王制楊」三字。「制楊」二字義不可解,必有舛誤。此二句聚珍本作「大會真定,帝自擊筑」,其上又有以下一段文字:「夜止蕪蔞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灶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灶炙衣。」考之范曄《後漢書》,此段文字當入《馮異傳》。《御覽》卷九〇未引此段文字,聚珍本輯者是據《書鈔》卷一二九、卷一三五、卷一四四所引連綴。
- ↑ 「上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此句至「劉公真天人也」諸句原無。《御覽》卷九〇屢引《東觀漢記》,有一處引云:「上破王郎,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餐啗。時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上餐,勞勉吏士,威嚴甚厲,於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又卷九三五引云:「世祖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士吏,威嚴甚厲,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今綜合兩處所引增補。聚珍本有此段文字,字句微異。又《書鈔》卷一四五、《御覽》卷八四七、范曄《後漢書·鄧禹傳》李賢注亦引,字句較簡略。
- ↑ 「餐啗」,《書鈔》卷一四五引作「食噉」。
- ↑ 「劉公真天人也」,杜工部《草堂詩箋補遺》卷二四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引云:「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節刪頗多。
- ↑ 「杜長威」,范曄《後漢書·王郎傳》、袁宏《後漢紀》卷二亦載杜長威詣光武帝營請降事,「杜長威」作「杜威」。「持節詣軍門」,此五字及下二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
- ↑ 「棨戟」,范曄《後漢書·杜詩傳》云:「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李賢注:「《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
- ↑ 「得吏民」,此三字上《類聚》卷一二引有「尋」字。
- ↑ 「公會諸將燒之」,《書鈔》卷九引「燒吏民謗帝」一句,即係括引此文。
- ↑ 「令反側者自安也」,上文「漢兵破邯鄲」至此句,《四庫全書》考證云:「按范書《光武紀》文與此同,《王郎傳》則云:『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說復小異。又此數句,姚本有之,而文有異同,今從《永樂大典》本。」「反側」,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者」,姚本作「子」,《類聚》卷一二、《文選》卷四三丘遲〈與陳伯之書〉李善注引亦作「子」,與范書《光武帝紀》、《後漢紀》卷二同。
- ↑ 「上圍邯鄲未下」,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有,《書鈔》卷一四七引,今據增補。
- ↑ 「更始遣使者即立公為蕭王」,《文選》卷四〇吳質〈答魏太子牋〉李善注引此一句,無「即」字,又「公」作「光武」。《初學記》卷九亦引更始立光武帝為蕭王事,字句極疏略。
- ↑ 「又擊破銅馬」,此句至「由是皆自安」諸句原無,《類聚》卷一二引,今據增補。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字句微異。
- ↑ 「封降賊渠率」,此下二句《類聚》卷一二引無,今據《文選》卷四三丘遲《與陳伯之書》李善注引增補。
- ↑ 「營」,此字《類聚》卷一二引無,聚珍本有,《文選》卷四三丘遲與陳伯之書李善注引亦有,今據增補。
- ↑ 「按行賊營」,《書鈔》卷一四引此一句。
- ↑ 「將」,此字《類聚》卷一二引無,今據《文選》卷四三丘遲與陳伯之書李善注引增補。
- ↑ 「投」,聚珍本同,《御覽》卷三七一引亦同,又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後漢紀》卷二也作「投」,惟《文選》卷四三丘遲與陳伯之書李善注引作「效」。
- ↑ 「詔馮異軍鴈門」,此下二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姚本亦有此下二句,作「詔曰,馮異軍鴈門,囗卒萬餘人降之」。聚珍本注云:「『詔』字下原本衍『曰』字,今刪。考范書帝紀及馮異傳俱不載此詔,惟異拒朱鮪、李軼時曾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則軍鴈門當即在是時。」
- ↑ 「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此二句至「營門不覺」諸句原無。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李賢於「追至右北平」句下注云:「《東觀記》、《續漢書》并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由此可知,東觀漢記原有光武擊尤來、大搶、五幡事。今據范書酌補「光武北擊尤來」至「或云已歿」諸句,以使上下文理通順。李賢又於「或云已歿」句下引東觀漢記云:「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營門不覺。」今亦補入。
- ↑ 「上破賊」,此句至「上大笑」諸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四九九引,今據增補。
- ↑ 「光武發薊還」,此句至「命諸將收葬吏士」諸句原無,今據《御覽》卷五五三引增補。聚珍本有此諸句,文字微異。
- ↑ 「師行鼓舞」,此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四六八引亦有,今據增補。
- ↑ 「鼓聲歌詠」,此句聚珍本作「歌詠雷聲」,《御覽》卷四六八引同。
- ↑ 「至中山」,原有「上發薊」三字,為避免與上文重複,今刪去。
- ↑ 「曰:帝王不可以久曠」,此二句至「萬姓為心」諸句原無。《文選》卷三七劉琨勸進表李善注云:「《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又注云:「《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今綜合兩處所引增補。聚珍本未輯「帝王不可以久曠」句。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
- ↑ 「耿純說上曰」,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四九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亦有此三句,今據增補。
- ↑ 「伯升」,姚本、聚珍本作「伯叔」,《類聚》卷一二引同。按「伯升」二字是,范曄《後漢書·鄧晨傳》云:「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
- ↑ 「劉子駿」,即劉歆。歆字子駿,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
- ↑ 「何知非僕耶」,此句《類聚》卷一二引作「何用知僕非也。」
- ↑ 「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此句姚本作「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類聚》卷一二引同。
- ↑ 「上奏世祖曰」,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亦未輯錄。《文選》卷三七劉琨《勸進表》李善注引,今據增補。
- ↑ 「乃命有司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原無「五成陌」三字,《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乃命有司設壇場於鄗之陽千秋亭五成陌。」今據增「五成陌」三字。
- ↑ 「燔燎告天,禋於六宗」,此二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五二八亦引,今據增補。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續漢志:「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為天地四方之宗,祠於洛陽之北,戌亥之地。」」
- ↑ 「改鄗為高邑」,此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亦引,今據增補。此句下聚珍本尚有以下一段文字:「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宣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斤。」」《御覽》卷九〇未引此段文字。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此詔在卓茂傳,今依范書編次。
- ↑ 「遂定都焉」,此句原無,聚珍本有,又《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李善注引云:「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今據補「遂定都焉」句。
- ↑ 「光武破聖公,與朱伯然書曰」,此二句至「太白清明」諸句原無,《御覽》卷五引,姚本、聚珍本亦有此數句,今據增補。「朱伯然」,《御覽》卷五引誤作「伯叔」。《書鈔》卷一五〇引云:「光武破二公,與朱伯然書曰:「交鋒之月,神星晝見,太白清明。」」今據改作「朱伯然」。姚本、聚珍本作「朱然」。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未即位前使馮異、寇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即位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國公王匡軍,此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然」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訛脫。」按朱伯然,不見范曄《後漢書》、《後漢紀》,此段文字的前後內容無從考知。
- ↑ 「二年」,原誤作「三年」,聚珍本作「二年」,與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後漢紀》相合,今據改正。
- ↑ 「上封功臣皆為列侯」,此句至「即授印綬」諸句原無,《類聚》卷五一引,今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所載,將此段文字連綴於建武二年正月下。聚珍本把此段文字移入丁恭傳內,無所依據。
- ↑ 「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云:「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
- ↑ 「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雷」字《御覽》卷一九八引同,《書鈔》卷四七引作「周」。按「雷」字是,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作「雷」。李賢注云:「易屯卦震下坎上,震為雷,初九曰「利建侯」,又曰「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
- ↑ 「聞」,《類聚》卷五一引無此字,聚珍本有,《御覽》卷一九八引亦有,今據增補。
- ↑ 「制郊兆於城南七里,北郊四里」,此二句原作「制郊祀於城南」。《御覽》卷五二七引云:「上都雒陽,制兆於城南七里,北郊四里。」今據增改。聚珍本與《御覽》卷五二七引同,惟「上」字作「故帝」二字。
- ↑ 「為圓壇」,此下三句原無,《玉海》卷九四引云:「光武於雒陽城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今據增補。姚本、聚珍本皆未輯此段文字。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李賢注引《續漢書》云:「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
- ↑ 「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此二句原無「時以」六字,聚珍本有,《御覽》卷五二七引亦有,今據增補。
- ↑ 「季夏黃色」,此句至「雲臺致敬祭祀禮亦宜之」諸句,原僅有「郊祀帝堯以配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二句,且「宗」下又脫「祀」字。今據《御覽》卷五二七引增補。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末句作「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
- ↑ 「漢劉祖堯」,原脫「堯」字,聚珍本有,今據增補。
- ↑ 「宜令」,此二字原誤倒,今據聚珍本乙正。
- ↑ 「至不能救」,此句聚珍本作「不敢救」。《後漢紀》卷四云:「浮遠,不能救。」四庫全書考證云:「按是時浮為幽州牧,彭寵攻浮於薊,則寵為客,浮為主,非浮遠至也。范書云:「帝讀檄,怒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寵果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最得其實,本書「至」字疑衍。」按「至」字與「不能救」三字作一句讀,文義可通。考證誤以「至」字與上文連讀,遂疑「至」字為衍文。
- ↑ 「咸曰上神」,《後漢紀》卷四云:「吏還說上語,皆以為神也。」
- ↑ 「南越獻白雉」,此句原無,稽瑞引云:「光武建武二年,南越獻白雉。」今據增補。
- ↑ 「光武征秦豐,幸舊宅」,此二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四張衡南都賦李善注、《玉海》卷一七五亦引,今據增補。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斬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於黎丘。至冬十月,乃幸舂陵。此牽連書之,殊未明晰。」
- ↑ 「上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此事《類聚》卷三九、《御覽》卷五二六亦引,字句相同。《書鈔》卷一六引「置酒舊宅」四字,當為同一事。
- ↑ 「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五五七亦引,今據增補。
- ↑ 「因以舂陵為章陵縣」,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傜役,比豐、沛,無有所豫。」此蓋牽連後事言之。《文選》卷四張衡南都賦李善注亦引此句,文字微異。
- ↑ 「隗囂上書,報以殊禮」,此二句原無,聚珍本有,《書鈔》卷九亦引,今據增補。《書鈔》卷一一引「待以殊禮」四字,與此為同一事。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 ↑ 「一石」,《書鈔》卷一五六引作「一斗」。
- ↑ 「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編珠卷四、《類聚》卷八五亦引此文。「旅」,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上李賢注云:「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類聚》卷八五引作「旋」,誤。
- ↑ 「其」,聚珍本作「為」,《文選》卷三四枚乘七發李善注引亦作「為」。
- ↑ 「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稽瑞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蠶自繭,披於山阜,民收其利,其後耘蠶稍廣,二物漸息。」與此文字出入較多。又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櫓生。五年彌多。」「櫓」當作「穭」,與「旅」字古通。「五年彌多」句,諸書皆未引徵。
- ↑ 「建武五年」,此句至「賜博士弟子有差」諸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五三四引,今據增補。
- ↑ 「諸生吏子弟」,其上原有「宮」字,係衍文,聚珍本無,《書鈔》卷八三、《類聚》卷三八引皆無此字,今據刪。
- ↑ 「野穀彌多」,此句原無,稽瑞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櫓生,五年彌多。」今據增補。「櫓」乃「穭」之訛,上文注已有說。
- ↑ 「吳漢下朐城」,平定董憲、龐萌,見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後漢紀》卷五。
- ↑ 「取此兩子置度外」,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
- ↑ 「至」,此字原脫,從文義來看,當有此字。聚珍本有,今據增補。
- ↑ 「簡練臣下之行」,《書鈔》卷七引「簡練臣下」四字。
- ↑ 「吏民驚惶」,《後漢紀》卷五云:「每幸郡國,見父老掾吏,問數十年事,吏民皆驚喜。」
- ↑ 「上猶以餘間講經藝」,「講」字《書鈔》卷一四引作「謀」,誤。《書鈔》卷一〇三、《類聚》卷五八引云:「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間講經藝。」《御覽》卷五九七、《永樂大典》卷二〇八五〇引同,惟脫「賞」字。
- ↑ 「署曰「公孫皇帝」」,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 ↑ 「到朝廷凡數十見」,范曄《後漢書·馬援傳》云:「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李賢注云:「《東觀記》曰凡十四見。」《通鑑》卷四一胡三省注引同。
- ↑ 「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此二句《書鈔》卷一四引作「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 ↑ 「校」,《書鈔》卷一四引作「受」。
- ↑ 「反復勝也」,據范曄《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聽信馬援之言,遂遣長子恂入質。而此記載隗囂遣子入侍在馬援之言以前,彼此歧異。
- ↑ 「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此句至「以為國家坐知千里」諸句原無,《文選》卷四〇任昉《奏彈曹景宗》李善注引有,今據增補。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字句微異。《書鈔》卷七引,僅有「坐知千里」四字。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六月載;「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歿。」又〈盧芳傳〉云:「建武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
- ↑ 「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此句《書鈔》卷一三六引作「上書以青布製囊素裹封書」。
- ↑ 「報」,原誤作「執」,聚珍本作「報」,今據改。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亦作「報」。
- ↑ 「塵」,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覽作「屬」。」是聚珍本輯者所用御覽與影宋本御覽字異。按作「塵」作「屬」,於義均通,而以「塵」字義長。《文選》卷一五張衡思玄賦李善注;「塵,久也。」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作「塵」。
- ↑ 「上書」,聚珍本同,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作「尚書」。
- ↑ 「刮璽」,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覽》作「引經」。」與影宋本御覽字異。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作「刮璽」。
- ↑ 「常以日出時」,「日」字下原衍一「日」字,聚珍本無,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亦無,今據刪。
- ↑ 「其餘以俟中使者出報」,此句聚珍本作「其餘禺中使者出報」,字有脫誤,當以《御覽》卷九〇所引為正。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作「其餘遇中使者出報」,亦有訛脫。
- ↑ 「所見」,聚珍本脫,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亦脫。
- ↑ 「詔誥天下令薄葬」,「詔」字下原衍「有」字,聚珍本無,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亦無,今據刪。
- ↑ 「八年閏月」,此年閏四月。
- ↑ 「五郡」,原誤作「五部」,聚珍本不誤,今據改。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八年「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大將軍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李賢注:「五郡謂隴西、金城、天水、酒泉、張掖。」《後漢紀》卷六云:建武閏四月,「竇融與五郡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第一」。第一屬高平縣。
- ↑ 「入」,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覽作「西」。」聚珍本輯者所用御覽與影宋本御覽字異。
- ↑ 「出城餐糗糒」,「餐」字下原衍「糧」字,聚珍本無,今據刪。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建武「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李賢注云:「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 ↑ 「腹脹死」,此下聚珍本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注云:「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陽;還,幸章陵,祠園陵。」《後漢紀》卷六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陽,過章陵,祠園廟。」《通鑑》卷四二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皆不言修園廟舊宅田里舍。初學記卷二四引東觀漢記云:「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顯然,聚珍本所輯是據初學記,把十七年事誤繫於十一年。范書光武帝紀十七年載: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乃悉為舂陵宗室起祠堂。……。十二月,至自章陵」。事又見《通鑑》卷四三。初學記所引與范書、通鑑完全相合。又光武帝在建武十一年幸章陵,來去匆匆,未能久停,不可能修園廟舊宅。而十七年幸章陵,停留兩月之久,故有時間修園廟舊宅。聚珍本編次失誤,可以肯定無疑。又按《文選》卷四張衡〈南都賦〉李善注引東觀漢記云:「建武中,更名舂陵為章陵,光武過章陵,祠園廟。」此所引乃東觀漢記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文,已見前。聚珍本在此引李善注所引為注,舛亂失次。
- ↑ 「入犍為界」,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蓋通始事言之。」
- ↑ 「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此「成都」乃「廣都」之誤。《後漢紀》卷六云:「漢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可為確證。
- ↑ 「獨言朝廷以為我縛賊手足矣」,此句文義不明,必有脫文。
- ↑ 「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此為拔廣都後事,上文敘事未完。范曄《後漢書·吳漢傳》云:「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 ↑ 「成都十萬人,不可輕也」,原無下句。此二句聚珍本作「成都十萬餘眾,不可輕也」,今據補下句。范曄《後漢書·吳漢傳》云:「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
- ↑ 「且」,范曄《後漢書·吳漢傳》作「但」。
- ↑ 「移徙輒自堅」,此敘事未完。據范曄《後漢書·吳漢傳》、《後漢紀》卷六所載,此下有吳漢違詔兵敗事,被引書者刪去。
- ↑ 「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此句《文選》卷五二魏文帝典論李善注引作「上詔讓漢曰」。後漢記卷六作「詔讓吳漢、劉尚曰」。按范曄《後漢書·吳漢傳》云:漢「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李賢注云:「《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作「禹」。」
- ↑ 「嬰」,《文選》卷五二魏文帝典論李善注作「孩」,與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同。
- ↑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此二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五二魏文帝《典論》李善注、王應麟《急就篇補注》卷三亦引,今據增補。「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為民間習語,言人各自以其所有為善。
- ↑ 「放麑」,《韓非子說林》云:「孟孫獵得麑,使秦巴西持之歸,其母隨之而啼,秦巴西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日,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又載淮南子人間訓、說苑貴德。「啜羹」,《戰國策魏策》云:「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 ↑ 「矣」,聚珍本注云:「《太平御覽》作「且」。」與影宋本御覽字異。
- ↑ 「名都王國」,聚珍本同,《書鈔》卷一三九、《類聚》卷九三、《文選》卷一四顏延之赭白馬賦李善注、《玉海》卷一四八引亦同。《御覽》卷三四二、事類賦卷一三引無「名都」二字。《書鈔》卷三一兩引,一引作「屠耆國」,一引作「屠耆」。
- ↑ 「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書鈔》卷一五、卷一二二亦引此事。
- ↑ 「手不持珠玉」,《書鈔》卷八引「不持珠玉」四字,與此相合。
- ↑ 「公孫述故哀帝時」,此下有脫文。按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為郎。……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由此可以推知下文大意是說述哀帝時為郎,習見漢家制度,據蜀時,以數郡之地備漢家威儀。
- ↑ 「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郊」字原誤作「交」,「樂」字下又脫「器」字。聚珍本作「郊」,亦脫「器」字。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
- ↑ 「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此下二句《書鈔》卷一五亦引。
- ↑ 「十三年」,此句至「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諸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二〇一亦引,今據增補。「十三年」,御覽引誤作「建武二年」。
- ↑ 「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 ↑ 「越裳獻白兔」,此句原無,稽瑞引云:「光武建武十三年,越裳獻白兔。」今據增補。
- ↑ 「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十四年載:「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為褎成侯。」李賢注:「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志,均子。古今注曰志時為密令。」
- ↑ 「十五年,詔曰」,此二句至「聚人遮道啼呼」諸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亦引有此段文字,惟無「十五年,詔曰」五字,今據增補。
- ↑ 「聚人遮道啼呼」,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隆坐徵下獄。」此所載詔文未完。」
- ↑ 「十七年」,此句至「起居平愈」諸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亦引,僅無「十七年」三字,今據增補。《書鈔》卷九六、卷一三九,《御覽》卷七四一亦引此段文字,字句皆較簡略。
- ↑ 「上以日食避正殿」,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十七年載:「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 ↑ 「幸章陵」,此下二句原無,初學記卷二四引,今據增補。聚珍本誤置於建武十一年。
- ↑ 「鳳皇至」,此句至「留十七日乃去」諸句原無,初學記卷三〇引,今據增補。「至」,聚珍本作「五」,《御覽》卷九一五引同,《類聚》卷九九引作「出」。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十七年十月載:「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郟縣。」
- ↑ 「高八九尺」,《御覽》卷九一五引同。姚本作「高八尺」,六帖卷九四、萬花谷後集卷四〇、合璧事類別集卷六二、《玉海》卷一九九、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亦作「高八尺」。聚珍本作「高八尺九寸」,《類聚》卷九九引同。
- ↑ 「蓋地數頃」,此上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有「行列」二字。
- ↑ 「商賈重寶」,此句至「道無拾遺」諸句原無,聚珍本有,《文選》卷四九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亦引,今據增補。此句上李善注引又有「建武十七年」五字。
- ↑ 「單車露宿」,《書鈔》卷一五引此一句。
- ↑ 「十九年」,此句至「其上尊號曰中宗」諸句原無,聚珍本有,惟「光武」二字作「帝」。《御覽》卷八九引亦有此段文字,僅無「十九年」三字。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 ↑ 「一歲」,《類聚》卷三九引作「一年」。
- ↑ 「陛下識知寺舍」,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云:「《風俗通》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
- ↑ 「眴」,原誤作「」,聚珍本作「眩」,《御覽》卷七四一引亦作「眩」,按「眴」與「眩」,二字通。
- ↑ 「廣室」,《御覽》卷七四一引作「廟室」。按當作「廣室」。范曄《後漢書·陰興傳》李賢注云:「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通鑑》卷四三胡三省注云:「余謂廣室者,寢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
- ↑ 「甘露降四十五日」,此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按《御覽》卷一二引云:「光武帝時,甘露降四十五里。」又卷八七二引云:「光武時,甘露降四十五日。」合璧事類卷一九引同。所引皆未明言具體年代,范曄後漢書、後漢記、通鑑諸書亦未載降甘露事,聚珍本繫於建武二十年,不知何據。
- ↑ 「二十五年」,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有,《類聚》卷九五亦引,今據增補。《御覽》卷九一二引作「建武二十五年,烏桓詣闕朝賀,獻貂皮」。
- ↑ 「乃自益其俸」,此句聚珍本作「今益其俸」,王先謙後漢書光武帝紀集解引作「□今益其奉」。
- ↑ 「初作壽陵」,此句至「乃令陶人作瓦器」一段文字原引作「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而《御覽》卷五五七引云:「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寶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卷九〇又引云:「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今綜合各處所引增訂。聚珍本所輯重複竄亂。「壽陵」,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云:「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漢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今循舊制也。」
- ↑ 「松、喬」,赤松子、王子喬,皆仙人。
- ↑ 「陂池」,刊謬正俗卷五云:「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吊二世賦「登陂陀之長阪」。凡陂陀者,猶言靡陀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陀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為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 ↑ 「迭興」,《通鑑》卷四四胡三省注云:「謂易姓而王者。」
- ↑ 「上常自細書」,此為建武二十六年事。此句上原有「臨平望平陰」至「霸陵獨完,非成法耶」一段文字,詳見注【217】。為避免與上文重出,今刪去。
- ↑ 「夜講經」,《書鈔》卷一二僅引此三字。
- ↑ 「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悔前徙之」,此三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二十六年李賢注亦引,今據增補。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蕃稱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謂掃地更為者此也。」此三句下聚珍本有「草創苟合,未有還人」二句。按「草創」云云二句,范曄《後漢書·趙傳》李賢注引,今歸入趙傳。
- ↑ 「汙七十二代」,《書鈔》卷八引此五字。《史記·封禪書》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說文解字敘云:「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初學記卷九引桓譚新論云:「太山之上,有石刻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論衡·書虛篇》云:「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是知封太山、禪梁父有七十二家,此為通行說法。
- ↑ 「三十二年」,此句至「勒石紀號」諸句原作「三十年,群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聚珍本同,惟「三十年」作「三十二年」。《書鈔》卷九一引《東觀漢記·光武紀》云:「中元元年,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也。」」今據聚珍本改「三十年」作「三十二年」,又據《書鈔》卷九一所引光武紀增補「群臣復奏言」云云四句。此段文字《御覽》卷五三六亦引,收入本書郊祀志。
- ↑ 「中元」,原誤作「中平」,聚珍本不誤,今據改。
- ↑ 「中元元年」,此句至「獨眇蹇者不差」諸句原無,聚珍本有,《類聚》卷九八亦引,今據增補。又《御覽》卷八七三亦引此段文字,字句較為簡略。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是年四月改元。
- ↑ 「差」,《御覽》卷八七三引同,聚珍本作「瘥」。按二字通。
- ↑ 「有赤草生於水涯」,此句至「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諸句原無,《類聚》卷九八引,今據增補。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惟「上遂」二字作「帝」,「記」作「紀」,又無「焉」字。餘與《類聚》卷九八引同。稽瑞引云:「光武中元元年,有赤草生於水涯。」又引云:「光武中元元年,祀長陵,醴泉出京師,又赤草生於水涯。」所引皆甚簡略。
- ↑ 「冬十月甲申」,此句至「四時上祭」諸句原無,《御覽》卷一三六引云:「中元元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后不宜配食。薄太姬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於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呂太后於園,四時上祭。」又卷五三一引云:「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祀高祖廟,呂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呂太后於園,四時上祭。」今綜合兩處所引增補。聚珍本有此段文字,僅個別字歧異。《書鈔》卷二四僅引「太后慈仁,子孫賴福」二句。
- ↑ 「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及北郊兆域」,此三句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初學記卷一三引云:「光武中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類聚》卷三八引同。惟無「光武中」三字。《御覽》卷五二七引云:「光武中元年,起明堂、辟雍、靈臺及北郊。」三書所引皆有脫文。此三句下聚珍本尚有「宣布圖讖於天下」一句,不知輯自何書。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載:「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 ↑ 「長吏」,原脫「吏」字,聚珍本同,今據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後漢紀》卷八所載光武帝遺詔增補。
- ↑ 「原陵」,《通鑑》卷四四胡三省注云:「帝王紀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注》:「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 ↑ 「或幽而光」,此條《文選》卷四三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李善注、卷四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玉海》卷四六亦引,文字全同。《書鈔》卷四引「炎精布耀」四字,《文選》卷五〇范曄《後漢書·光武紀》贊李善注引「漢以炎精布曜」六字,《書鈔》卷三引「或幽而光」四字。按此條文字出自東觀漢記光武帝紀序,《文選》卷一一、卷四六、卷五〇和《玉海》卷四六於此條文字前皆冠有「東觀漢記序」五字。
- ↑ 「傳榮」,此二字有誤,無從校正。
- ↑ 「身在行伍」,此條文字從內容上看,似為光武帝紀序中語。
- ↑ 「天然之姿」,此四字《書鈔》卷五亦引。
- ↑ 「龍舉雲興」,此四字《書鈔》卷一三亦引。
- ↑ 「蕩蕩人無能名焉」,此條文字從內容上看,當是光武帝紀序中語。
- ↑ 「廣開束手之路」,此條文字不見范曄《後漢書》、《後漢紀》,年代不可確考,姑繫於篇末。以下各條文字情況相同。
- ↑ 「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聚珍本注云:「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
- ↑ 「故皆保全」,此條文字聚珍本有,不知輯自何書。
- ↑ 「新野主」,原誤作「新野王」,聚珍本不誤,今據改。「吳侯」,當作「吳房侯」。范曄《後漢書·鄧晨傳》云:「晨初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及三女皆遇害。……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李賢注:「吳房,今豫州縣也。」
- ↑ 「周均為富波侯」,聚珍本注云:「封均事范書不載。」
- ↑ 「外祖樊重為壽張侯」,范曄《後漢書·樊宏傳》云:「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 ↑ 「重子丹為射陽侯」,封於建武十三年,見范曄《後漢書·樊宏傳》。
- ↑ 「孫茂為平望侯」。封於建武二十七年,見范曄《後漢書·樊宏傳》。
- ↑ 「尋玄鄉侯」,原誤作「彝鄉侯」,今據聚珍本校改。據范曄《後漢書·樊宏傳》,尋於建武十三年封玄鄉侯。
- ↑ 「從子沖更父侯」,「沖」字范曄《後漢書·樊宏傳》作「忠」。沖封更父侯在建武十三年,見范書。
- ↑ 「后父陰睦宣恩侯」,「睦」字原誤作「隆」,「恩」字原誤作「陽」,今據聚珍本改。《書鈔》卷四七引東觀漢記云:「建武三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睦,皇后父也。」聚珍本陰睦傳「三年」作「二年」。范曄《後漢書·光烈陰皇后紀》載,建武九年,下詔「追爵謚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陸即睦。
- ↑ 「子識原鹿侯」,封於建武十五年,見范曄《後漢書·陰識傳》。
- ↑ 「就為信陽侯」,范曄《後漢書·陰興傳》云:「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李賢注:「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信陽」與「新陽」,二者未知孰是。范書《虞延傳》、《樂恢傳》,《井丹傳》、《吳良傳》皆稱「信陽侯陰就」,馮衍傳、朱暉傳稱「新陽侯陰就」。
- ↑ 「來歙征羌侯」,范曄《後漢書·來歙傳》云:建武十一年,歙遇刺亡,帝「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
- ↑ 「弟由宜西侯」,「西」字下聚珍本有「鄉」字。范曄《後漢書·來歙傳》云:「建武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 ↑ 「寧平公主」,李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李雄」,李通少子。范曄《後漢書·李通傳》載雄封召陵侯,未言具體年月。
- ↑ 「后父郭昌為陽安侯」,追封於建武二十六年,見范曄《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
- ↑ 「流綿曼侯」,范曄《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作「況綿蠻侯」。流之封在建武二年。
- ↑ 「兄子竟新郪侯」,范曄《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云:建武十七年,「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為新郪侯」。
- ↑ 「匡發干侯」,范曄《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云:建武十七年,「竟弟匡為發干侯」。
- ↑ 「馮邯為鍾離侯」,不見范曄《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