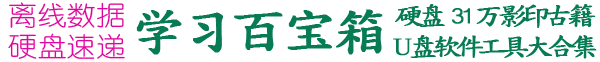在线文库
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敕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核議予謚入祠,以昭軫慰。其建文諸臣之死事者,並命甄議。茲大學士等議上錄其生平大節表著者,予以專謚;餘則通謚為「忠烈」、「忠節」,次則通謚為「烈愍」、「節愍」,統計一千六百餘人。若諸生、韋布未通仕籍及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流,則入祀所在忠義祠,統計又二千餘人,各為一冊進。覽之,均為允協。因名之曰《勝朝殉節諸臣錄》;冠以所頒諭旨,附載廷臣議疏,匯刊頒行,俾天下後世讀史者有所考質。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迥非漢、唐、宋所可及。錄而旌之,亦累朝所未舉行;似亦足以褒顯忠貞,風勵臣節。固不必如張若溎所請之遍行查訪,徒滋紛擾,致無了期。且即再入數千人,於表章大義亦無所增減。廷臣駁議惟韙,亦並載之。爰題詩簡端,用示大意。
}}
信史由來貴癉彰,勝朝殉節與膻薌。
五常萬古既雲樹,潛德幽光允賴揚。
等度早傳遼及宋,後先直邁漢和唐。
{{~|諸臣泉壤應相慶,舍死初心久乃償。
宋李若水從欽宗至金營不屈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尚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自兩都而下,閩也、浙也、粵與滇黔也,凡所盡難諸臣、諸士民、婦女,搜羅廣列,統予謚祀;且上逮建文革除諸忠。闓澤遐敷,重淵胥被矣。伏讀是錄卷端弁列御製詩並序,仰見純廟於易代而下之孤忠遺烈,軫恤至深。宸翰褒加,實為之三致意焉。其「四庫全書提要」及「議疏」二則與史事有涉,茲悉轃附。謹載跋。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勝朝殉節諸臣錄》,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
明自萬曆以還,朝綱日紊,中原瓦解。景命潛移,我國家肇造丕基,龍興東土;王師順動,望若雲霓。而當時守土諸臣各為其主,往往殞身碎首,喋血危疆。逮乎掃蕩妖氛,宅中定鼎,乾坤再造,陬澨咸歸。而故老遺臣猶思以螳臂當車,致煩齊斧:載諸史冊,一一可稽。我皇上幾餘覽古,軫惻遺忠。念其冒刃攖鋒,雖屬不知天運;而疾風勁草,百折不移,要為死不忘君,無慚臣節。用加贈典,以勵綱常。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於廷,俾各以原官錫之新謚。蓋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一也。至於崇禎之季,銅馬縱橫,或百戰捐生、或孤城效死;雖將傾之廈,一木難支,而毅魄英魂自足千古。自范景文等二十餘人已蒙世祖章皇帝易名賜祭、炳耀丹青外,其縶馬埋輪、沉淵伏劍在甲申三月以前者,並命博徵載籍,詳錄芳蹤。若夫壬午「革除傳疑行遯致身」一案,見聞雖有異詞,抗節諸臣生死要為定據;亦詳為甄錄,進慰忠魂。大抵以欽定《明史》為主,而參以官修《大清一統志》、各省通志諸書,皆臚列姓名,考證事跡,勒為一編。凡立身始末卓然可傳,而又取義成仁、搘拄名教者,各予專謚,共三十三人。若平生無大表見,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匯為通謚:其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於官微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謚者,並祀於所在忠義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如楊維垣等失身閹黨,一死僅足自贖者,則不濫登焉。書成,命以《勝朝殉節諸臣錄》為名;並新制宸章弁諸簡首,宣付武英殿刊刻頒行,以垂示久遠。
臣等竊惟自古代嬗之際,其致身故國者,每多蒙以惡名,故鄭樵謂「《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毌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沉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見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間即有追加褒贈,如唐太宗之於姚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人而止。誠自書契以來,未有天地為心、渾融彼我,闡明風教、培植彞倫,不以異代而歧視如我皇上者。臣等恭繹詔旨,仰見權衡予奪,袞鉞昭然。不獨勁節孤忠咸邀渥澤,而明昭彰癉,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義,亦炳若日星。敬讀是編,彌凜然於皇極之彞訓矣。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殉節錄議毓
大學士臣舒赫德、臣于敏中等謹奏:奏為遵旨一並議奏事。
左都御史張若溎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明季殉節事跡」一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此折並著大學士九卿等一並議奏。欽此。』欽遵。據稱:『竊聞定稿衙門以《明史》及各省《通志》為斷,其說是矣。然《明史》、《通志》固本朝纂修之書,抗志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行,方且指為不順;孰敢大書、特書以志不朽。然則欲專求之於《明史》、《通志》,除峻秩顯官有關大局者之外,其餘人等,臣疑其不能多睹。請先就《明史》、《通志》查考編次進呈,並請行文直省各督撫再加採訪,務期確實不爽、文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跡;限其半年之內,陸續具奏。臣等詳加考核,取其信而有徵者編纂成書』等語。
臣等伏查明季殉節諸臣,蒙我皇上錫謚褒忠;臣等承命集議,謹遵原奉諭旨就《明史》及《輯覽》所載,詳加摘錄。又思歷經官修之《大清一統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義例較寬,所收均為詳信;亦應酌加參考,用廣搜羅。至一切野乘、裨官,誠以其傳述多訛,未敢概為援引。今該左都御史以《明史》、《通志》所載無多,請行各督撫再加採訪;固亦推廣聖仁,闡幽顯微至意。臣等恭繹欽定《明史》一書,原系仰稟睿裁,筆削公正。凡與本朝交涉事跡,莫不詳確紀載,毫無忌諱。故上自遼東死事諸人,下及福、唐、桂諸王臣子之阻兵抗命者,悉皆編入「列傳」,大書特書。不特顯秩崇班各詳本末,即於子衿、韋布亦一一附著其姓名。方策具存,無難考見。臣等現在核辦各項,本於《明史》者實什之七、八,並未有如該左都御史所云不能多睹,以致埋沒疏虞之處。至如文集、說部等類,原非謂其一無可據。然如李國楨誤國辱身,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足見野史之冒濫難憑;又如吳繼善降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乃稱其大罵捐軀,更見私集之阿諛難據。是以從前修史時,間加刊削,實有不得不從嚴慎者。今臣等辦理謚典,擬於《明史》以外兼及志書,裒輯已廣;故專謚、通謚至有一千五、六百人。聖澤覃施,極為周溥。若因其間尚有遺佚,復令督撫採訪增加,則自今上距國朝定鼎百有餘年,正史既不載其名、故老又無從詢問,文獻並不足徵;而僅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所考核以辨其誣信。轉恐真偽混淆,毋裨彰癉。況天下之忠義一也,我皇上褒崇節烈、獎恤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世。此不獨身被易名之典者,共蒙優渥殊恩;即或當日傳聞闕略,間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不正氣咸伸,漏泉同感。又何必勒限行查,徒滋紛擾。應該將左都御史所奏之處毋庸議。
除謚典各條款已另行擬議具奏外,臣等謹遵旨將此折一並會議。是否有當?伏候訓示遵行。謹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