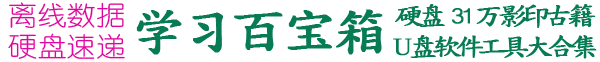在线文库
文集
自序
余之研究哲學始于辛壬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於其人生哲學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後漸覺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于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于客觀的知識。此意于《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今歲之春復返而讀汗德之書,嗣今以後將此數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進,取前說而讀之亦一快也,故并諸雜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云爾
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海甯王國維自序
論性
今吾人對一事物,雖互相反對之議論皆得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則其事物必非吾人所能知者也。「二加二為四。」,「二點之間隻可引一直線。」,無論何人,未有能反對之者也。因果之相嬗,質力之不滅,無論何人,未有能反對之者也。數學及物理學之所以為最確實之知識者,豈不以此矣乎?今孟子之言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二者皆互相反對之說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然則吾人之於人性,固有不可知者在歟?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命者,固非無故歟?且於人性論中不但得容反對之說而已,於一人之說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誰歟?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人為)也”,然所以能偽者何故歟?汗德曰“道德之於人心,無上之命令也”,何以未幾而又有根惡之說歟?叔本華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謂拒絕生活之欲者,又何自來歟?古今東西之論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使性之為物,如數及空間之性質,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確,而其言之也無不同,則吾人雖昌言有論人性之權利,可也。試問吾人果有此權利否乎?今論人性者之反對矛盾如此,則性之為物固不能不視為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今夫吾人之所可得而知者,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也。先天的知識如空間、時間之形式,及悟性之範疇,此不待經驗而生,而經驗之所由以成立者,自汗德之知識論出後,今日殆為定論矣。後天的知識乃經驗上之所教我者,凡一切可以經驗之物皆是也。二者之知識,皆有確實性,但前者有普遍性及必然性,後者則不然。然其確實,則無以異也。今試問性之為物,果得從先天中或後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識之形式而不及於知識之材質。而性固一知識之材質也,若謂於後天中知之,則所知者又非性何?則吾人經驗上所知之性,其受遺傳與外部之影響者不少,則其非性之本來面目,固已久矣。故斷言之曰“性之為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既如斯矣,於是欲論人性者,非馳於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夫經驗上之所謂性,固非性之本然,苟執經驗上之性以為性,則必先有善惡二元論起焉。何則?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反對之事實而非相對之事實也。相對之事實,如寒熱厚薄等是,大熱曰熱,小熱曰寒,大厚曰厚,稍厚曰薄。善惡則不然。大善曰善,小善非惡,大惡曰惡,小惡亦非善。又積極之事實而非消極之事實也。有光曰明,無光曰暗,有有曰有,無有曰無。善惡則不然。有善曰善,無善猶非惡,有惡曰惡,無惡猶非善。惟其為反對之事實,故善惡二者不能由其一說明之。唯其為積極之事實,故不能舉其一而遺其他。故從經驗上立論,不得不盤旋於善惡二元論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識,必求其說明之統一,而決不以此善惡二元論為滿足也。於是性善論、性惡論及超絕的一元論(即性無善無不善說及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接武而起。夫立於經驗之上以言性,雖所論者非真性,然尚不至於矛盾也。至超乎經驗之外而求其說明之統一,則雖反對之說,吾人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則?超乎經驗之外,吾人固有言論之自由。然至欲說明經驗上之事實時,則又不得不自圓其說,而複反於二元論。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今略述古人論性之說而暴露其矛盾,世之學者可以觀焉。
我國之言性者古矣。堯之命舜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仲虺之誥湯曰:“唯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乂。”《湯誥》則雲:“惟皇上帝,降哀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唯後。”此二說互相發明,而與霍布士之說若合符節。然人性苟惡而不可以為善,雖聰明之君主亦無以乂之,而聰明之君主亦天之所生也。又苟有善之恒性,則豈待君主之綏乂之乎?然則二者非互相豫想,皆不能持其說。且仲虺之於湯,固所謂見而知之者,不應其說之矛盾如此也。二誥之說,不過舉其一麵,而遺其他麵耳。嗣是以後,人又有唱一元之論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所謂民受大地之中以生者,亦不外《湯誥》之意。至孔子而始唱超絕的一元論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但從經驗上推論之,故以之說明經驗上之事實,自無所矛盾也。
告子本孔子之人性論而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說雖為孟子所駁,然實孔子之真意。所謂湍水者,性相近之說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者,習相遠之說也。孟子雖攻擊之而主性善論,然其說則有未能貫通者。其山木之喻曰:“牛山之木嚐美矣……是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晝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此豈人之情也哉?”然則所謂旦旦伐之者何歟?所謂梏亡之者何歟?無以名之,名之曰“欲”。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然則所謂欲者何自來歟?若自性出,何為而與性相矛盾歟?孟子於是以小體大體說明之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顧以心為天之所與,則耳目二者,獨非天之所與歟?孟子主性善,故不言耳目之欲之出於性,然其意則正如此。故孟子之性論之為二元論,昭然無疑矣。
至荀子反對孟子之說而唱性惡論曰:“禮義法度,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又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政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此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政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人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篇》)。”吾人且進而評其說之矛盾其最顯著者,區別人與聖人為二是也。且夫聖人獨非人也歟哉?常人待聖人出,禮義興,而後出於治,合於善。則夫最初之聖人即製作禮義者,又安所待歟?彼說禮之所由起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禮之所由起也(《禮論篇》)。”則所謂禮義者,亦可由欲推演之。然則胡不曰人惡其亂也,故作禮義以分之,而必曰先王何哉?又其論禮之淵源時,亦含矛盾之說曰:“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性惡篇》)。”然又以三年之喪為稱情,而立文曰:“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親也,至死無窮。故曰說豫娩澤憂患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之發於顏色者也……(《理論篇》)。”此與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所以告夷之者何異?非所謂感於自然不待事而後然者歟?則其非反於性而悖於情明矣。於是荀子性惡之一元論,由自己破滅之。
人性之論,唯盛於儒教之哲學中,至同時之他學派則無之。約而言之,老莊主性善,故崇自然,申韓主性惡,故尚刑名。然在此諸派中並無爭論及之者。至漢而《淮南子》奉老子之說而唱性善論,其言曰:“清淨恬愉,人之性也(《人間訓》)。”故曰:“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鬥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也,則動而惑營。”又曰:“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齊俗訓》)。”於是《淮南子》之性善論與孟子同終破裂,而為性欲二元論。
同時董仲舒亦論人性曰:“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資之謂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米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之所為之內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其論法全似荀子,而其意則與告子同。然董子亦非能久持此超絕的一元論者,夫彼之形而上學,固陰陽二元論也。其言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嗣陽尊陰卑篇》)。”故曰:“天雨有陰陽之施,人亦雨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篇》)。”由此二元論而一麵主性惡之說曰:“民之為言瞑也,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深察名號篇》)?”劉向謂仲舒作書美荀卿,非無據也。然一麵又謂“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王道通三篇》)”。又曰:“陰之行不得於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深察名號篇》)?”夫人受命於天,取仁於天,捐情輟欲,乃合天道,則又近於性善之說。要之,仲舒之說欲調和孟、荀二家,而不免以苟且滅裂終者也。至揚雄出,遂唱性善惡混之二元論。至唐之中葉,倫理學上複提起人性論之問題。韓愈之《原性》,李翱之《複性書》,皆有名於世。愈區別性與情為二翱,雖謂情由性出,而又以為性善而情惡,其根據薄弱,實無足言者。至宋之王安石複紹述告子之說,其《性情論》曰:“性情一也。七情之未發於外而存於心者,性也。七情之發於外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也。故性情一也。”又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無非情。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無非情。情而當於理,則聖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同時蘇軾亦批評韓愈之說而唱超絕的一元論,又下善之界說。其《揚雄論》曰:“性者果泊然而無所為耶?則不當複有善惡之說。苟性之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於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禦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禦之,而之乎惡。由是觀之,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所能有也。且夫言性,又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於性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聖人唯以其一人之所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也(《東坡全集》卷四十七)。”蘇王二子蓋知性之不能賦以善惡之名,故遁而為此超絕的一元論也。綜觀以上之人性論,除董仲舒外,皆就性論性,而不涉於形而上學之問題。至宋代哲學興(蘇王二氏雖宋人,然於周張之思想全不相涉),而各由其形而上學以建設人性論。周子之語最為廣漢,其《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則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又曰:“誠無為,幾善惡(《通書·誠幾德章》)。”幾者動之微,誠者即前所謂太極也。太極動而後有陰陽,人性動而後有善惡。當其未動時,初無善惡之可言。所謂秀而最靈者,以才言之,而非以善惡言之也。此實超絕的一元論,與蘇氏所謂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所能有者無異。然周子又謂“誠者,聖人之本,純粹至善者也(《通書·誠上》)”。然人之本體既善,則其動也,何以有善惡之區別乎?周子未嚐說明之。故其性善之論,實由其樂天之性質與尊崇道德之念出,而非有名學上必然之根據也。
橫渠張子亦由其形而上學而演繹人性論,其言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正蒙·太和篇》)。”即謂人之性與太虛同體,善惡之名無自而加之。此張子之本意也。又曰:“氣本之虛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同《太和篇》)。”此即海額爾之辨證法,所謂由正生反,由反生合者也。象者,海氏之所謂正對者,反也。和解者,正反之合也。故曰:“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同《太和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所不性焉(同《誠明篇》)”。又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同上)。”由是觀之,彼於形而上學立太虛之一元,而於其發現也,分為形神之二元。善出於神,惡出於形,而形又出於神,合於神。故二者之中,神其本體,而形其客形也。故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同《參兩篇》)。”然形既從神出,則氣質之性何以與天地之性相反歟?又氣質之性何以不得謂之性歟?此又張子所不能說明也。
至明道程子之說曰:“生生之謂易,此天之所以為道也。天隻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隻是善,便有一個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二程全書》卷二)。”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同上)。”由是觀之,明道之所謂性,兼氣而言之。其所謂善,乃生生之意,即廣義之善,而非孟子所謂性善之善也。故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有自幼而惡,有自幼而善,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二程全書》卷二)。”按,明道於此語意未明。蓋既以生為性,而性中非有善惡二者相對,則當雲善固出於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出於性。又當雲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善惡。才說善惡,便不是性。然明道不敢反對孟子,故為此曖昧之語,然其真意則正與告子同。然明道他日又混視廣義之善與狹義之善,而反覆性善之說,故明道之性論於宋儒中最為薄弱者也。
至伊川糾正明道之說,分性與氣為二而唱性善論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近思錄·道體類》)。”又曰:“性無不善,而有善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二程全書》卷十九)。”蓋欲主張性善之說,則氣質之性之易趨於惡,此說之一大障礙也。於是非置氣於性之外,則不能持其說。故伊川之說離氣而言性,則得持其性善之一元論,若置氣於性中,則純然空間的善惡二元論也。
朱子繼伊川之說,而主張理氣之二元論。其形而上學之見解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學的上》)。”又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語類一》)。”而此理伊川已言之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性理會通》卷二十六)。”但於人性上伊川所目為氣者,朱子直謂之性。即性之純乎理者,謂之天地之性,其雜乎氣者,謂之氣質之性,而二者又非可離而為二也。故曰:“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語類》卷四)。”又曰:“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學的上》)。”而性如水,然氣則盛水之器也。故曰:“水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淤泥之器盛之則濁(《語類》卷四)。”故由朱子之說,理無不善,而氣則有善有不善。故朱子之性論與伊川同,不得不謂之二元論也。
朱子又自其理氣二元論,而演繹其理欲二元論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個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性理會通》卷五十)。”象山陸子起而駁之曰:“天理人欲之分,語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動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全集》三十五)?”又駁人心道心之說曰:“心一也,安得有二心(《全集》三十四)?”此全立於告子之地位,而為超絕的一元論也。然此非象山之真意,象山固絕對的性善論者也。其告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全集》三十四)。”故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同三十二)。”然試問人之所以遷於物者如何?象山亦歸之於氣質曰:“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同上)。”故陸子之意與伊川同別氣於性,而以性為善。若合性與氣而言之,則亦為二元論。陽明王子亦承象山之說而言性善,然以格去物欲為致良知之第一大事業。故古今之持性善論而不蹈於孟子之矛盾者,殆未之有也。
嗚呼!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自生民以來至於今,世界之事變,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鬥乎?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孰非由此而起乎?故世界之宗教,無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蠻之神雖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二種,即有愛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與惡神是已。至文明國之宗教,於上帝之外,其不豫想惡魔者殆稀也。在印度之婆羅門教,則造世界之神謂之梵天Brahma,維持世界者謂之吠舍那Aishnu,而破壞之者謂之濕婆Siva,以為今日乃濕婆之治世,梵天與吠舍那之治世已過去矣。其後乃有三位一體之說。此則猶論理學之由二元論而變為超絕的一元論也。迤印度以西,則波斯之火教立阿爾穆茲Ormuzd與阿利曼Ahriman之二神。阿爾穆茲,善神也,光明之神也,平和之神也。阿利曼則主惡與暗黑及爭鬥。猶太教之耶和華Jehovah與撒旦Satan,實自此出者也。希臘神語中之亞波羅Apolo與地哇尼速斯Dionysus之關係,亦頗似之。嗣是以後,基督教之理知派亦承此思想,謂世界萬物之形式為神,而其物質則墮落之魔鬼也。暗黑且惡之魔鬼,與光明且善之神相對抗,而各欲加其勢力於人現在之世界,即神與魔鬼之戰地也。夫所謂神者,非吾人善性之寫象乎?所謂魔鬼者,非吾人惡性之小影乎?他如猶太、基督二教之墮落之說,佛教及基督教之懺悔之說,皆示善惡二性之爭鬥。蓋人性苟善,則墮落之說為妄。既惡矣,又安知墮落之為惡乎?善則無事於懺悔,惡而知所以懺悔,則其善端之存在,又不可誣也。夫豈獨宗教而已,曆史之所紀述,詩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鬥乎?但前者主紀外界之爭,後者主述內界之爭,過此以往,則吾不知其區別也。吾人之經驗上善惡二性之相對立如此,故由經驗以推論人性者,雖不知與性果有當與否,然尚不與經驗相矛盾,故得而持其說也。超絕的一元論,亦務與經驗上之事實相調和,故亦不見有顯著之矛盾。至執性善、性惡之一元論者,當其就性言性時,以性為吾人不可經驗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說。然欲以之說明經驗,或應用於修身之事業,則矛盾即隨之而起。餘故表而出之,使後之學者勿徒為此無益之議論也。
釋理
昔阮文達公作《塔性說》,謂翻譯者但用典中“性”字以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力言翻譯者遇一新義為古語中所無者,必新造一字,而不得襲用似是而非之古語。是固然矣,然文義之變遷,豈獨在輸入外國新義之後哉?吾人對種種之事物而發見其公共之處,遂抽象之而為一概念,又從而命之以名,用之既久,遂視此概念為一特別之事物,而忘其所從出。如理之概念,即其一也。吾國語中“理”字之意義之變化,與西洋“理”字之意義之變化,若出一轍。今略述之如左:
- (一)理字之語源。《說文解字》第一篇:“理,治玉也,從玉里聲。”段氏玉裁注:“《戰國策》‘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是理為剖析也。”由此類推,而種種分析作用皆得謂之曰“理”。鄭玄《樂記》注:“理者,分也。”《中庸》所謂“文理密察”,即指此作用也。由此而分析作用之對象,即物之可分析而粲然有係統者,亦皆謂之理。《逸論語》曰:“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此從理之本義之動詞而變為名詞者也,更推之而言他物,則曰地理(《易·係詞傳》)、曰腠理(《韓非子》)、曰色理、曰蠶理、曰箴理(《荀子》),就一切物而言之曰條理(《孟子》)。然則所謂理者,不過謂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之可分析者而已矣。
其在西洋各國語中,則英語之Reason,與我國今日“理”字之義大略相同,而與法國語之Raison,其語源同出於拉丁語之Ratio,此語又自動詞Retus(思索之意)而變為名詞者也。英語又謂推理之能力曰Discourse,同時又用為言語之義。此又與意大利語之Discorso同出於拉丁語之Discursus,與希臘語之Logos,皆有言語及理性之兩義者也。其在德意志語,則其表理性也曰Vernunft,此由Vernehmen之語出。此語非但聽字之抽象名詞,而實謂知言語所傳之思想者也。由此觀之,古代二大國語及近世三大國語,皆以思索(分合概念之力)之能力及言語之能力,即他動物之所無,而為人類之獨有者,謂之曰理性 Logos(希)、Ratio(拉)、Vernunft(德)、Raison(法)、Reason(英)。而從吾人理性之思索之徑路,則下一判斷,必不可無其理由,於是拉丁語之Ratio、法語之Raison、英語之Reason等,於理性外又有理由之意義。至德語之Vernunft,則但指理性,而理由則別以Grunde之語表之。吾國之理字,其義則與前者為近,兼有理性與理由之二義。於是理之解釋,不得不分為廣義的及狹義的二種。
- (二)理之廣義的解釋。理之廣義的解釋,即所謂理由是也。天下之物,絕無無理由而存在者。其存在也,必有所以存在之故。此即物之充足理由也。在知識界,則既有所與之前提,必有所與之結論隨之。在自然界,則既有所與之原因,必有所與之結果隨之。然吾人若就外界之認識而皆以判斷表之,則一切自然界中之原因即知識上之前提,一切結果即其結論也。若視知識為自然之一部,則前提與結論之關係,亦得視為因果律之一種。故歐洲上古及中世之哲學,皆不區別此二者,而視為一物。至近世之拉衣白尼誌始分晰之,而總名之曰“充足理由之原則”,於其《單子論》之小詩中括之為公式曰:“由此原則,則苟無必然或不得不然之充足理由,則一切事實不能存在,而一切判斷不能成立。”汗德亦從其說,而立形式的原則與物質的原則之區別。前者之公式曰“一切命題必有其論據”,後者之公式曰“一切事物必有其原因”。其學派中之克珊範台爾更明言之曰:“知識上之理由(論據)必不可與事實上之理由(原因)相混。前者屬名學,後者屬形而上學。前者思想之根本原則,後者經驗之根本原則也。原因對實物而言,論據則專就吾人之表象言之。”至叔本華而複就充足理由之原則為深邃之研究曰“此原則就客觀上言之,為世界普遍之法則。就主觀上言之,乃吾人之知力普遍之形式也。世界各事物無不入此形式者,而此形式可分為四種:一,名學上之形式。即從知識之根據之原則者曰,既有前提,必有結論。二,物理學上之形式。即從變化之根據之原則者曰,既有原因,必有結果。三,數學上之形式。此從實在之根據之原則者曰,一切關係由幾何學上之定理定之者,其計算之成績不能有誤。四,實踐上之形式。曰動機既現,則人類及動物不能不應其固有之氣質,而為惟一之動作。此四者,總名之曰充足理由之原則”。此四分法中,第四種得列諸第二種之形式之下,但前者就內界之經驗言之,後者就外界之經驗言之,此其所以異也。要知第一種之充足理由之原則乃吾人理性之形式,第二種悟性之形式,第三種感性之形式也。此三種之公共之性質,在就一切事物而證明其所以然及其不得不然。即吾人就所與之結局觀之,必有其所以然之理由,就所與之理由觀之,必有不得不然之結局。此世界中最普遍之法則也。而此原則所以為世界最普遍之法則者,則以其為吾人之知力之最普遍之形式。故陳北溪(淳)曰“理有確然不易的意”,臨川吳氏(澄)曰“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征之吾人日日之用語,所謂“萬萬無此理”,“理不應爾”者,皆指理由而言也。
- (三)理之狹義的解釋。理之廣義的解釋外,又有狹義的解釋,即所謂理性是也。夫吾人之知識分為二種,一直觀的知識,一概念的知識也。直觀的知識,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識,則理性之作用也。直觀的知識,人與動物共之。概念之知識,則惟人類所獨有,古人所以稱人類為理性的動物或合理的動物者,為此故也。人之所以異於動物,而其勢力與憂患且百倍之者,全由於此。動物生活於現在,人則亦生活於過去及未來。動物但求償其一時之欲,人則為十年百年之計。動物之動作,由一時之感覺決定之,人之動作,則決之於抽象的概念。夫然,故彼之動作從豫定之計畫,而不為外界所動,不為一時之利害所搖。彼張目斂手,而為死後之豫備。彼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地,而持之以歸於邱墓。且對種種之動機而選擇之者,亦惟人為能。何則?吾人惟有概念的知識,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先使一切遠近之動機表之以概念,而悉現於意識,然後吾人得遞驗其力之強弱,而擇其強者而從之。動物則不然。彼等所能覺者,現在之印象耳。惟現在之苦痛之恐怖心,足以束縛其情欲。逮此恐怖心久,而成為習慣,遂永遠決定其行為,謂之曰“馴擾”。故感與覺,人與物之所同,思與知,則人之所獨也。動物以振動表其感情及性質,人則以言語傳其思想,或以言語揜蓋之。故言語者,乃理性第一之產物,亦其必要之器官也。此希臘及意大利語中所以以一語表理性及言語者也。此人類特別之知力,通古今東西,皆謂之曰“理性”即指吾人自直觀之觀念中造抽象之概念,及分合概念之作用。自希臘之柏拉圖、雅裏大德勒至近世之洛克、拉衣白尼誌,皆同此意。其始混用之者,則汗德也。汗德以理性之批評為其哲學上之最大事業,而其對理性之概念,則有甚曖昧者。彼首分理性為純粹及實踐二種純粹理性指知力之全體,殆與知性之意義無異。彼於《純粹理性批評》之《緒論》中曰:“理性者,吾人知先天的原理的能力是也。”實踐理性則謂合理的意誌之自律。自是“理性”二字始有特別之意義。而其所謂純粹理性中,又有狹義之理性。其下狹義理性之定義也,亦互相矛盾。彼於理性與悟性之別實不能深知,故於《先天辨證論》中曰:“理性者,吾人推理之能力(《純理批評》第五版三百八十六頁)。”又曰:“單純判斷,則悟性之所為也(同九十四頁)。”叔本華於《汗德哲學之批評》中曰“由汗德之意,謂若有一判斷而有經驗的、先天的,或超名學的根據,則其判斷乃悟性之所為。如其根據而為名學的,如名學上之推理式等,則理性之所為也”。此外尚有種種之定義,其義各不同。其對悟性也亦然。要之,汗德以通常所謂理性者謂之悟性,而與理性以特別之意義,謂吾人於空間及時間中結合感覺以成直觀者,感性之事;而結合直觀而為自然界之經驗者,悟性之事;至結合經驗之判斷以為形而上學之知識者,理性之事也。自此特別之解釋,而汗德以後之哲學家遂以理性為吾人超感覺之能力,而能直知本體之世界及其關係者也。特如希哀林、海額爾之徒,乘雲馭風而組織理性之係統。然於吾人之知力中果有此能力否?本體之世界果能由此能力知之否?均非所問也。至叔本華出,始嚴立悟性與理性之區別。彼於《充足理由之論文》中證明直觀中已有悟性之作用存。吾人有悟性之作用,斯有直觀之世界。有理性之作用,而始有概念之世界。故所謂理性者,不過製造概念及分合之之作用而已。由此作用,吾人之事業已足以遠勝於動物。至超感覺之能力,則吾人所未嚐經驗也。彼於其《意誌及觀念之世界》及《充足理由之論文》中辨之累千萬言,然後“理性之概念”燦然複明於世。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程子曰:“性即理也。”其對理之概念,雖於名學的價值外,更賦以倫理學的價值,然就其視理為心之作用時觀之,固指理性而言者也。
- (四)理之客觀的假定。由上文觀之,理之解釋有廣狹二義。廣義之理是為理由,狹義之理則理性也。充足理由之原則為吾人知力之普遍之形式,理性則知力作用之一種,故二者皆主觀的,而非客觀的也。然古代心理上之分析未明,往往視理為客觀上之物,即以為離吾人之知力而獨立,而有絕對的實在性者也。如希臘古代之額拉吉來圖謂天下之物無不生滅變化,獨生滅循環之法則,乃永遠不變者,額氏謂之曰天運,曰天秩,又曰天理Logos。至斯多噶派更紹述此思想,而以指宇宙之本體,謂生產宇宙及構造宇宙之神。即普遍之理也,一麵生宇宙之實質,而一麵賦以形式。故神者,自其有機的作用言之,則謂之創造及指導之理;自其對個物言之,則謂之統轄一切之命;自其以普遍決定特別言之,則謂之序;自其有必然性言之,則謂之運。近世希臘哲學史家災爾列爾之言曰“由斯多噶派之意,則所謂天心、天理、天命、天運、天然、天則,皆一物也。故其所謂理,兼有理、法、命、運四義,與額拉吉來圖同。但於開辟論之意義外,兼有實體論之意義,此其相異者也”。希臘末期之斐洛與近世之初之馬爾白蘭休,亦皆有此“理即神也”之思想。此理之自主觀的意義而變為客觀的意義者也。更返而觀吾中國之哲學,則理之有客觀的意義,實自宋人始。《易·說卦傳》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固以理為性中之物。孟子亦既明言理為心之所同然矣。而程子則曰“在物為理”,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原之為心為物,程子不言,至朱子直言之曰:“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至萬物之有理,存於人心之有知,此種思想固朱子所未嚐夢見也。於是理之淵源,不得求諸外物。於是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又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於是對周子之太極而與以內容曰“太極不過一個理字”。萬物之理皆自此客觀的大理出,故曰“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又《語類》雲:“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故朱子之所謂理,與希臘斯多噶派之所謂理,皆預想一客觀的理存於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過其一部分而已。於是理之概念,自物理學上之意義出,至宋以後而遂得形而上學之意義。
- (五)理之主觀的性質。如上所述,理者,主觀上之物也,故對朱子之實在論,而有所謂觀念論者起焉。夫孟子既以理為心之所同,然至王文成則明說之曰:“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我國人之說理者,未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也。其在西洋,則額拉吉來圖及斯多噶派之理說,固為今日學者所不道,即充足理由原則之一種,即所謂因果律者,自雅裏大德勒之範疇說以來,久視為客觀上之原則。然希臘之懷疑派駁之於先,休蒙論之於後,至汗德、叔本華,而因果律之有主觀的性質,遂為不可動之定論。休蒙謂因果之關係,吾人不能直觀之,又不能證明之者也。凡吾人之五官所得直觀者,乃時間上之關係,即一事物之續他事物而起之事實是也。吾人解此連續之事物,為因果之關係。此但存於吾人之思索中,而不存於事物。何則?吾人於原因之觀念中,不能從名學上之法則而演繹結果之觀念,又結果之觀念中,亦不含原因之觀念,故因果之關係,決非分析所能得也。其所以有因果之觀念者,實由觀念聯合之法則而生,即由觀念之互相連續者屢反複於吾心,於是吾人始感其間有必然之關係,遂疑此關係亦存於客觀上之外物。易言以明之,即自主觀上之必然的關係,轉而視為客觀上之必然的關係,此因果之觀念之所由起也。汗德力拒此說,而以困果律為悟性先天之範疇,而非得於觀念聯合之習慣,然謂宇宙不能賦吾心以法則,而吾心實與宇宙以法則,則其視此律為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實與休蒙同也。此說至叔本華而更精密證明之。叔氏謂吾人直觀時,已有悟性(即自果推因之作用)之作用行乎其間。當一物之呈於吾前也,吾人所直接感之者,五官中之感覺耳。由此主觀上之感覺,進而求其因於客觀上之外物,於是感覺遂變而為直觀,此因果律之最初之作用也。由此主觀與客觀間之因果之關係,而視客觀上之外物,其間亦皆有因果之關係,此於先天中預定之者也。而此先天中之所預定所以能於後天中證明之者,則以此因果律乃吾人悟性之形式,而物之現於後天中者,無不入此形式。故其《充足理由論文》之所陳述,實較之汗德之說更為精密完備也。夫以充足理由原則中之因果律,即事實上之理由猶全屬吾人主觀之作用,況知識上之理由及吾人知力之一種之理性乎?要之,以理為有形而上學之意義者,與《周易》及畢達哥拉斯派以數為有形而上學之意義同,自今日視之,不過一幻影而已矣。
由是觀之,則所謂理者,不過理性、理由二義,而二者皆主觀上之物也。然則古今東西之言理者,何以附以客觀的意義乎?曰“此亦有所自”。蓋人類以有概念之知識,故有動物所不能者之利益,而亦陷於動物不能陷之誤謬。夫動物所知者,個物耳。就個物之觀念,但有全偏明昧之別,而無正誤之別。人則以有概念,故從此犬彼馬之個物之觀念中抽象之,而得“犬”與“馬”之觀念。更從犬馬牛羊及一切跂行喙息之觀念中抽象之,而得“動物”之觀念。更合之植物、礦物而得“物”之觀念。夫所謂物,皆有形質可衡量者也。而此外尚有不可衡量之精神作用,而人之抽象力進而不已必求一語以賅括之,無以名之,強名之曰“有”。然離心與物之外,非別有所謂“有”也。離動植、礦物以外,非別有所謂“物”也。離犬馬牛羊及一切跂行喙息之屬外,非別有所謂“動物”也。離此犬彼馬之外,非別有所謂“犬”與“馬”也。所謂馬者,非此馬即彼馬,非白馬即黃馬、驪馬。如謂個物之外,別有所謂馬者,非此非彼非黃非驪非他色,而但有馬之公共之性質,此亦三尺童子之所不能信也。故所謂“馬”者,非實物也,概念而已矣。而概念之不甚普遍者,其離實物也不遠,故其生誤解也不多。至最普遍之概念,其初固亦自實物抽象而得,逮用之既久,遂忘其所自出,而視為表特別之一物,如上所述“有”之概念是也。夫離心物二界別無所謂“有”,然古今東西之哲學往往以“有”為有一種之實在性。在我中國則謂之曰太極曰玄曰道,在西洋則謂之曰神。及傳衍愈久,遂以為一自證之事實,而若無待根究者,此正柏庚所謂種落之偶像,汗德所謂先天之幻影。人而不求真理則已,人而唯真理之是求,則此等謬誤,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之也。理之概念,亦豈異於此?其在中國語中,初不過自物之可分析而有係統者抽象而得此概念,輾轉相借,而遂成朱子之理即太極說。其在西洋,本但有理由及理性之二義,輾轉相借,而前者生斯多噶派之宇宙大理說,後者生汗德以降之超感的理性說。所謂由燈而之槃,由燭而之鑰,其去理之本義固已遠矣。此無他,以理之一語為不能直觀之概念,故種種誤謬得附此而生也。而所謂太極,所謂宇宙、大理,所謂超感的理性,不能別作一字,而必借理字以表之者,則又足以證此等觀念之不存於直觀之世界,而惟寄生於廣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過一幻影而已矣。故為之考其語源並其變遷之跡,且辨其性質之為主觀的而非客觀的,世之好學深思之君子,其亦有取於此歟?
由上文觀之,則理之意義,以理由而言,為吾人知識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則為吾人構造概念及定概念間之關係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種也。故理之為物,但有主觀的意義,而無客觀的意義。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學上之意義,而無形而上學上之意義也。然以理性之作用為吾人知力作用中之最高者,又為動物之所無,而人之所獨有,於是但有心理學上之意義者,於前所述形而上學之意義外,又有倫理學上之意義。
此又中外倫理學之所同,而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之者也。理之有倫理學上之意義,自《樂記》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天理對人欲而言,確有倫理上之意義。然則所謂天理,果何物歟?案《樂記》之意,與孟子小體大體之說極相似。今援孟子之說以解之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由此觀之,人所以引於物者,乃由不思之故,而思(定概念之關係)者正理性之作用也。然則《樂記》之所謂天理,固指理性言之。然理性者,知力之一種,故理性之作用,但關於真偽,而不關於善惡。然在古代,真與善之二概念之不相區別,故無足怪也。至宋以降,而理欲二者遂為倫理學上反對之二大概念。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蔽於人欲,則亡天理矣。”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於是理之一字於形而上學之價值(實在)外,兼有倫理學上之價值(善),其間惟朱子與國朝婺源戴氏之說頗有可味者。朱子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個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又曰:“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麵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戴東原氏之意與朱子同,而顛倒其次序而言之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又曰:“天理雲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朱子所謂“安頓得好”與戴氏所謂“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者,則其視理也,殆以“義”字“正”字“恕”字解之。於是理之一語,又有倫理學上之價值。其所異者,惟朱子以理為人所本有而安頓之不恰好者,則謂之欲,戴氏以欲為人所本有,而安頓之使無爽失者理也。
其在西洋之倫理學中亦然。柏拉圖分人性為三品:一曰嗜欲,二曰血氣,三曰理性。而以節製嗜欲與血氣而成克己與勇毅二德為理性之任,謂理性者,知識與道德所稅駕之地也。厥後斯多噶派亦以人性有理性及感性之二元質,而德之為物,隻在依理而克欲,故理性之語,亦大染倫理學之色彩。至近世汗德而遂有實踐理性之說。叔本華於其《汗德哲學批評》中極論之曰汗德以愛建築上之配偶,故其說純粹理性也,必求其匹偶。而說實踐理性,而雅裏大德勒之Nous praktikos與煩瑣哲學之Intellectus practicus(皆實踐知力之義)二語,已為此語之先導,然其意與二者大異。彼以理性為人類動作之倫理的價值之所由生,謂一切人之德性及高尚神聖之行,皆由此出,而無待於其他。故由彼之意,則合理之動作與高尚神聖之動作為一,而私利慘酷卑陋之動作,但不合理之動作而已。然不問時之古今,地之東西,一切國語皆區別此二語(理性與德性)。即在今日,除少數之德意誌學者社會外,全世界之人猶執此區別。夫歐洲全土所視為一切德性之模範者,非基督教之開祖之生活乎?如謂彼之生活為人類最合理之生活,彼之教訓示人以合理的生活之道則,人未有不議其大不敬者也。今有人焉,從基督之教訓而不計自己之生活,舉其所有以拯無告之窮民,而不求其報。如此者,人固無不引而重之,然孰敢謂其行為為合理的乎?或如阿諾爾特以無上之勇,親受敵人之刃,以圖其國民之勝利者,孰得謂之合理的行為乎?又自他方麵觀之,今有一人焉,自幼時以來,深思遠慮,求財產與名譽,以保其一身及妻子之福祉。彼舍目前之快樂,而忍社會之恥辱,不寄其心於美學及哲學等無用之事業,不費其日於不急之旅行,而以精確之方法,實現其身世之目的。彼之生涯雖無害於世,然終其身無一可褒之點,然孰不謂此種俗子有非常之推理力乎?又設有一惡人焉,以卑劣之策獵取富貴,甚或盜國家而有之,然後以種種詭計蠶食其鄰國,而為世界之主。彼其為此也,堅忍果戾而不奪,於正義及仁愛之念有妨彼之計畫者,剪之除之屠之刈之而無所顧,驅億萬之民於刀鋸縲絏而無所憫,然且厚酬其黨類及助己者而無所吝,以達其最大之目的,孰不謂彼之舉動全由理性出者乎?當其設此計畫也,必須有最大之悟性,然執行此計畫,必由理性之力。此所謂實踐理性者非歟?將謹慎與精密,深慮與先見,馬啟萬里所以描寫君主者,果不合理的歟?夫人知其不然也。要知大惡之所由成,不由於其乏理性,而反由與理性同盟之故。故汗德以前之作者,皆以良心為倫理的衝動之源,以與理性相對立。盧梭於其《哀美耳》中既述二者之區別,即雅裏大德勒亦謂德性之根源,不存於人性之合理的部分,而存於其非理的部分。基開祿所謂理性者,罪惡必要之手段,其意亦謂此也。何則?理性者,吾人構造概念之能力也。而概念者,乃一種普遍而不可直觀之觀念,而以言語為之記號,此所以使人異於禽獸,而使於圓球上占最優之位置者也。蓋禽獸常為現在之奴隸,而人類則以有理性之故,能合人生及世界之過去、未來而統計之,故能不役於現在,而作有計畫有係統之事業,可以之為善,亦可以之為惡。而理性之關於行為者,謂之實踐理性,故所謂實踐理性者,實與拉丁語之Prudentra(謹慎小心)”相似,而與倫理學上之善無絲毫之關係者也。
吾國語中之“理”字,自宋以後,久有倫理學上之意義,故驟聞叔本華之說,固有未易首肯者。然理之為義,除理由、理性以外,更無他解。若以理由言,則倫理學之理由,所謂動機是也。一切行為無不有一物焉為之機括,此機括或為具體的直觀,或為抽象的概念,而其為此行為之理由則一也。由動機之正否而行為有善惡,故動機,虛位也,非定名也。善亦一動機,惡亦一動機。理性亦然。理性者,推理之能力也。為善由理性,為惡亦由理性,則理性之但為行為之形式,而不足為行為之標準,昭昭然矣。惟理性之能力為動物之所無,而人類之所獨有,故世人遂以形而上學之所謂真與倫理學之所謂善,盡歸諸理之屬性,不知理性者,不過吾人知力之作用,以造概念,以定概念之關係,除為行為之手段外,毫無關於倫理上之價值。其所以有此誤解者,由理之一字乃一普遍之概念。故此又前篇之所極論,而無待贅述者也。
○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
自十九世紀以降,教育學蔚然而成一科之學。溯其原始,則由德意誌哲學之發達是已。當十八世紀之末葉,汗德始由其嚴肅論之倫理學而說教育學,然尚未有完全之係統。厥後海爾巴德始由自己之哲學,而組織完全之教育學。同時,德國有名之哲學家往往就教育學有所研究,而各由其哲學係統以創立自己之教育學。裴奈楷然也,海額爾派之左右翼亦然也。此外專門之教育學家,其竊取希哀林及休來哀爾、馬黑爾之說以構其學說者亦不少,獨無敢由叔本華之哲學以組織教育學者,何則?彼非大學教授也。其生前之於學界之位置與門弟子之數,決非兩海氏之比。其性行之乖僻,使人人視之若蛇蠍。然彼終其身索居於法蘭克福特,非有一親愛之朋友也。殊如其哲學之精神與時代之精神相反對,而與教育學之以增進現代之文明為宗旨者,儼然有持方柄入圓鑿之勢。然叔氏之學說果與現代之文明不相並立歟?即令如是,而此外叔氏所貢獻於教育學者,竟不足以成一家之說歟?抑真理之戰勝必待於後世,而曠世之天才不容於同時,如叔本華自己之所說歟?至十九世紀之末,腓力特尼采始公一著述曰《教育家之叔本華》。然尼采之學說為世人所詬病,亦無以異於昔日之叔本華,故其說於普通之學界中,亦非有偉大之勢力也。尼氏此書,餘未得見,不揣不敏,試由叔氏之哲學說以推繹其教育上之意見。其條目之詳細,或不如海、裴諸氏,至其立腳地之堅固,確實用語之精審明晰,自有哲學以來,殆未有及叔氏者也。嗚呼!《充足原理》之出版已九十有一年,《意誌及觀念之世界》之出版八十有七年,《倫理學之二大問題》之出版亦六十有五年矣,而教育學上無奉叔氏之說者,海氏以降之逆理說乃彌滿充塞於教育界,譬之歌白尼既出,而猶奉多祿某之天文學,生達維之後,而猶言斯他爾之化學,不亦可哀也歟!夫哲學,教育學之母也。彼等之哲學既鮮確實之基礎,欲求其教育學之確實,又烏可得乎!茲略述叔氏之哲學說與其說之及於教育學之影響,世之言教育學可以觀焉。哲學者,世界最古之學問之一,亦世界進步最遲之學問之一也。自希臘以來至於汗德之生二千餘年,哲學上之進步幾何?自汗德以降至於今百有餘年,哲學上之進步幾何?其有紹述汗德之說而正其誤謬,以組織完全之哲學係統者,叔本華一人而已矣。而汗德之學說,僅破壞的而非建設的。彼憬然於形而上學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識論易形而上學,故其說僅可謂之哲學之批評,未可謂之真正之哲學也。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識論出,而建設形而上學,複與美學、倫理學以完全之係統。然則視叔氏為汗德之後繼者,寧視汗德為叔氏之前驅者為妥也。茲舉叔氏哲學之特質如下:
汗德以前之哲學家,除其最少數外,就知識之本質之問題皆奉素樸實在論,即視外物為先知識而存在,而知識由經驗外物而起者也。故於知識之本質之問題上奉實在論者,於其淵源之問題上,不得不奉經驗論。其有反對此說者,亦未有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也。汗德獨謂吾人知物時,必於空間及時間中而由因果性(汗德舉此等性,其數凡十二。叔本華僅取此性)整理之。然空間時間者,吾人感性之形式,而因果性者,吾人悟性之形式。此數者皆不待經驗,而存而構成吾人之經驗者也。故經驗之世界,乃外物之入於吾人感性、悟性之形式中者,與物之自身異。物之自身雖可得而思之,終不可得而知之。故吾人所知者,唯現象而已。此與休蒙之說,其差隻在程度而不在性質。即休蒙以因果性等出於經驗,而非有普遍性及必然性。汗德以為本於先天而具此二性,至於對物之自身,則皆不能讚一詞。故如以休蒙為懷疑論者乎,則汗德之說,雖欲不謂之懷疑論,不可得也。叔本華於知識論上奉汗德之說曰:“世界者,吾人之觀念也。一切萬物皆由充足理由之原理決定之,而此原理,吾人知力之形式也。物之為吾人所知者,不得不入此形式,故吾人所知之物決非物之自身,而但現象而已。易言以明之,吾人之觀念而已。”然則物之自身,吾人終不得而知之乎?叔氏曰:“否。他物則吾不可知,若我之為我,則為物之自身之一部,昭昭然矣。而我之為我,其現於直觀中時,則塊然空間及時間中之一物,與萬物無異。然其現於反觀時,則吾人謂之意誌而不疑也。而吾人反觀時,無知力之形式行乎其間,故反觀時之我,我之自身也。然則我之自身,意誌也。而意誌與身體,吾人實視為一物,故身體者,可謂之意誌之客觀化,即意誌之入於知力之形式中者也。吾人觀我時,得由此二方麵,而觀物時,隻由一方麵,即唯由知力之形式中觀之,故物之自身,遂不得而知。然由觀我之例推之,則一切物之自身,皆意誌也。”叔本華由此以救汗德批評論之失,而再建形而上學。於是汗德矯休蒙之失,而謂經驗的世界有超絕的觀念性與經驗的實在性者,至叔本華而一轉,即一切事物由叔本華氏觀之,實有經驗的觀念性,而有超絕的實在性者也。故叔本華之知識論,自一方麵觀之,則為觀念論,自他方麵觀之,則又為實在論。而彼之實在論,與昔之素樸實在論異,又昭然若揭矣。
古今之言形而上學及心理學者,皆偏重於知力之方麵,以為世界及人之本體,知力也。自柏拉圖以降至於近世之拉衣白尼誌,皆於形而上學中持此主知論。其間雖有若聖奧額斯汀謂一切物之傾向,與吾人之意誌同,有若汗德於其《實理批評》中說意誌之價值,然尚未得為學界之定論。海爾巴德複由主知論以述係統之心理學,而由觀念及各觀念之關係,以說明一切意識中之狀態。至叔本華出,而唱主意論。彼既由吾人之自覺,而發見意誌為吾人之本質,因之以推論世界萬物之本質矣。至是複由經驗上證明之,謂吾人苟曠觀生物界與吾人精神發達之次序,則意誌為精神中之第一原質,而知力為其第二原質,自不難知也。植物上逐日光,下趨土漿,此明明意誌之作用,然其知識安在?下等動物之於飲食男女,好樂而惡苦也與吾人同,此明明意誌之作用,然其知識安在?即吾人之墜地也,初不見有知識之跡,然且呱呱而啼饑,瞿瞿而索母,意誌之作用早行乎其間。若就知力上言之,彌月而始能視,於是始見有悟性之作用。三歲而後能言,於是始見有理性之作用。知力之發達後於意誌也如此。就實際言之,則知識者,實生於意誌之需要。一切生物,其階級愈高,其需要愈增,而其所需要之物亦愈精而愈不易得,而其知力亦不得不應之而愈發達。故知力者,意誌之奴隸也,由意誌生而還為意誌用者也。植物所需者,空氣與水耳。之二者無乎不在,得自來而自取之,故雖無知識可也。動物之食物存乎植物及他動物,又各動物各有特別之嗜好,不得不由己力求之,於是悟性之作用生焉。至人類所需,則其分量愈多,其性質愈貴,其數愈雜,悟性之作用不足應其需,始生理性之作用,於是知力與意誌二者始相區別。至天才出,而知力遂不複為意誌之奴隸,而為獨立之作用。然人之知力之所由發達,由於需要之增,與他動物固無以異也。則主知說之心理學不足以持其說,不待論也。心理學然。形而上學亦然。而叔氏之他學說雖不慊於今人,然於形而上學、心理學漸有趨於主意論之勢,此則叔氏之大有造於斯二學者也。
於是叔氏更由形而上學進而說美學。夫吾人之本質既為意誌矣,而意誌之所以為意誌,有一大特質焉,曰生活之欲。何則?生活者非他,不過自吾人之知識中所觀之意誌也。吾人之本質既為生活之欲矣,故保存生活之事為人生之唯一大事業,且百年者,壽之大齊,過此以往,吾人所不能暨也。於是向之圖個人之生活者,更進而圖種姓之生活。一切事業皆起於此。吾人之意誌,誌此而已。吾人之知識,知此而已。既誌此矣,既知此矣,於是滿足與空乏,希望與恐怖,數者如環無端,而不知其所終。目之所觀,耳之所聞,手足所觸,心之所思,無往而不與吾人之利害相關。終身仆仆而不知所稅駕者,天下皆是也。然則此利害之念竟無時或息歟?吾人於此桎梏之世界中竟不獲一時救濟歟?曰有。唯美之為物不與吾人之利害相關係,而吾人觀美時,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則?美之對象非特別之物,而此物之種類之形式又觀之之我,非特別之我,而純粹無欲之我也。夫空間、時間既為吾人直觀之形式,物之現於空間者皆並立,現於時間者皆相續,故現於空間時間者,皆特別之物也。既視為特別之物矣,則此物與我利害之關係,欲其不生於心,不可得也。若不視此物為與我有利害之關係,而但觀其物,則此物已非特別之物,而代表其物之全種,叔氏謂之曰“實念”。故美之知識,實念之知識也。而美之中,又有優美與壯美之別。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關係而玩之而不厭者,謂之曰“優美之感情”。若其物直接不利於吾人之意誌,而意誌為之破裂,唯由知識冥想其理念者,謂之曰“壯美之感情”。然此二者之感吾人也,因人而不同,其知力彌高,其感之也彌深。獨天才者,由其知力之偉大而全離意誌之關係,故其觀物也視他人為深,而其創作之也與自然為一,故美者,實可謂天才之特許物也。若夫終身局於利害之桎梏中,而不知美之為何物者,則滔滔皆是。且美之對吾人也,僅一時之救濟,而非永遠之救濟,此其倫理學上之拒絕意誌之說所以不得已也。
吾人於此可進而窺叔氏之倫理學。從叔氏之形而上學,則人類於萬物,同一意誌之發現也。其所以視吾人為一個人,而與他人物相區別者,實由知力之蔽。夫吾人之知力既以空間、時間為其形式矣,故凡現於知力中者,不得不複雜。既複雜矣,不得不分彼我。然就實際言之,實同一意誌之客觀化也。易言以明之,即意誌之入於觀念中者,而非意誌之本質也。意誌之本質,一而已矣。故空間、時間二者,用婆羅門及佛教之語言之,則曰“摩耶之網”;用中世哲學之語言之,則曰“個物化之原理”也。自此原理,而人之視他人及物也,常若與我無毫髮之關係。苟可以主張我生活之欲者,則雖犧牲他人之生活之欲以達之,而不之恤,斯之謂“過”。其甚者無此利己之目的,而惟以他人之苦痛為自己之快樂,斯為之“惡”。若一旦超越此個物化之原理,而認人與己皆此同一之意誌,知己所弗欲者,人亦弗欲之,各主張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於是有正義之德。更進而以他人之快樂為己之快樂,他人之苦痛為己之苦痛,於是有博愛之德。於正義之德中,己之生活之欲,己加以限製。至博愛,則其限製又加甚焉。故善惡之別,全視拒絕生活之欲之程度以為斷。其但主張自己之生活之欲,而拒絕他人之生活之欲者,是為過與惡。主張自己亦不拒絕他人者,謂之正義。稍拒絕自己之欲以主張他人者,謂之博愛。然世界之根本,以存於生活之欲之故,故以苦痛與罪惡充之。而在主張生活之欲以上者,無往而非罪惡。故最高之善,存於滅絕自己生活之欲,且使一切生物皆滅絕此欲,而同入於涅槃之境。此叔氏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也。此絕對的博愛主義與克己主義。雖若有嚴肅論之觀,然其說之根柢存於意誌之同一之說,由是而以永遠之正義說明為惡之苦與為善之樂,故其說自他方麵言之,亦可謂立於快樂論及利己主義之上者也。
叔氏於其倫理學之他方麵,更調和昔之自由意誌論及定業論,謂意誌自身絕對的自由也。此自由之意誌苟一旦有所決而發見於人生,及其動作也,則必為外物所決定,而毫末不能自由。即吾人有所與之品性對所與之動機,必有所與之動作隨之。若吾人對所與之動機而欲不為之動乎?抑動矣,而欲自異於所與之動作乎?是猶卻走而惡影,擊鼓而欲其所金聲也,必不可得之數也。蓋動機律之決定吾人之動作也,與因果律之決定物理界之現象無異。此普遍之法則也,必然之秩序也。故同一之品性對同一之動機,必不能不為同一之動作。故吾人之動作,不過品性與動機二者感應之結果而已。更自他方麵觀之,則同一之品性對種種之動機,其動作雖殊,仍不能稍變其同一之方向,故德性之不可以言語教也,與美術同。苟倫理學而可以養成有德之人物,然則大詩人及大美術家亦可以美學養成之歟?有人於此而有貪戾之品性乎?其為匹夫,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可也。浸假而為君主,則擲千萬人之膏血以征服宇宙可也。浸假而受宗教之感化,則摩頂放踵,棄其生命、國土以求死後之快樂可也。此數者,其動作不同,而其品性則絕不稍異。此豈獨他人不能變更之哉?即彼自己,亦有時痛心疾首而無可如何者也。故自由之意誌苟一度自決而現於人生之品性以上,則其動作之必然,無可諱也。仁之不能化而為暴,暴之不能化而為仁,與鼓之不能作金聲,鍾之不能作石聲無以異。然則吾人之品性遂不能變化乎?叔氏曰:“否。吾人之意誌苟欲此生活而現於品性以上,則其動作有絕對的必然性。然意誌之欲此與否,或不欲此而欲彼,則有絕對的自由性者也。吾人苟有此品性,則其種種之動作,必與其品性相應。然此氣質非他,吾人之所欲而自決定之者也。然欲之與否,則存於吾人之自由。於是吾人有變化品性之義務,雖變化品性者古今曾無幾人,然品性之所以能變化,即意誌自由之征也。然此變化僅限於超絕的品性,而不及於經驗的品性。”由此觀之,叔氏於倫理學上持經驗的定業論與超絕的自由論,與其於知識論上持經驗的觀念論與超絕的實在論無異。此亦自汗德之倫理學出,而又加以係統的說明者也。由是叔氏之批評善惡也,亦帶形式論之性質。即謂品性苟善,則其動作之結果如何,不必問也。若有不善之品性,則其動作之結果,雖或有益無害,然於倫理學上,實非有絲毫之價值者也。
至叔氏哲學全體之特質,亦有可言者。其最重要者,叔氏之出發點在直觀(即知覺),而不在概念是也。蓋自中世以降之哲學,往往從最普遍之概念立論,不知概念之為物,本由種種之直觀抽象而得者,故其內容不能有直觀以外之物。而直觀既為概念以後,亦稍變其形而不能如直觀自身之完全明晰,一切謬妄皆生於此。而概念之愈普遍者,其離直觀愈遠,其生謬妄愈易。故吾人欲深知一概念,必實現之於直觀,而以直觀代表之而後可。若直觀之知識,乃最確實之知識。而概念者,僅為知識之記憶傳達之用,不能由此而得新知識。真正之新知識,必不可不由直觀之知識,即經驗之知識中得之。然古今之哲學家往往由概念立論,汗德且不免此,況他人乎?特如希哀林、海額爾之徒專以概念為哲學上唯一之材料,而不複求之於直觀,故其所說非不莊嚴宏麗,然如蜃樓海市,非吾人所可駐足者也。叔氏謂彼等之哲學曰言語之遊戲,寧為過歟!叔氏之哲學則不然。其形而上學之係統,實本於一生之直觀所得者。其言語之明晰與材料之豐富,皆存於此。且彼之美學、倫理學中亦重直觀的知識,而謂於此二學中,概念的知識無效也。故其言曰:“哲學者,存於概念而非出於概念。”即以其研究之成績載之於言語(概念之記號)中,而非由概念出發者也。叔氏之哲學所以淩轢古今者,其淵源實存於此。彼以天才之眼觀宇宙人生之事實,而於婆羅門佛教之經典及柏拉圖、汗德之哲學中發見其觀察之不謬,而樂於稱道之。然其所以構成彼之偉大之哲學係統者,非此等經典及哲學,而人人耳中、目中之宇宙人生即是也。易言以明之,此等經典哲學乃彼之宇宙觀及人生觀之注腳,而其宇宙觀及人生觀非由此等經典哲學出者也。
更有可注意者,叔氏一生之生活是也。彼生於富豪之家,雖中更衰落,尚得維持其索居之生活,彼送其一生於哲學之考察,雖一為大學講師,然未幾即罷,又非以著述為生活者也。故其著書之數,於近世哲學家中為最少,然書之價值之貴重有如彼者乎?彼等日日為講義,日日作雜誌之論文(殊如希哀林、海額爾等),其為哲學上真正之考察之時殆希也。獨叔氏送其一生於宇宙人生上之考察與審美上之瞑想,其妨此考察者,獨彼之強烈之意誌之苦痛耳。而此意誌上之苦痛,又還為哲學上之材料,故彼之學說與行為,雖往往自相矛盾,然其所謂為哲學而生而非以哲學為生者,則誠夫子之自道也。
至是吾人可知叔氏之在哲學上之位置,其在古代則有希臘之柏拉圖,在近世則有德意誌之汗德,此二人固叔氏平生所最服膺,而亦以之自命者也。然柏氏之學說中,其所說之真理,往往被以神話之麵具。汗德之知識論,固為曠古之絕識,然如上文所述,乃破壞的而非建設的,故僅如陳勝、吳廣,帝王之驅除而已。更觀叔氏以降之哲學,如翻希奈爾芬、德赫爾、德曼等,無不受叔氏學說之影響。特如尼采由叔氏之學說出,浸假而趨於叔氏之反對點,然其超人之理想,其所負於叔氏之天才論者亦不少。其影響如彼,其學說如此,則叔氏與海爾巴脫等之學說,孰真孰妄,孰優孰絀,固不俟知者而決也。
吾人既略述叔本華之哲學,更進而觀其及於教育學說。彼之哲學如上文所述,既以直觀為唯一之根據矣,故其教育學之議論,亦皆以直觀為本。今將其重要之學說述之如左:
叔氏謂直觀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唯直接間接與此相聯絡者,斯得為真理,而去直觀愈近者,其理愈真。若有概念雜乎其間,則欲其不罹於虛妄,難矣。如吾人持此論以觀數學,則歐幾裏得之方法二千年間所風行者,欲不謂之乖謬,不可得也。夫一切名學上之證明,吾人往往反而求其源於直觀。若數學,固不外空間、時間之直觀,而此直觀非後天的直觀,而先天的直觀也。易言以明之,非經驗的直觀,而純粹的直觀也。即數學之根據存於直觀,而不俟證明,又不能證明者也。今若於數學中舍其固有之直觀,而代以名學上之證明,與人自斷其足,而俟輦而行者何異?於彼《充足之理由之原理》之論文中述知識之根據(謂名學上之根據)與實在之根據(謂數學上之根據)之差異,數學之根據惟存於實在之根據,而知識之根據則與之全不相涉。何則?知識之根據但能說物之如此如彼,而不能說何以如此如彼。而歐幾裏得則全用從此根據以說數學,今以例證之。當其說三角形也,固宜首說各角與各邊之互相關係,且其互相關係也。正如理由與結論之關係而合於充足理由之原理之形式,而此形式之在空間中與在他方麵無異,常有必然之性質。即一物所以如此,實由他物之異於此物者如此故也。歐氏則不用此方法以說明三角形之性質,僅與一切命題以名學上之根據,而由矛盾之原理以委曲證明之,故吾人不能得空間之關係之完全之知識,而僅得其結論,如觀魚龍之戲,但示吾人以器械之種種作用,而其內部之聯絡及構造,則終未之示也。吾人由矛盾之原理,不得不認歐氏之所證明者為真實,然其何以真實,則吾人不能知之。故雖讀歐氏之全書,不能真知空間之法則,而但記法則之某結論耳。此種非科學的知識,與醫生之但知某病與其治療之法,而不知二者之關係無異。然於某學問中,舍其固有之證明而求之於他其結果,自不得不如是也。
叔氏又進而求其用此方法之原因,蓋自希臘之哀利梯克派首立所觀及所思之差別及其衝突,美額利克派、詭辯派、新阿克特美派及懷疑派等繼之。夫吾人之知識中,其受外界之感動者五官,而變五官所受之材料為直觀者,悟性也。吾人由理性之作用而知五官及悟性,固有時而欺吾人,如夜中視朽索而以為蛇,水中置一棒而折為二,所謂幻影者是也。彼等但注意於此,以經驗的直觀為不足恃,而以為真理唯存於理性之思索,即名學上之思索,此唯理論與前之經驗論相反對。歐幾裏得於是由此論之立腳地以組織其數學,彼不得已而於直觀上發見其公理,但一切定理皆由此推演之,而不複求之於直觀。然彼之方法之所以風行後世者,由純粹的直觀與經驗的直觀之區別未明於世故。迨汗德之說出,歐洲國民之思想與行動皆為之一變,則數學之不能不變,亦自然之勢也。蓋從汗德之說,則空間與時間之直觀,全與一切經驗的直觀異。此能離感覺而獨立,又限製感覺,而不為感覺所限製者也。易言以明之,即先天的直觀也,故不陷於五官之幻影。吾人由此始知歐氏之數學用名學之方法,全無謂之小心也。是猶夜行之人視大道為水,趑趄於其旁之草棘中,而懼其失足也。始知幾何學之圖中,吾人所視為必然者,非存於紙上之圖,又非存於抽象的概念,而唯存於吾人先天所知之一切知識之形式也。此乃充足理由之原理所轄者。而此實在之根據之原理,其明晰與確實,與知識之根據之原理無異。故吾人不必離數學固有之範圍,而獨信任名學之方法。如吾人立於數學固有之範圍內,不但能得數學上當然之知識,並能得其所以然之知識,其賢於名學上之方法遠矣。歐氏之方法,則全分當然之知識與所以然之知識為二,但使吾人知其前者而不知其後者,此其蔽也。吾人於物理學中,必當然之知識與所以然之知識為一,而後得完全之知識。故但知托利珊利管中之水銀,其高三十英寸,而不知由空氣之重量支持之,尚不足為合理的知識也。然則吾人於數學中獨能以但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滿足乎?如畢達哥拉斯之命題,但示吾人以直角三角形之有如是之性質。而歐氏之證明法,使吾人不能求其所以然。然一簡易之圖,使吾人一望而知其必然及其所以然,且其性質所以如此者,明明存於其一角為直角之故。豈獨此命題為然,一切幾何學上之真理皆能由直觀中證之。何則?此等真理元由直觀中發見之者,而名學上之證明,不過以後之附加物耳。叔氏幾何學上之見地如此,厥後哥薩克氏由叔氏之說以教授幾何學,然其書亦見棄於世。而世之授幾何學者,仍用歐氏之方法,積重之難返,固若是哉!
叔氏於數學上重直觀而不重理性也如此,然叔氏於教育之全體,無所往而不重直觀,故其教育上之意見,重經驗而不重書籍。彼謂概念者,其材料自直觀出,故吾人思索之世界,全立於直觀之世界上者也。從概念之廣狹,而其離直觀也有遠近,然一切概念無一不有直觀為之根柢。此等直觀與一切思索以其內容,若吾人之思索而無直觀為之內容乎?則直空言耳,非概念也。故吾人之知力如一銀行,然必備若干之金幣,以應鈔票之取求,而直觀如金錢,概念如鈔票也。故直觀可名為第一觀念,而概念可名為第二觀念,而書籍之為物,但供給第二種之觀念。苟不直觀一物,而但知其概念,不過得大概之知識。若欲深知一物及其關係,必直觀之而後可,決非言語之所能為力也。以言語解言語,以概念比較概念,極其能事,不過達一結論而已。但結論之所得者非新知識,不過以吾人之知識中所固有者應用之於特別之物耳。若觀各物與其間之新關係而貯之於概念中,則能得種種之新知識。故以概念比較概念,則人人之所能,至能以概念比較直觀者,則希矣。真正之知識唯存於直觀,即思索(比較概念之作用)時亦不得不藉想像之助。故抽象之思索而無直觀為之根柢者,如空中樓閣,終非實在之物也。即文字與語言,其究竟之宗旨,在使讀者反於作者所得之具體的知識。苟無此宗旨,則其著述不足貴也。故觀察實物與誦讀,其間之差別不可以道裏計。一切真理唯存於具體的物中,與黃金之唯存於礦石中無異,其難隻在搜尋之。書籍則不然。吾人即於此得真理,亦不過其小影耳,況又不能得哉!故書籍之不能代經驗,猶博學之不能代天才,其根本存於抽象的知識不能取具體的知識而代之也。書籍上之知識,抽象的知識也,死也。經驗的知識,具體的知識也,則常有生氣。人苟乏經驗之知識,則雖富書籍上之知識,猶一銀行而出十倍其金錢之鈔票,亦終必倒閉而已矣。且人苟過用其誦讀之能力,則直觀之能力必因之而衰弱,而自然之光明反為書籍之光所掩蔽。且注入他人之思想,必壓倒自己之思想,久之,他人之思想遂寄生於自己之精神中,而不能自思一物。故不斷之誦讀,其有害於精神也必矣。況精神之為物非奴隸,必其所欲為者,乃能有成。若強以所不欲學之事,或已疲而猶用之,則損人之腦髓,與在月光中讀書,其有損於人之眼無異也。而此病殊以少時為甚。故學者之通病,往往在自七歲至十二歲間習希臘拉丁之文法。彼等蠢愚之根本實存於此,吾人之所深信而不疑也。夫吾人之所食,非盡變為吾人之血肉,其變為血肉者,必其所能消化者也。苟所食而過於其所能消化之分量,則豈徒無益,而反以害之。吾人之讀書豈有以異於此乎!額拉吉來圖曰“博學非知識”此之謂也。故學問之為物,如重甲胄然,勇者得之,固益有不可禦之勢,而施之於弱者,則亦倒於地而已矣。叔氏於知育上之重直觀也如此,與盧騷、貝斯德祿奇之說如何相近,自不難知也。
而美術之知識全為直觀之知識,而無概念雜乎其間,故叔氏之視美術也尤重於科學。蓋科學之源雖存於直觀,而既成一科學以後,則必有整然之係統,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類者,而合其相類者以排列之於一概念之下,而此概念複與相類之他概念排列於更廣之他概念之下。故科學上之所表者,概念而已矣。美術上之所表者,則非概念,又非個象,而以個象代表其物之一種之全體,即上所謂實念者是也,故在在得直觀之。如建築、雕刻、圖畫、音樂等,皆呈於吾人之耳目者。唯詩歌(並戲劇、小說言之)一道,雖藉概念之助以喚起吾人之直觀,然其價值全存於其能直觀與否。詩之所以多用比興者,其源全由於此也。由是叔氏於教育上甚蔑視曆史,謂曆史之對象非概念,非實念,而但個象也。詩歌之所寫者,人生之實念,故吾人於詩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識。故詩歌之所寫者,人及其動作而已。而曆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動作即彼動作,其數雖巧曆,不能計也。然此等事實,不過同一生活之欲之發現,故吾人欲知人生之為何物,則讀詩歌賢於曆史遠矣。然叔氏雖輕視曆史,亦視曆史有一種之價值。蓋國民之有曆史,猶個人之有理性。個人有理性,而能有過去、未來之知識,故與動物之但知現在者異。國民有曆史,而有自己之過去之知識,故與蠻民之但知及身之事實者異。故曆史者,可視為人類之合理的意識,而其於人類也,如理性之於個人,而人類由之以成一全體者也。曆史之價值唯存於此,此叔氏就曆史上之意見也。
叔氏之重直觀的知識,不獨於知育、美育上然也,於德育上亦然。彼謂道德之理論,對吾人之動作無絲毫之效,何則?以其不能為吾人之動作之機括故也。苟道德之理論而得為吾人動作之機括乎,必動其利己之心而後可。然動作之由利己之心發者,於道德上無絲毫之價值者也。故真正之德性,不能由道德之理論,即抽象之知識出,而唯出於人己一體之直觀的知識。故德性之為物,不能以言語傳者也。基開祿所謂德性非可教者,此之謂也。何則?抽象的教訓,對吾人之德性即品性之善無甚勢力。苟吾人之品性而善歟,則虛偽之教訓不能沮害之,真實之教訓亦不能助之也。教訓之勢力,隻及於表麵之動作。風俗與模範亦然。但品性自身不能由此道變更之。一切抽象的知識,但與吾人以動機,而動機但能變吾人意誌之方向,而不能變意誌之本質。易言以明之,彼但變其所用之手段,而不變所誌之目的。今以例證之。苟人欲於未來受十倍之報酬,而施大惠於貧民,與望將來之大利,而購不售之股票者,自道德上之價值考之,二者固無以異也。故彼之為正教之故而處異端以火刑者,與殺越人於貨者何所擇?蓋一求天國之樂,一求現在之樂,其根柢皆歸於利己主義故也。所謂德性不可教者,此之謂也。故真正之善,必不自抽象的知識出,而但出於直觀的知識。唯超越個物化之原理,而視己與人皆同一之意誌之發現,而不容厚此而薄彼。此知識不得由思索而失之,亦不能由思索得之。且此知識以非抽象的知識,故不能得於他人,而唯由自己之直觀得之。故其完全之發現,不由言語而唯由動作。正義、博愛、解脫之諸德,皆由此起也。然則美術、德性均不可教,則教育之事廢歟?曰:“否。”教育者,非徒以書籍教之之謂,即非徒與以抽象的知識之謂。苟時時與以直觀之機會,使之於美術、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識,此亦屬於教育之範圍者也。自然科學之教授觀察與實驗,往往與科學之理論相並而行。人未有但以科學之理論為教授,而以觀察、實驗為非教授者,何獨於美育及德育而疑之?然則叔氏之所謂德性不可教者,非真不可教也,但不可以抽象的知識導之使為善耳。現今伯林大學之教授巴爾善氏於其所著倫理學係統中,首駁叔氏德性不可教之說,然其所說全從利己主義上計算者。此正叔氏之所謂謹慎,而於道德上無絲毫之價值者也。其所以為此說,豈不以如叔氏之說,則倫理學為無效,而教育之事將全廢哉?不知由教育之廣義言之,則導人於直觀,而使之得道德之真知識,固亦教育上之事。然則此說之對教育有危險與否,固不待知者而決也。由此觀之,則叔氏之教育主義,全與其哲學上之方法同,無往而非直觀主義也。
○紅樓夢評論△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憂患與勞苦之與生相對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憂患與勞苦者,人人之所惡也。然則詎不人人欲其所惡,而惡其所欲歟?將其所惡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終非可欲之物歟?人有生矣,則思所以奉其生。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寒而欲衣,露處而欲宮室,此皆所以維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則數十年,多則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為不足。於是於數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進而圖永遠之生活時則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進而育子女矣,則有保抱扶持、飲食教誨之責,婚嫁之務。百年之間,早作而夕思,窮老而不知所終。問有出於此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之外者乎?無有也。百年之後,觀吾人之成績,其有逾於此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之外者乎?無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種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於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約束而立一國,擇其賢且智者以為之君,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學校以教之,為之警察以防內奸,為之陸海軍以禦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為也。夫人之於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設計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歟?吾人之憂患勞苦,固亦有所以償之者歟?則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質,熟思而審考之也。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伯。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謂之曰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故苦痛而無回複之快樂者有之矣,未有快樂而不先之或繼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與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減。何則?文化愈進,其知識彌廣,其所欲彌多,又其感苦痛亦彌甚故也。然則人生之所欲既無以逾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又不外乎苦痛,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吾人生活之性質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識,遂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即與吾人之利害相關係。就其實而言之,則知識者,固生於此欲,而示此欲以我與外界之關係,使之趨利而避害者也。常人之知識,止知我與物之關係。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與我相關係者,而於此物中,又不過知其與我相關係之部分而已。及人知漸進,於是始知欲,知此物與我之關係,不可不研究此物與彼物之關係。知愈大者,其研究逾遠焉。自是而生各種之科學。如欲知空間之一部之與我相關係者,不可不知空間全體之關係,於是幾何學興焉(按西洋幾何學Geometry之本義,係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視為應用之科學,而不視為純粹之科學也)。欲知力之一部之與我相關係者,不可不知力之全體之關係,於是力學興焉。吾人既知一物之全體之關係,又知此物與彼物之全體之關係,而立一法則焉以應用之,於是物之現於吾前者,其與我之關係及其與他物之關係,粲然陳於目前而無所遁。夫然後吾人得以利用此物,有其利而無其害,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進於無窮。此科學之功效也。故科學上之成功,雖若層樓傑觀,高嚴巨麗,然其基址則築乎生活之欲之上,與政治上之係統立於生活之欲之上無以異。然則吾人理論與實際之二方麵,皆此生活之欲之結果也。
由是觀之,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方麵,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即與苦痛相關係。茲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此時也,吾人之心無希望,無恐怖,非複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猶積陰彌月,而旭日杲杲也。猶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飄著於故鄉之海岸也。猶陣雲慘淡,而插翅之天,使齎平和之福音而來者也。猶魚之脫於罾網,鳥之自樊籠出,而遊於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於吾人,無利害之關係而後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實物而後可。然則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夫自然界之物,無不與吾人有利害之關係,縱非直接,亦必間接相關係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與我之關係而觀物,則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鳥飛花落,固無往而非華胥之國,極樂之土也。豈獨自然界而已?人類之言語動作,悲歡啼笑,孰非美之對象乎?然此物既與吾人有利害之關係,而吾人欲強離其關係而觀之,自非天才,豈易及此?於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觀於自然人生中者複現之於美術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與己無關係,而超然於利害之外。是故觀物無方,因人而變。濠上之魚,莊惠之所樂也,而漁父襲之以網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繼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無所住,則雖殉財之夫,貴私之子,寧有對曹霸、韓幹之馬,而計馳騁之樂;見畢宏、韋偃之鬆,而思棟梁之用,求好逑於雅典之偶,思稅駕於金字之塔者哉?故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
而美之為物有二種,一曰優美,一曰壯美。苟一物焉,與吾人無利害之關係,而吾人之觀之也,不觀其關係,而但觀其物,或吾人之心中無絲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觀物也,不視為與我有關係之物,而但視為外物,則今之所觀者,非昔之所觀者也。此時吾心寧靜之狀態,名之曰“優美之情”,而謂此物曰“優美”。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誌為之破裂,因之意誌遁去,而知力得為獨立之作用以深觀其物,吾人謂此物曰“壯美”,而謂其感情曰“壯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屬前種。至於地獄變相之圖、決鬥垂死之像、廬江小吏之詩、雁門尚書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憐,其遇雖戾夫為之流涕,詎有子頹樂禍之心,寧無尼父反袂之戚,而吾人觀之不厭千複。格代之詩曰:
“Whatinlifedothonlygrieveus.Thatsee.”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於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
此之謂也。此即所謂“壯美之情”,而其快樂存於使人忘物我之關係,則固與優美無以異也。
至美術中之與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者。若美術中而有眩惑之原質乎?則又使吾人自純粹之知識出,而複歸於生活之欲。如粔籹蜜餌,《招魂》《七發》之所陳;玉體橫陳,周昉、仇英之所繪;《西廂記》之《酬柬》,《牡丹亭》之《驚夢》;伶元之傳飛燕,楊慎之贗秘辛;徒諷一而勸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雲有“靡靡”之誚,法秀有“綺語”之訶。雖則夢幻泡影,可作如是觀,而拔舌地獄,專為斯人設者矣。故眩惑之於美,如甘之於辛,火之於水,不相並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樂,醫人世之苦痛,是猶欲航斷港而至海,入幽穀而求明,豈徒無益,而又增之。則豈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與物之關係,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與優美及壯美相反對,其故實存於此。
今既述人生與美術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標準,以觀我國之美術。而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吾人於是得一絕大著作曰《紅樓夢》。
△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裒伽爾之詩曰:“Yewisemen,highly,deeply
learned,Whoknow,How,whenand
wheredoallthingspairandlove?YemenofloftywisdomsayWhathappenedtomethe
tellmewhere,how,when,Andwhyithappenedthus.”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學,既深且躋。粲粲生物,罔不匹儔,各齧厥唇,而相厥攸。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時始,來自何處?嗟汝哲人,淵淵其知。相彼百昌,奚而熙熙?願言哲人,詔餘其故。自何時始,來自何處(譯文)?
裒伽爾之問題,人人所有之問題,而人人未解決之大問題也。人有恒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再食則饑。若男女之欲,則於一人之生活上,寧有害無利者也,而吾人之欲之也如此,何哉?吾人自少壯以後,其過半之光陰,過半之事業,所計畫所勤動者為何事?漢之成、哀,曷為而喪其生?殷辛、周幽,曷為而亡其國?勵精如唐玄宗、英武,如後唐莊宗,曷為而不善其終?且人生苟為數十年之生活計,則其維持此生活,亦易易耳,曷為而其憂勞之度,倍蓰而未有已?記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苟能解此問題,則於人生之知識,思過半矣。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豈不可哀也歟!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詩歌、小說之描寫此事者,通古今東西,殆不能悉數,然能解決之者鮮矣。《紅樓夢》一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彼於開卷即下男女之愛之神話的解釋。其敘此書之主人公賈寶玉之來曆曰:
卻說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隻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第一回)。
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誌自由之罪惡也。夫頑鈍者既不幸而為此石矣,又幸而不見用,則何不遊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以自適其適,而必欲入此憂患勞苦之世界,不可謂非此石之大誤也。由此一念之誤,而遂造出十九年之曆史,與百二十回之事實,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與?又於第百十七回中,述寶玉與和尚之談論曰:
“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你那玉是從那裏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和尚笑道:“你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隻是自己的底裏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早該還我了。”
所謂自己的底裏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之一念之誤,而此念之所自造也。及一聞和尚之言,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而其拒絕之也,亦不得由自己,是以有還玉之言。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攜入紅塵者,非彼二人之所為,頑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頑石自己而已。此豈獨寶玉一人然哉?人類之墮落與解脫,亦視其意誌而已。而此生活之意誌,其於永遠之生活,比個人之生活為尤切。易言以明之,則男女之欲,尤強於飲食之欲。何則?前者無盡的,後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後者形而下的也。又如上章所說生活之於苦痛,二者一而非二,而苦痛之度,與主張生活之欲之度為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於後者之苦痛。而《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入於無生之域。當其終也,恒幹雖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滿於現在之生活,而求主張之於異日,則死於此者,固不得不複生於彼,而苦海之流,又將與生活之欲而無窮。故金釧之墮井也,司棋之觸牆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脫也,求償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別之生活,而對生活之為物,則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而柳湘蓮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於金釧。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則雖出世而無與於解脫。苟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如鴛鴦之死,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則惜春、紫鵑之事,固亦其所優為者也。
而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脫,唯非常之人為能,其高百倍於後者,而其難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觀之,則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脫由於苦痛之閱曆,而不由於苦痛之知識。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然於解脫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猶時時起而與之相抗,而生種種之幻影。所謂惡魔者,不過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脫,存於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滿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滿足,如此循環,而陷於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變其氣質,而超出乎苦樂之外,舉昔之所執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之鼎。彼以疲於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複起而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脫之狀態也。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紫鵑。後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後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後者美術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後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為賈寶玉者也。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夫歐洲近世之文學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為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最為精切故也。若《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有以異於彼乎?彼於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胠篋》之篇,而作焚化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則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誌漸決,然尚屢失於寶釵,幾敗於五兒,屢蹶屢振,而終獲最後之勝利。讀者觀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實,其解脫之行程,精進之曆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發揮之。我輩之讀此書者,宜如何表滿足感謝之意哉!而吾人於作者之姓名,尚有未確實之知識,豈徒吾儕寡學之羞,亦足以見二百餘年來,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誰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書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然則予之為此論,亦自知有罪也矣。
△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如上章之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廂記》之以《驚夢》終也,未成之作也。此書若成,吾烏知其不為《續西廂》之淺陋也。有《水滸傳》矣,曷為而又有《蕩寇誌》?有《桃花扇》矣,曷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紅樓夢》矣,彼《紅樓複夢》《補紅樓夢》《續紅樓夢》者,曷為而作也?又曷為而有反對紅樓夢之《兒女英雄傳》?故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曆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曆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縲絏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麵,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曆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紅樓複夢》等,正代表吾國人樂天之精神者也。
《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讀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計外,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以視寶琴、岫煙、李紋、李綺等,若藐姑射神人,敻乎不可及矣。夫此數人者,曷嚐無生活之欲,曷嚐無苦痛?而書中既不及寫其生活之欲,則其苦痛自不得而寫之。足以見二者如驂之靳,而永遠的正義,無往不逞其權力也。又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也。《紅樓夢》則不然,趙姨、鳳姊之死,非鬼神之罰,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紈之受封,彼於《紅樓夢》十四曲中,固已明說之曰: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韶華去之何迅,再休題繡帳鴛衾。隻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隻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第五回)。
此足以知其非詩歌的正義,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無非永遠的正義之所統轄也。故曰《紅樓夢》一書,徹頭徹尾的悲劇也。
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種之悲劇,吾人對蛇蠍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未嚐不悚然戰栗,然以其罕見之故,猶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種,則見此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於吾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嫕,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由此之故,此書中壯美之部分,較多於優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質殆絕焉。作者於開卷即申明之曰:
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汙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麵,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欲寫出自己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鬼一般(此又上節所言之一證)。
慈舉其最壯美者之一例,即寶玉與黛玉最後之相見一節曰:
那黛玉聽著傻大姐說寶玉娶寶釵的話,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踏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隻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腳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裏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隻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隻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隻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隻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隻瞧著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瞧著寶玉笑。兩個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隻管對著臉呆笑起來。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呆笑起來。……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隻管笑,隻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第九十六回)。
如此之文,此書中隨處有之,其動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人不經驗之也。
《紅樓夢》之為悲劇也如此。昔雅裏大德勒於《詩論》中,謂悲劇者,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殊如恐懼與悲憫之二者,為悲劇中固有之物,由此感發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故其目的,倫理學上之目的也。叔本華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而於悲劇之中,又特重第三種,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故。故美學上最終之目的,與倫理學上最終之目的合。由是《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絡也。
△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
自上章觀之,《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上之價值,即存乎此。然使無倫理學上之價值以繼之,則其於美術上之價值,尚未可知也。今使為寶玉者,於黛玉既死之後,或感憤而自殺,或放廢以終其身,則雖謂此書一無價值可也。何則?欲達解脫之域者,固不可不嚐人世之憂患,然所貴乎憂患者,以其為解脫之手段故,非重憂患自身之價值也。今使人日日居憂患,言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其所領之境界,除陰雲蔽天,沮洳彌望外,固無所獲焉。黃仲則《綺懷詩》曰:
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又其卒章曰:
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其一例也。《紅樓夢》則不然。其精神之存於解脫,如前二章所說,茲固不俟喋喋也。
然則解脫者,果足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觀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寶玉者,固世俗所謂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虛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類,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為人類之法則。順之者安,逆之者危;順之者存,逆之者亡。於今日之人類中,吾固不能不認普通之道德之價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據歟?抑出於盲目的動作,而別無意義存乎其間歟?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據,則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謂之絕對的道德可也。然吾人從各方麵觀之,則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實由吾人類之祖先一時之誤謬。詩人之所悲歌,哲學者之所瞑想,與夫古代諸國民之傳說,若出一揆。若第二章所引《紅樓夢》第一回之神話的解釋,亦於無意識中暗示此理,較之《創世記》所述人類犯罪之曆史,尤為有味者也。夫人之有生,既為鼻祖之誤謬矣,則夫吾人之同胞,凡為此鼻祖之子孫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脫之域,則鼻祖之罪,終無時而贖,而一時之誤謬,反覆至數千萬年而未有已也。則夫絕棄人倫如寶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無所辭其不忠不孝之罪。若開天眼而觀之,則彼固可謂幹父之蠱者也。知祖父之誤謬,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顧得謂之不孝哉?然則寶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之說,誠有見乎所謂孝者在此不在彼,非徒自辯護而已。
然則,舉世界之人類,而盡入於解脫之域,則所謂宇宙者,不誠無物也歟?然有無之說,蓋難言之矣。夫以人生之無常,而知識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謂有,非所謂真有者乎?
則自其反而言之,又安知吾人之所謂無,非所謂真無者乎?即真無矣,而使吾人自空乏與滿足、希望與恐怖之中出,而獲永遠息肩之所,不猶愈於世之所謂有者乎?然則吾人之畏無也,與小兒之畏暗黑何以異?自已解脫者觀之,安知解脫之後,山川之美,日月之華,不有過於今日之世界者乎?讀《飛鳥各投林》之曲,所謂“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者,有歟無歟,吾人且勿問,但立乎今日之人生而觀之,彼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難者又曰:人苟無生,則宇宙間最可寶貴之美術,不亦廢歟?曰:美術之價值,對現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絕對的價值也。其材料取諸人生,其理想亦視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趨於其反對之方麵。如此之美術,唯於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價值耳。今設有人焉,自無始以來,無生死,無苦樂,無人世之掛礙,而唯有永遠之知識,則吾人所寶為無上之美術,自彼視之,不過蛩鳴蟬噪而已。何則?美術上之理想,固彼之所自有,而其材料,又彼之所未嚐經驗故也。又設有人焉,備嚐人世之苦痛,而已入於解脫之域,則美術之於彼也,亦無價值。何則?美術之價值,存於使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彼既無生活之欲矣,而複進之以美術,是猶饋壯夫以藥石,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然而超今日之世界人生以外者,於美術之存亡,固自可不必問也。
夫然,故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羅門教及佛教,希伯來之基督教,皆以解脫為唯一之宗旨。哲學家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近世德意誌之叔本華,其最高之理想,亦存於解脫。殊如叔本華之說,由其深邃之知識論、偉大之形而上學出,一掃宗教之神話的麵具,而易以名學之論法,其真摯之感情,與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濟之,故其說精密確實,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學說,徒屬想像而已。然事不厭其求詳,姑以生平所疑者商榷焉。夫由叔氏之哲學說,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絕意誌之說,非一切人類及萬物,各拒絕其生活之意誌,則一人之意誌,亦不可得而拒絕。何則?生活之意誌之存於我者,不過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於一切人類及萬物者,皆與我之意誌同。而此物我之差別,僅由於吾人知力之形式,故離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觀之,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意誌,皆我之意誌也。然則拒絕吾一人之意誌,而姝姝自悅曰解脫,是何異決蹄?之水,而注之溝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哉!佛之言曰:“若不盡度眾生,誓不成佛。”其言猶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觀之,此豈徒能之而不欲哉!將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華之言一人之解脫,而未言世界之解脫,實與其意誌同一之說,不能兩立者也。叔氏於無意識中亦觸此疑問,故於其《意誌及觀念之世界》之第四編之末,力護其說曰:
人之意誌,於男女之欲,其發現也為最著。故完全之貞操,乃拒絕意誌即解脫之第一步也。夫自然中之法則,固自最確實者。使人人而行此格言,則人類之滅絕,自可立而待。至人類以降之動物,其解脫與墮落,亦當視人類以為準。吠陁之經典曰:“一切眾生之待聖人,如饑兒之望慈父母也。”基督教中亦有此思想。珊列休斯於其《人持一切物歸於上帝》之小詩中曰:“嗟汝萬物靈,有生皆愛汝。總總環汝旁,如兒索母乳。攜之適天國,惟汝力是怙。”德意誌之神秘學者馬斯太哀克赫德亦雲:“《約翰福音》雲:餘之離世界也,將引萬物而與我俱。基督豈欺我哉!夫善人,固將持萬物而歸之於上帝,即其所從出之本者也。今夫一切生物,皆為人而造,又各自相為用。牛羊之於水草,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氣,野獸之於林莽皆是也。一切生物皆上帝所造,以供善人之用,而善人攜之以歸上帝。”彼意蓋謂人之所以有用動物之權利者,實以能救濟之之故也。
於佛教之經典中,亦說明此真理,方佛之尚為菩提薩埵也,自王宮逸出而入深林時,彼策其馬而歌曰:“汝久疲於生死兮,今將息此任載。負餘躬以遐舉兮,繼今日而無再。苟彼岸其餘達兮,餘將徘徊以汝待(《佛國記》)。”此之謂也(英譯《意誌及觀念之世界》第一冊第四百九十二頁)。
然叔氏之說,徒引據經典,非有理論的根據也。試問釋迦示寂以後,基督屍十字架以來,人類及萬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異於昔也。然則所謂持萬物而歸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歟?抑徒沾沾自喜之說,而不能見諸實事者歟?果如後說,則釋迦、基督自身之解脫與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數也。往者作一律曰:
生平頗憶挈盧敖,東過蓬萊浴海濤。何處雲中聞犬吠,至今湖畔尚烏號。
人間地獄真無間,死後泥洹枉自豪。終古眾生無度日,世尊祇合老塵囂。
何則?小宇宙之解脫,視大宇宙之解脫以為準故也。赫爾德曼人類涅槃之說,所以起而補叔氏之缺點者以此。要之,解脫之足以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與否,實存於解脫之可能與否。若夫普通之論難,則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圍之大樹也。今使解脫之事,終不可能,然一切倫理學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歟?今夫與此無生主義相反者,生生主義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無窮,以無窮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內,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義之理想之所不許也。故由生生主義之理想,則欲使世界生活之量達於極大限,則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達於極小限。蓋度與量二者,實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福祉者,亦僅歸於倫理學者之夢想而已。夫以極大之生活量,而居於極小之生活度,則生活之意誌之拒絕也奚若?此生生主義與無生主義相同之點也。苟無此理想,則世界之內,弱之肉,強之食,一任諸天然之法則耳,奚以倫理為哉?然世人日言生生主義,而此理想之達於何時,則尚在不可知之數。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終古不過一理想而已矣。人知無生主義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義之理想之何若,此則大不可解脫者也。
夫如是,則《紅樓夢》之以解脫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歟?夫以人生憂患之如彼,而勞苦之如此,苟有血氣者,未有不渴慕救濟者也,不求之於實行,猶將求之於美術。獨《紅樓夢》者,同時與吾人以二者之救濟。人而自絕於救濟則已耳,不然,則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歡迎之也。
△第五章餘論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之主人公之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隨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
綜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為即納蘭性德。其說要非無所本。案性德《飲水詩集·別意》六首之三曰:
獨擁餘香冷不勝,殘更數盡思騰騰。今宵便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又《飲水詞》中《於中好》一闋雲:
別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卻憶紅樓半夜燈。又《減字木蘭花》一闋詠新月雲: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
“紅樓”之字凡三見,而雲“夢紅樓”者一。又其亡婦忌日作《金縷曲》一闋,其首三句雲: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
“葬花”二字,始出於此。然則《飲水集》與《紅樓夢》之間,稍有文字之關係,世人以寶玉為即納蘭侍衛者,殆由於此。然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
至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且此問題,實與美術之淵源之問題相關係。如謂美術上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則其淵源必全存於經驗而後可。夫美術之源,出於先天,抑由於經驗,此西洋美學上至大之問題也。叔本華之論此問題也,最為透辟。茲援其說,以結此論。其言(此論本為繪畫及雕刻發,然可通之於詩歌小說)曰:
附:靜庵詩稿·古今體詩五十首
△雜詩(戊戌四月)飄風自北來,吹我中庭樹。鳥烏覆其巢,向晦歸何處。西山揚頹光,須臾複霾霧。翛翛長夜間,漫漫不知曙。旨蓄既以罄,桑土又雲腐。欲從鴻鵠翔,铩羽不能遽。
陰陽陶萬彙,溫溧固有數。亮無未雨謀,蒼蒼何喜怒。美人如桃李,灼灼照我顏。貽我絕代寶,昆山青琅玕。一朝各千里,執手涕汍瀾。我身局鬥室,我魂馳關山。
神光互離合,咫尺不得攀。惜哉此瑰寶,久棄巾箱間。日月如矢激,倏忽鬢毛斑。我誦《唐棣》詩,愧恧當奚言。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其上矗楩楠,鬱鬱幹雲衢。
匠石忽驚視,謂與凡材殊。詰朝事斤斧,浹辰塗丹朱。明堂高且嚴,詄蕩天人居。虹梁抗日月,菡萏紛扶敷。顧此豫章苗,謂為中欂櫨。付彼拙工輩,刻削失其初。
柯幹未雲堅,不如櫟與樗。中道失所養,幽怨當何如。△嘉興道中(己亥)舟入嘉興郭,清光拂客衣。朝陽承月上,遠樹與星稀。
歲富多新築,潮平露舊磯。如聞迎大府,河上有旌旗。△八月十五夜月
一餐靈藥便長生,眼見山河幾變更。留得當年好顏色,嫦娥底事太無情?△紅豆詞
南國秋深可奈何,手持紅豆幾摩挲。累累本是無情物,誰把閑愁付與他。
門外青驄郭外舟,人生無奈是離愁。不辭苦向東風祝,到處人間作石尤。
別浦盈盈水又波,憑欄渺渺思如何?縱教踏破江南種,隻恐春來茁更多。
勻圓萬顆爭相似,暗數千回不厭癡。留取他年銀燭下,拈來細與話相思。△題梅花畫
夢中恐怖諸天墮,眼底塵埃百斛強。苦憶羅浮山下住,萬梅花裏一胡床。△題友人三十小象
勸君惜取鏡中姿,三十光陰隙裏馳。四海一身原偶寄,千金三致豈前期。
論才君自輕儕輩,學道餘猶半黠癡。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
幾看昆池累劫灰,俄驚滄海又樓台。早知世界由心造,無奈悲歡觸緒來。
翁埠潮回千頃月,超山雪盡萬株梅。卜鄰莫忘他年約,同醉中山酒一杯。△雜感
側身天地苦拘攣,姑射神人未可攀。雲若無心常淡淡,川如不競豈潺潺。
馳懷敷水條山裏,托意開元武德間。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書古書中故紙(癸卯)
昨夜書中得故紙,今朝隨意寫新詩。長捐篋底終無恙,比入懷中便足奇。
黯淡誰能知汝恨,沾塗亦自笑餘癡。書成付與爐中火,了卻人間是與非。△端居端居多暇日,自與塵世疏。處處得幽賞,時時讀異書。高吟驚戶牖,清談霏瓊琚。有時作兒戲,距躍繞庭除。
角力不恥北,說隱自忘愚。雖慚雲中鶴,終勝轅下駒。如此複不樂,問君意何如。陽春煦萬物,嘉樹自敷榮。枳棘茁其旁,既鋤還複生。我生三十載,役役苦不平。如何萬物長,自作犧與牲。
安得吾喪我,表裏洞澄瑩。纖雲歸大壑,皓月行太清。不然蒼蒼者,褫我聰與明。冥然逐嗜欲,如蛾赴寒檠。何為方寸地,矛戟森縱橫。聞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
袞袞百年內,持此欲何成。孟夏天氣柔,草木日夕長。遠山入吾廬,顧影自駘蕩。晴川帶芳甸,十里平如掌。時與二三子,披草越林莽。清曠淡人慮,幽蒨遺世網。歸來倚小閣,坐待新月上。
漁火散微星,暮鍾發疏響。高談達夜分,往往入遐想。
詠此聊自娛,亦以示吾黨。△嘲杜鵑
去國千年萬事非,蜀山回首夢依稀。自家慣作他鄉客,猶自朝朝勸客歸。
幹卿何事苦依依,塵世由來愛別離。歲歲天涯啼血盡,不知催得幾人歸。△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
積雨經旬煙滿湖,先生小疾未全蘇。水聲粗悍如驕將,天色淒涼似病夫。
江上癡雲猶易散,胸中妄念苦難除。何當直上千峰頂,看取金波湧太虛。△遊通州湖心亭扁舟出西郭,言訪湖中寺。野鳥困樊籠,奮然思展翅。入門緣亭坳,塵勞始一憩。方愁亭午熱,清風颯然至。
新荷三兩翻,葭去無際。湖光檻底明,山色樽前墜。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山川非吾故,紛然獨相媚。
嗟爾不能言,安得同把臂。△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
新秋一夜蚊如市,喚起勞人使自思。試問何鄉堪著我,欲求大道況多歧。
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隻益疑。欲語此懷誰與共,鼾聲四起鬥離離。△秋夜即事
蕭然飯罷步魚磯,東寺疏鍾度夕霏。一百八聲親數徹,不知清露濕人衣。△偶成二首我身即我敵,外物非所虞。人生免繈褓,役物固有餘。網罟一朝作,魚鳥失寧居。矯矯驊與騮,垂耳服我車。
玉女粲然笑,照我讀奇書。嗟汝矜智巧,坐此還自屠。一日戰百慮,茲事與生俱。膏明蘭自燒,古語良非虛。蠕蠕繭中蛹,自縛還自鑽。解鈴虎頷下,隻待係者還。
大患固在我,他求寧非謾。所以古達人,獨求心所安。翩然鴻鵠舉,山水恣汗漫。奇花散澗穀,喈喈鳴鵷鸞。悠然七尺外,獨得我所觀。至人更卓絕,古井浩無瀾。
中夜搏嗜欲,甲裳朱且殷。凱歌唱明發,筋力亦雲單。蟬蛻人間世,兀然入泥洹。此語聞自昔,踐之良獨難。
厥途果奚從,吾欲問瞿曇。△拚飛
拚飛懶逐九秋雕,孤耿真成八月蜩。偶作山遊難盡興,獨尋僧話亦無聊。
歡場隻自增蕭瑟,人海何由慰寂寥。不有言愁詩句在,閑愁那得暫時消。△重遊狼山寺
不過招提半載餘,秋高重訪素師居。來桑下還三宿,便擬山中構一廬。
此地果容成小隱,百年那厭讀奇書。君看嶺外囂塵上,詎有吾儕息影區。△塵勞
迢迢征雁過東皋,謖謖長鬆卷怒濤。苦覺秋風欺病骨,不堪宵夢續塵勞。
至今嗬壁天無語,終古埋憂地不牢。投閣沈淵爭一間,子雲何事反離騷?△來日二首來日滔滔來,去日滔滔去。適然百年內,與此七尺遇。爾從何處來?行將徂何處?扶服徑幽穀,途遠日又暮。
霅然一罅開,熹微知天曙。便欲從此逝,荊棘窘餘步。稅駕知何所,漫漫就前路。常恐一擲中,失此黃金注。我力既雲痡,哲人倘見度。瞻望弗可及,求之縑與素。
宇宙何寥廓,吾知則有涯。麵牆見人影,真麵固難知。箘簵半在水,本末互參池。持刀剡作矢,勁直固無虧。耳目不足憑,何況胸所思。人生一大夢,未審覺何時。
相逢夢中人,誰為析餘疑?吾儕皆肉眼,何用試金篦。△登狼山支雲塔
數峰明媚互招尋,孤塔崚嶒試一臨。檻底江流仍日夜,岩間海草未銷沉。
蓬萊自合今時淺,哀樂偏於我輩深。局促百年何足道,滄桑回首亦駸駸。△病中即事(甲辰)
滴殘春雨住無期,開盡園花臥不知。因病廢書增寂寞,強顏入世苦支離。
擬隨桑戶遊方外,未免揚朱泣路歧。聞道南山薇蕨美,膏車徑去莫遲疑。△暮春
晨翻書帙鳥無嘩,晚步郊原草正芽。院落春深新著燕,池塘雨過亂鳴蛙。
心間差許觀身世,病起粗能玩物華。但使猖狂過百歲,不嫌孤負此生涯。△馮生
眾庶馮生自足悲,真人何事困饘饣也?家貧且貸河侯粟,行苦終思牧女糜。
溟海巨鵬將徙日,雪山大道未成時。生平不索長生藥,但索丹方可忍饑。△曉步
興來隨意步南阡,夾道垂楊相帶妍。萬木沈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
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與野鷗申後約,不辭旦旦冒寒煙。△蠶餘家浙水濱,栽桑徑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蠶盈筐篚。蠕蠕食複息,蠢蠢眠又起。口腹雖累人,操作終自己。
絲盡口卒屠,織就鴛鴦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耑耑索其偶,如馬遭鞭棰。呴濡視遺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亻蠡亻蠡長孫子。茫茫千萬載,輾轉周複始。
嗟汝竟何為,草草閱生死。豈伊悅此生,抑由天所畀?
畀者固不仁,悅者長已矣。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平生
平生苦憶挈盧敖,東過蓬萊浴海濤。何處雲中聞犬吠,至今湖畔尚烏號。
人間地獄真無間,死後泥洹枉自豪。終古眾生無度日,世尊隻合老塵囂。△秀州
看月不知清夜長,歸橈漸入秀州鄉。天邊遠樹山千疊,風裏垂楊態萬方。
一自名園竄狐兔,至今淥水少鴛鴦。不須為唱梅村曲,芳草萋萋自斷腸。△偶成文章千古事,亦與時榮枯。並世盛作者,人握靈蛇珠。朝菌媚初日,容色非不腴。飄風夕以至,零落委泥塗。
且複舍之去,周流觀石渠。蔽虧東觀籍,繁會南郭竽。譬如貳負屍,桎梏南山隅。恒幹塊猶存,精氣蕩無餘。小子瞢無狀,亦複事操觚。自忘宿瘤質,攬鏡學施朱。
東家與西舍,假得紫羅襦。主者雖不索,跬步終趑趄。
且當養毛羽,勿作南溟圖。△九日遊留園
朝朝吳市踏紅塵,日日蕭齋兀欠伸。到眼名園初屬我,出城山色便迎人。
奇峰頗欲作人立,喬木居然閱世新。忍放良辰等閑過,不辭歸路雨沾巾。△天寒
天寒木落凍雲鋪,萬點城頭未定烏。隻合楊朱歎歧路,不應阮籍哭窮途。
窮途回駕元非失,歧路亡羊信可籲。駕得靈槎三十丈,空攜片石訪成都。△欲覓
欲覓吾心已自難,更從何處把心安。詩緣病輟彌無賴,憂與生來詎有端。
起看月中霜萬瓦,臥聞風裏竹千竿。滄浪亭北君遷樹,何限棲鴉噪暮寒。△出門
出門惘惘知奚適,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購書那計讀,且消今日敢論旬。
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過石門我行迫季冬,及此風雨夕。狂飆掠舷過,聲聲如裂帛。後船窘呼號,似聞樓擄折。孤懷不能寐,高枕聽淅瀝。
須臾風雨止,微光漏舷隙。悠然發清興,起坐岸我幘。片月掛東林,垂垂兩岸白。小鬆如人長,離立四五尺。老桑最醜怪,亦複可怡悅。疏竹帶輕皞,搖搖正秀絕。
生平幾見汝,對麵若不識。今夕獨何夕,著意媚孤客。
非徒豁雙眸,直欲奮六翮。此頃能百年,豈惜長行役。△留園玉蘭花(乙巳)
庭中新種玉蘭樹,枝長幹短花無數。燦如幼女冠六珈,躑躅牆陰不能步。
今朝送客城西隅,留園名花天下無。拔地扶疏三四丈,倚天綽約百餘株。
我上東樓頻目極,樓西花海花西日。海上銀濤突兀來,日邊瑤闕參差出。
南圃辛夷亦已花,雪山缺處露朝霞。閑憑危檻久徙倚,眼底層層生絳紗。
窈窕吳娘自矜許,卻來花底羞無語。直令椒麝黯無香,坐使紅顏色消沮。
將歸小住更凝眸,瞑色催人不可留。歸來徑臥添愁悵,萬花倒插藻井上。△坐致
坐致虞唐亦太癡,許身稷契更奚為?誰能妄把平成業,換卻平生萬首詩。△五月二十三夜出閶門驅車至覓渡橋
小齋竟日兀營營,忽試霜蹄四馬輕。螢火時從風裏墮,雉垣偏向電邊明。
靜中觀我原無礙,忙裏哦詩卻易成。歸路不妨冒雷雨,茲遊快絕冠平生。△將理歸裝得馬湘蘭畫幅喜而賦此
舊苑風流獨擅場,土苴當日睨侯王。書生歸舸真奇絕,載得金陵馬四娘。
小石叢蘭別樣清,朱絲細字亦精神。君家宰相成何事,羞殺千秋馮玉英(馬士英善繪事,其遺墨流傳人間者,世人醜之,往往改其名為馮玉英雲)。
續編
○原命
我國哲學上之議論,集於性與理二字。次之者,命也。命有二義:通常之所謂命,《論語》所謂“死生有命”是也。哲學上之所謂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命之有二義,其來已古。西洋哲學上亦有此二問題。其言禍福壽夭之有命者,謂之定命論Fata-Lism。其言善惡賢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動作皆由前定者,謂之定業論Determinism。而定業論與意誌自由論之爭,尤為西洋哲學上重大之事實,延至今日而尚未得最終之解決。我國之哲學家除墨子外,皆定命論者也,然遽謂之定業論者,則甚不然。古代之哲學家中,今舉孟子以代表之。孟子之為持定命論者而兼亦持意誌自由論,得由下二章窺之。其曰: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又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弗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弗謂命也。
前章之所謂命,即“死生有命”之命。後章之命,與“天命之謂性”之命略同,而專指氣質之清濁而言之。其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則孟子之非定業論者,昭昭然矣。至宋儒亦繼承此思想,今舉張橫渠之言以代表之。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正蒙·誠明篇》)
通觀我國哲學上,實無一人持定業論者,故其昌言意誌自由論者,亦不數數覯也,然我國倫理學無不預想此論者。此論之果確實與否,正吾人今日所欲研究者也。
我國之言命者,不外定命論與非定命論二種。二者於哲學上非有重大之興味,故可不論。又,我國哲學上無持定業論者,其他經典中所謂命,又與“性”字與理字之義相近,朱子所謂“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而二者之說已見於餘之《釋理》《論性》二篇,故亦可不論。今轉而論西洋哲學上與此相似之問題,即定業論與自由意誌論之爭及其解決之道,庶於吾國之性命論上亦不無因之明晰雲爾。
定業論者之說曰:“吾人之行為皆為動機所決定,雖吾人有時於二行為間或二動機間若能選擇其一者,然就實際言之,不過動機之強者製動機之弱者,而己之選擇作用無與焉。故吾人行為之善惡皆必然的,因之吾人品性之善惡亦必然的,而非吾人自由所為也。”意誌自由論反是,謂吾人於二動機間有自由之選擇力,而為一事與否,一存於吾人之自由,故吾人對自己之行為及品性,不能不自負其責任。此二者之爭,自希臘以來永為哲學上之題目。汗德純理批評之第三安梯諾朱中所示正理及反理之對立,實明示此爭論者也。
此二論之爭論而不決者,蓋有由矣。蓋從定業論之說,則吾人對自己之行為無絲毫之責任,善人不足敬,而惡人有辭矣。從意誌自由論之說,則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為之破滅。此又愛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於是汗德始起而綜合此二說,曰“在現象之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以為其原因,而此原因複有他原因以為之原因,如此遞衍以至於無窮無往,而不發見因果之關係。故吾人之經驗的品性中,在在為因果律所決定,故必然而非自由也。此則定業論之說,真也。然現象之世界外,尚有本體之世界,故吾人經驗的品性外,亦尚有睿智的品性。而空間、時間及因果律,隻能應用於現象之世界,本體之世界,則立於此等知識之形式外,故吾人之睿智的品性,自由的非必然的也。此則意誌自由論之說,亦真也。故同一事實,自現象之方麵言之,則可謂之必然,而自本體之方麵言之,則可謂之自由。而自由之結果,得現於現象之世界中,所謂無上命法是也。即吾人之處一事也,無論實際上能如此與否,必有當如此不當如彼之感,他人亦不問我能如此否。苟不如此,必加以嗬責。使意誌而不自由,則吾人不能感其當然,他人亦不能加以責備也。今有一妄言者於此,自其經驗的品性言之,則其原因存於不良之教育、腐敗之社會,或本有不德之性質,或缺羞惡之感情,又有妄言所得之利益之觀念為其目前之動機,以決定此行為。而吾人之研究,妄言之原因也,亦得與研究自然中之結果之原因同。然吾人決不因其固有之性質故,決不因其現在之境遇故,亦決不因前此之生活狀態故,而不加以責備,其視此等原因,若不存在者。然而以此行為為彼之所自造,何則?吾人之實踐理性,實離一切經驗的條件而獨立,以於吾人之動作中生一新方向,故妄言之罪,自其經驗的品性言之,雖為必然的,然睿智的品性,不能不負其責任也”。此汗德之調停說之大略也。
汗德於是下自由之定義:其消極之定義曰“意誌之離感性的衝動而獨立”,其積極之定義則曰“純粹理性之能現於實踐也”。然意誌之離衝動而獨立與純粹理性之現於實踐,更無原因以決定之歟?汗德亦應之曰“有理性之勢力即是也”。故汗德以自由為因果之一種,但自由之因果與自然之因果,其性質異耳。然既有原因以決定之矣,則雖欲謂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謂之自由者,則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勢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吾人所以從理性之命令,而離身體上之衝動而獨立者,必有種種之原因。此原因不存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個人之精神,必存於民族之精神。而此等表麵的自由,不過不可見之原因戰勝可見之原因耳。其為原因所決定,仍與自然界之事變無以異也。
叔本華亦紹述汗德之說而稍正其誤,謂動機律之在人事界,與因果律之在自然界同,故意誌之既入經驗界而現於個人之品性以後,則無往而不為動機所決定。惟意誌之自己拒絕,或自己主張,其結果雖現於經驗上,然屬意誌之自由。然其謂意誌之拒絕自己,本於物我一體之知識,則此知識非即拒絕意誌之動機乎?則“自由”二字,意誌之本體果有此性質否?吾不能知。然其在經驗之世界中,不過一空虛之概念,終不能有實在之內容也。
然則吾人之行為既為必然的,而非自由的,則責任之觀念又何自起乎?曰一切行為必有外界及內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意識,必存於無意識。而此種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對此等原因,但為其所決定,而不能加以選擇。如汗德所引妄言之例,固半出於教育及社會之影響,而吾人之入如此之社會,受如此之教育,亦有他原因以決定之,而此等原因往往為吾人所不及覺。現在之行為之不適於人生之目的也一,若當時全可以自由者,於是有責任及悔恨之感情起,而此等感情以為心理上一種之勢力故,故足為決定後日行為之原因。此責任之感情之實踐上之價值也。故吾人責任之感情,僅足以影響後此之行為,而不足以推前此之行為之自由也。餘以此二論之爭與命之問題相聯絡,故批評之於此。又使世人知責任之觀念自有實在上之價值,不必藉意誌自由論為羽翼也。
○人間嗜好之研究
活動之不能以須臾息者,其唯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動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動之地,則感一種之快樂。反是,則感一種之苦痛。此種苦痛,非積極的苦痛,而消極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虛的苦痛也。空虛的苦痛比積極的苦痛,尤為人所難堪。何則?積極的苦痛猶為心之活動之一種,故亦含快樂之原質。而空虛的苦痛,則並此原質而無之故也。人與其無生也,不如惡生。與其不活動也,不如惡活動。此生理學及心理學上之二大原理,不可誣也。人欲醫此苦痛,於是用種種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Tokilltime”,而在我中國則名之曰“消遣”。其用語之確當,均無以易。一切嗜好由此起也。
然人心之活動亦夥矣。食色之欲所以保存個人及其種姓之生活者,實存於人心之根柢,而時時要求其滿足。然滿足此欲,固非易易也。於是或勞心,或勞力,戚戚肙肙以求其生活之道。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工作”。工作之為一種積極的苦痛,吾人之所經驗也。且人固不能終日從事於工作,歲有閑月,月有閑日,日有閑時,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簡,其閑暇愈多。此時雖乏積極的苦痛,然以空虛之消極的苦痛代之,故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動者,雖無益於生活之事業,亦鶩而趨之。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嗜好”。雖嗜好之高尚卑劣,萬有不齊,然其所以慰空虛之苦痛而與人心以活動者,其揆一也。
嗜好之為物,本所以醫空虛的苦痛者,故皆與生活無直接之關係。然若謂其與生活之欲無關係,則甚不然者也。人類之於生活既競爭而得勝矣,於是此根本之欲複變而為勢力之欲,而務使其物質上與精神上之生活,超於他人之生活之上。此勢力之欲,即謂之生活之欲之苗裔,無不可也。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體力,而使之活動。其直接為生活故而活動時,謂之曰“工作”。或其勢力有餘,而唯為活動故而活動時,謂之曰“嗜好”。故嗜好之為物,雖非表直接之勢力,亦必為勢力之小影。或足以遂其勢力之欲者,始足以動人心而醫其空虛的苦痛。不然,欲其嗜之也難矣。今吾人當進而研究種種之嗜好,且示其與生活及勢力之欲之關係焉。
嗜好中之煙酒二者,其令人心休息之方麵多,而活動之方麵少。易言以明之,此二者之效,寧在醫積極的苦痛,而不在醫消極的苦痛。又此二者於心理上之結果外,兼有生理上之結果,而吾人對此二者之經驗亦甚少,故不具論。今先論博弈。夫人生者,競爭之生活也。苟吾人競爭之勢力無所施於實際,或實際上既競爭而勝矣,則其剩餘之勢力,仍不能不求發泄之地。博弈之事,正於抽象上表出競爭之世界,而使吾人於此滿足其勢力之欲者也。且博弈以但表普遍的抽象的競爭,而不表所競爭者之為某物(故為金錢而賭博者不在此例),故吾人競爭之本能,遂於此以無嫌疑無忌憚之態度發表之,於是得窺人類極端之利己主義。至實際之人生中,人類之競爭雖無異於博弈,然能如是之磊磊落落者鮮矣。且博與弈之性質亦自有辨。此二者雖皆世界競爭之小影,而博又為運命之小影,人以執著於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於無望之福,而暗於無望之禍。而於賭博之中,此無望之福時時有可能性在,以博之勝負,人力與運命二者決之,而弈之勝負,則全由人力決之故也。又但就人力言,則博者,悟性上之競爭,而奕者,理性上之競爭也。長於悟性者,其嗜博也甚於奕。長於理性者,其嗜奕也愈於博。嗜博者之性格,機警也,脆弱也,依賴也。嗜奕者之性格,謹慎也,堅忍也,獨立也。譬之治生,前者如朱公居陶居與時逐,後者如任氏之折節為儉,盡力田畜,亦致千金。人亦各隨其性之所近,而欲於競爭之中發見其勢力之優勝之快樂耳。吾人對博奕之嗜好,殆非此無以解釋之也。
若夫宮室車馬衣服之嗜好,其適用之部分屬於生活之欲,而其妝飾之部分,則屬於勢力之欲。馳騁田獵跳舞之嗜好,亦此勢力之欲之所發表也。常人之對書畫古物也亦然。彼之愛書籍,非必愛其所含之真理也。愛書畫古玩,非必愛其形式之優美古雅也。以多相衒,以精相衒,以物之稀而難得也相衒。讀書者亦然,以博相衒。一言以蔽之,衒其勢力之勝於他人而已矣。常人對戲劇之嗜好,亦由勢力之欲出。先以喜劇(即滑稽劇)言之。夫能笑人者,必其勢力強於被笑者也。故笑者,實吾人一種勢力之發表。然人於實際之生活中雖遇可笑之事,然非其人為我所素狎者,或其位置遠在吾人之下者,則不敢笑。獨於滑稽劇中,以其非事實,故不獨使人能笑,而且使人敢笑。此即對喜劇之快樂之所存也。悲劇亦然。霍雷士曰:“人生者自觀之者言之,則為一喜劇;自感之者言之,則又為一悲劇也。”自吾人思之,則人生之運命,固無以異於悲劇。然人當演此悲劇時,亦俯首杜口,或故示整暇,汶汶而過耳。欲如悲劇中之主人公且演且歌,以訴其胸中之苦痛者,又誰聽之,而誰憐之乎?夫悲劇中之人物之無勢力之可言,固不待論。然敢鳴其苦痛者與不敢鳴其痛苦者之間,其勢力之大小,必有辨矣。夫人生中固無獨語之事,而戲曲則以許獨語故,故人生中久壓抑之勢力,獨於其中筐傾而篋倒之,故雖不解美術上之趣味者,亦於此中得一種勢力之快樂。普通之人之對戲曲之嗜好,亦非此不足以解釋之矣。
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學美術,亦不外勢力之欲之發表。希爾列爾既謂兒童之遊戲,存於用剩餘之勢力矣。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遊戲,故其淵源之存於剩餘之勢力,無可疑也。且吾人內界之思想感情,平時不能語諸人,或不能以莊語表之者,於文學中以無人與我一定之關係故,故得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勢力所不能於實際表出者,得以遊戲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勢力充實不可以已,遂不以發表自己之感情為滿足,更進而欲發表人類全體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於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為之發揚而不能自已。故自文學言之,創作與賞鑒之二方麵,亦皆以此勢力之欲為之根柢也。文學既然,他美術何獨不然?豈獨美術而已,哲學與科學亦然。柏庚有言曰“知識即勢力也”。則一切知識之欲,雖謂之即勢力之欲,亦無不可。彼等以其勢力卓越於常人故,故不滿足於現在之勢力,而欲得永遠之勢力。雖其所用以得勢力之手段不同,然其目的固無以異。夫然,始足以活動人心而醫其空虛的苦痛。以人心之根柢,實為一生活之欲。若勢力之欲故,苟不足以遂其生活,或勢力者決不能使之活動。以是觀之,則一切嗜好,雖有高卑優劣之差,固無非勢力之欲之所為也。
然餘之為此論,固非使文學美術之價值下齊於博奕也。不過自心理學言之,則此數者之根柢,皆存於勢力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動,以療其空虛之苦痛。以此所論者,乃事實之問題,而非價值之問題故也。若欲抑製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則必有潰決之一日。此又從人心活動之原理出,有教育之責及欲教育自己者,不可不知所注意焉。
○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
古之儒家,初無所謂哲學也。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無一語及於哲學。其言性與天道,雖高第弟子如子貢,猶以為不可得而聞,則雖斷為未嚐言焉,可也。儒家之有哲學,自《易》之《係辭·說卦》二傳及《中庸》始。《易傳》之為何人所作,古今學者尚未有定論,然除傳中所引孔子語若干條外,其非孔子之作,則可斷也。後世祖述《易》學者,除揚雄之《太玄經》、邵子之《皇極經世》外,亦曾無幾家,而此數家之書,亦不多為人所讀。故儒家中此派之哲學,未可謂有大勢力也。獨《中庸》一書,《史記》既明言為子思所作,故至於宋代,此書遂為諸儒哲學之根柢。周子之言太極,張子之言太虛,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視為宇宙人生之根本,與《中庸》之言誠無異,故亦特尊此書,躋諸《論》《孟》之例,故此書不獨如《係辭》等傳,表儒家古代之哲學,亦古今儒家哲學之淵源也。然則辜氏之先譯此書,亦可謂知務者矣。
然則孔子不言哲學,若《中庸》者,又何自作乎?曰:“《中庸》之作,子思所不得已也。”當是時,略後孔子而生,而於孔子之說外別樹一幟者老氏(老氏之非老聃說,見汪中《述學補遺》)、墨氏。老氏、墨氏亦言道德,言政治,然其說皆歸本於哲學。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虛”與“靜”是已。今執老子而問以人何以當虛當靜,則彼將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老子》十二章)”。此虛且靜者,老子謂之曰“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中略),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墨子道德、政治上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愛也、利也。今試執墨子而問以人何以當愛當利,則彼將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又曰“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墨子·法儀篇》)”。則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雖老子之說虛靜求諸天之本體,而墨子之說愛利求諸天之意誌,其間微有不同,然其所以自固其說者則一也。孔子亦說仁說義,又說種種之德矣。今試問孔子以人何以當仁當義,孔子固將由人事上解釋之。若求其解釋於人事以外,豈獨由孔子之立腳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若子思則生老子、墨子後,比較他家之說,而懼乃祖之教之無根據也,遂進而說哲學,以固孔子道德、政治之說。今使問子思以人何以當誠其身,則彼將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其所以為此說者,豈有他哉?亦欲以防禦孔子之說以敵二氏而已。其或生二子之後,濡染一時思辨之風氣而為此說,均不可知。然其方法之異於孔子,與其所以異之原因不出於此二者,則固可決也。
然《中庸》雖為一種之哲學,雖視“誠”為宇宙人生之根本,然與西洋近世之哲學固不相同。子思所謂誠,固非如裴希脫Fichte之Ego、解林Schelling之Absolute、海格爾Hegel之Idea、叔本華Schopenhauer之Will、哈德曼Hartmann之Unconscious也。其於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議論亦未必盡有界限。如執近世之哲學以述古人之說,謂之彌縫古人之說則可,謂之忠於古人,則恐未也。夫古人之說,固未必悉有條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時而說天道,時而說人事。豈獨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複如此。幸而其所用之語,意義甚為廣莫,無論說天說人時,皆可用此語,故不覺其不貫串耳。若譯之為他國語,則他國語之與此語相當者,其意義不必若是之廣。即令其意義等於此語,或廣於此語,然其所得應用之處不必盡同,故不貫串、不統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貫串、統一,勢不能不用意義更廣之語。然語意愈廣者,其語愈虛,於是古人之說之特質漸不可見,所存者其膚廓耳。譯古書之難全在於是。如辜氏此書中之譯“中”為“Ourtrueself”、“和”為“Moraiorder”,其最著者也。餘如以“性”為“Lawofourbeing”、以“道”為“Morallaw”亦出於求統一之弊。以吾人觀之,則“道”與其謂之“MoralIaw”,寧謂之“Moralorder”。至“性”之為“Lawofourbeing”則“law”之一字,除與“Morallaw”之“Law”字相對照外,於本義上固毫不需此,故不如譯為“EssenceofourbeingorOurtruenature”妥也。此外如此類者,尚不可計。要之,辜氏此書如為解釋《中庸》之書,則吾無間。然且必謂我國之能知《中庸》之真意者,殆未有過於辜氏者也。若視為翻譯之書,而以辜氏之言即子思之言,則未敢信以為善本也。其他種之弊,則在以西洋之哲學解釋《中庸》。其最著者,如“誠則形,形則著”數語。茲錄其文如左:
“Wherethereistruth,thereis
substance.thereissubstance,
thereisreality.Wherethereis
reality,thereisintelligence.thereisintelligence,thereispower.
Wherethereisinfluence.Where
thereisinfluence,thereiscreation.
此等明明但就人事說,鄭注與朱注大概相同,而忽易以“Substance,reality”等許多形而上學上之語“MetaphysicalTerms”,豈非以西洋哲學解釋此書之過哉!至“至誠無息”一節之前半,亦但說人事,而“無息”、“久征”、“悠遠”、“博厚”、“高明”等字,亦皆以形而上學之語譯之,其病亦與前同。讀者苟平心察之,當知餘言之不謬也。
上所述二項,乃此書中之病之大者,然亦不能盡為譯者咎也。中國語之不能譯為外國語者,何可勝道。如《中庸》之第一句,無論何人不能精密譯之。外國語中之無我國“天”字之相當字,與我國語中之無“God”之相當字無以異。吾國之所謂天,非蒼蒼者之謂,又非天帝之謂,實介二者之間,而以蒼蒼之物質具天帝之精神者也。“性”之字亦然。故辜氏所譯之語,尚不失為適也。若夫譯“中”為“OurtrueSelforMoralorder”,是亦不可以已乎。裏雅各JamesLegge之譯“中”為“Mean”,固無以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中”。今辜氏譯“中”為“OurtrueSelf”,又何以解“君子而時中”之“中”乎?吾寧以裏雅各氏之譯中為“Mean”,猶得《中庸》一部之真意者也。夫“中Mean”之思想,乃中國古代相傳之思想,自堯雲“執中”,而皋陶乃衍為“九德”之說。皋陶不以寬為一德,栗為一德,而以二者之中之寬,而栗為一德,否則當言十八德,不當言九德矣。《洪範》“三德”之意亦然。此書中“尊德性”一節及“問強”、“索隱”二章,尤在發明此義。此亦本書中最大思想之一,寧能以“OurtureselforOurcentralself”空虛之語當之乎?又豈得以類於雅裏士多德(Aristotle)之中說而唾棄之乎?餘所以謂失古人之說之特質而存其膚廓者,為此故也。辜氏自謂涵泳此書者且二十年,而其涵泳之結果如此,此餘所不能解也。餘如“和”之譯為“Moralorder”也,“仁”之譯為“Moralsense”也,皆同此病。要之,皆過於求古人之說之統一之病也。至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學釋此書,其病反是。前病失之於減古書之意義,而後者失之於增古書之意義。吾人之譯古書,如其量而止則可矣。或失之減,或失之增,雖為病不同,同一不忠於古人而已矣。辜氏譯本之病,其大者不越上二條,至其以己意釋經之小誤,尚有若干條。茲列舉之如左:
(一)“是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辜氏譯為:Whereforeitisthatthemoralmanwatchesdillgentlyover
whathiseyescannotseeandisinfearandaweocannothear.
其於“其”字一字之訓則得矣,然《中庸》之本意,則亦言不自欺之事。鄭玄注曰: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朱注所謂“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雖用模梭之語,然其釋“獨”字也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則知朱子之說,仍無以異於康成。而辜氏之譯語,其於“其”字雖妥,然涵泳全節之意義,固不如舊注之得也。(二)“隱惡而揚善。”辜氏譯之曰:
Helookeduponevilmerelyassome
thingnegative,andherecognisedonlywhatwasgoodashavingpositiveexistence.
此又以西洋哲學解釋古書,而忘此節之不能有此意也。夫以“惡”為“Negative”,“善”為“Positive”,此乃希臘以來哲學上一種之思想。自斯多噶派Stoics及新柏拉圖派NeoPlatonism之辨神論Theodicy,以至近世之萊布尼茲Leibnitz,皆持此說,不獨如辜氏注中所言大詩人沙士比亞Shakespeare及葛德Goethe二氏之見解而已。然此種人生觀雖與《中庸》之思想非不能相容,然與好問察言之事有何關係乎?如此斷章取義以讀書,吾竊為辜氏不取也。且辜氏亦聞孟子之語乎?孟子曰: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此即“好問”二句之真注腳。至其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乃曰:
Takingthetwoextremesofpositive
andnegative,heappliedthemean
betweenthetwoextremesinhis
judgeanddealingswithpeople.
夫雲“totakethetwoextremesofgoodandevil”(執善惡之中),已不可解,況雲“takingthetwoextremesofpositiveandnegative乎?且如辜氏之意,亦必二者皆“positive”,而後有“extremes”之可言,以“Positive及“negative”為“twoextremes”,可謂支離之極矣。今取朱注以比較之曰: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中略)。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此二解之孰得孰失,不待知者而決矣。
(三)“天下國家可均也。”辜氏譯為:
Amanmaybeabletorenouncethe
possesionofKingdomsandEmpire.而複注之曰:Theword均intextabove,literally‘even,equallydividedishereusedasaverb‘tobeindifferentto’(平視),hen
然試問“均”字果有“tobeindifferentto”(漠視)之訓否乎?豈獨“均”字無此訓而已,即“平視”二字(出《魏誌·劉楨傳注》),亦曷嚐訓此?且即令有此訓,亦必有二不相等之物,而後可言均之平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故若雲天下敝屣可均,則辜氏之說當矣。今但雲天下國家可均,則果如辜氏之說,將均天下國家於何物者哉?至“tobeindifferentto”,不過外國語之偶有“均”字表麵之意者,以此釋“均”,苟稍知中國語者,當無人能首肯之也。
(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鄭注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
其言最為精確。朱子注此節曰“結上文”,亦即鄭意。乃辜氏則譯其上句曰:
Themorallawtakesitsriseinrelationbetweenmanandwoman.
而複引葛德“浮斯德”戲曲Faust中之一節以證之,實則此處並無此意,不如舊注之得其真意也。
(五)辜氏於第十五章以下,即譯“哀公問政”章(朱注本之第二十章),而繼以“舜其大孝”、“無憂”、“達孝”三章,又移“鬼神之為德”一章於此下,然後繼以“自誠明”章。此等章句之更定,不獨有獨斷之病,自本書之意義觀之,亦決非必要也。
(六)辜氏置“鬼神”章於“自誠明”章之上,當必以此章中有一“誠”字故也。然辜氏之譯“誠之不可揜也”乃曰:
Suchisevidenceofthingsinvisible
thatitisimpossibletodoubtthespiritualnatureofman.
不言“誠”字而以“鬼神”代之,尤不可解。夫此章之意,本謂鬼神之為物,亦誠之發現,而乃譯之如此。辜氏於此際,何獨不為此書思想之統一計也。
(七)“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數者,皆指武王言之,朱注“此言武王之事”是也。乃辜氏則以此五句別為一節,而屬之文王,不顧文義之滅裂甚矣。其好怪也!辜氏獨斷之力如此,則更無怪其以武王未受命為文王未受命,及周公成文武之德為周公以周之王成於文武之德也。
(八)“禮所生也,之下,居下位”三句,自為錯簡,故朱子亦從鄭注。乃辜氏不認此處有錯簡,而意譯之曰:
Forunlesssocialinequalities
havetrueandmoralbasis,governmentofthepeopleisanimpossibility.
複於注中直譯之曰:Unlessthelowerordersare
satisfiedwiththoseabovethem,governmentofthepeopleisanimpossibility.
複於下節譯之曰:
Ifthoseinauthorityhavenotthe
Confidenceofthoseunderthem,
governmentofthepeopleisanimposs
按“不獲乎上”之意,當與孟子“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及“不得乎君則熱中”之“得”字相同。如辜氏之解,則《經》當雲“在上位,不獲乎下”,不當雲“在下位,不獲乎上”矣。但辜氏之所以為此解者,亦自有故。以若從字句解釋,則與上文所雲“為天下國家”,下文所雲“民不可得而治”不相容也。然“在下位”以下,自當如鄭注別為一節。而在下位者,既雲“在位”,則自有治民之責,其間固無矛盾也。況孟子引此語亦雲“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乎?要之,此種穿鑿,亦由求古人之說之統一之過也。
(九)“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辜氏譯之曰:
Toattaintothesovereigntyofthe
world,therearethereimportant
thingsnecessary;theymayperhaps
besummedupinoneblamelessnessoflife.
以“三重”歸於“一重”,而即以“寡過”當之,殊屬非是。朱子解為“人得寡過”,固非如辜氏之解,更屬穿鑿。愚按,此當謂王天下者重視儀禮、製度、考文三者,則能寡過也。
(十)“上馬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下馬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一節承上章而言。無征之征,即夏禮殷禮不足征之征,故朱子章句解為“雖善而皆不可考”是也。乃辜氏譯首二句曰:
Howeverexcellentasystemofmoral
truthappeallingtoSupernaturalauthoritymaybe,itisnotverifiablebyexprerience.
以“appealingtosupernaturalauthority”釋“上”字,穿鑿殊甚。不知我國古代固無求道德之根本於神意者,就令有之,要非此際子思之所論者也。
至辜氏之解釋之善者,如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之一為豫,此從鄭注,而善者實較朱注更為直截。此書之不可沒者,唯此一條耳。
吾人更有所不慊者,則辜氏之譯此書,並不述此書之位置如何,及其與《論語》諸書相異之處,如餘於此文首頁之所論。其是否如何,尚待大雅之是正。然此等問題,為譯述及注釋此書者所不可不研究明矣。其尤可異者,則通此書無一語及於著書者之姓名,而但冠之曰《孔氏書》。以此處《大學》則可矣,若《中庸》之為子思所作,明見於《史記》,又從子思再傳弟子孟子書中,猶得見《中庸》中之思想文字,則雖欲沒其姓名,豈可得也。又譯者苟不信《中庸》為子思所作,亦當明言之,乃全書中無一語及此,何耶?要之,辜氏之譯此書,謂之全無曆史上之見地可也。唯無曆史上之見地,遂誤視子思與孔子之思想全不相異。唯無曆史上之見地,故在在期古人之說之統一。唯無曆史上之見地,故譯子思之語以西洋哲學上不相幹涉之語。幸而譯者所讀者,西洋文學上之書為多,其於哲學所入不深耳。使譯者而深於哲學,則此書之直變為柏拉圖之語錄、康德之實踐理性批評,或變為斐希脫、解林之書,亦意中事。又不幸而譯者不深於哲學,故譯本中雖時時見康德之知識論及倫理學上之思想,然以不能深知康德之知識論,故遂使西洋形而上學中空虛廣莫之語充塞於譯本中。吾人雖承認《中庸》為儒家之形而上學,然其不似譯本之空廓,則固可斷也。又譯本中為發明原書,故多引西洋文學家之說,然其所引證者,亦不必適合。若再自哲學上引此等例,固當什伯千萬於此。吾人又不能信譯者於哲學上之知識狹隘如此,寧信譯者以西洋通俗哲學為一藍本,而以《中庸》之思想附會之,故務避哲學家之說,而多引文學家之說,以使人不能發見其真贓之所在。此又一說也。由前之說,則失之固陋。由後之說,則失之欺罔。固陋與欺罔,其病雖不同,然其不忠於古人則一也。故列論其失,世之君子,或不以餘言為謬乎。
此文作於光緒丙午,曾登載於上海《教育世界》雜誌。此誌當日不行於世,故鮮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檢理舊篋,始得之。《學衡》雜誌編者請轉載,因複覽一過。此文對辜君批評頗酷,少年習氣,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識,世間久有定論。此文所指摘者,不過其一二小疵。讀者若以此而抹殺辜君,則不獨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國維附記。
○自序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犬馬之齒已過。三十誌學以來,十有餘年,體素羸弱,不能銳進於學。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間,進步之跡,有可言焉。夫懷舊之感,恒篤於暮年;進取之方,不容於反顧。餘年甫壯,而學未成,冀一簣以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舉前十年之進步,以為後此十年、二十年進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勵之一道也。餘家在海寧,故中人產也。一歲所入,略足以給衣食。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兒時所不喜外,其餘晚自塾歸,每泛覽焉。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能形似而已。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恒怏怏,亦不能專力於是矣。二十二歲,正月始至上海,主《時務報》館任書記校讎之役。二月,而上虞羅君振玉等私立之東文學社成,請於館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焉,汪君許之。然館事頗劇,無自習之暇,故半年中之進步,不如同學諸子遠甚。夏六月,又以病足歸裏,數月而愈。愈而複至滬,則《時務報》館已閉。羅君乃使治社之庶務,而免其學資。是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餘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睽隔,自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其時擔任數學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亦未嚐不自笑也。顧君勤於教授。其時所用藤澤博士之算術、代數兩教科書,問題殆以萬計。同學三四人者,無一問題不解,君亦無一不校閱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變,學社解散。蓋餘之學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時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裏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亂稍定,羅君乃助以資,使遊學於日本。亦從藤田君之勸,擬專修理學,故抵日本後,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自是以後,遂為獨學之時代矣。體素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而此時為餘讀書之指導者,亦即藤田君也。次歲春,始讀翻爾彭之《社會學》及文之名。學海甫定《心理學》之半,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於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文特爾彭之《哲學史》。當時之讀此等書,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之道無異。幸而已得讀日文,則與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學概論》《哲學史》,次年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誌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銳,是歲前後讀二過。次及於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誌論》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誌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為通汗德哲學關鍵。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複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此則當日誌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書,亦時涉獵及之。近數年來為學之大略如此。顧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其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則二三時,多或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朋友談論,則涉獵雜書。唯此二三時間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而已。夫以餘境之貧薄而體之孱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餘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故書十年間之進步,非徒以為責他日進步之券,亦將以勵今之人,使不自餒也。若夫餘之哲學上及文學上之撰述,其見識文采亦誠有過人者,此則汪氏中所謂“斯有天致,非由人力,雖情苻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為世告焉。
○自序二前篇既述數年間為學之事,茲複就為學之結果述之。
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
今日之哲學界,自赫爾德曼以後,未有敢立一家係統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係統,自創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學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賓塞爾,但蒐集科學之結果或古人之說,而綜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謂可信而不可愛者也。此外所謂哲學家,則實哲學史家耳。以餘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亦有由焉,則填詞之成功是也。餘之於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餘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餘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餘之處。因詞之成功而有誌於戲曲,此亦近日之奢願也。然詞之於戲曲,一抒情,一敘事,其性質既異,其難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後者乎?但餘所以有誌於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裏計。此餘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誌乎是也。然目與手不相謀,誌與力不相副,此又後人之通病。故他日能為之與否,所不敢知。至為之而能成功與否,則愈不敢知矣。
雖然以餘今日研究之日淺而修養之力乏,而遽絕望於哲學及文學,毋乃太早計乎?苟積畢生之力,安知於哲學上不有所得,而於文學上不終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無成功,而得於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賞為消遣之法,以自逭於聲色貨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詩》雲“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此吾輩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創造之力,苟一日集於餘躬,則俟諸天之所為歟,俟諸天之所為歟!
○汗德像讚
人之最靈厥維天官。外以接物,內用反觀。小知間間,敝帚是享。群言淆亂,孰正其枉。大疑潭潭,是糞是除。中道而反,喪其故居。篤生哲人,凱尼之堡。息彼眾喙,示我大道。觀外於空,觀內於時。諸果粲然,厥因之隨。凡此數者,知物之式。存於能知,不存於物。匪言之艱,證之維艱。雲霾解駁,秋山巉巉。赤日中天,燭彼窮陰。丹鳳在霄,百鳥皆瘖。穀可如陵,山可為藪。萬歲千秋,公名不朽。光緒二十九年八月
○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美術者,天才之製作也”,此自汗德以來百餘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然天下之物,有決非真正之美術品而又決非利用品者,又其製作之人決非必為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製作之美術無異者,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欲知古雅之性質,不可不知美之普遍之性質。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雖物之美者,有時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視為美時,決不計及其可利用之點。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於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而美學上之區別美也,大率分為二種:曰優美,曰宏壯。自巴克及汗德之書出,學者殆視此為精密之分類矣。至古今學者對優美及宏壯之解釋,各由其哲學係統之差別而各不同。要而言之,則前者由一對象之形式不關於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於此對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藝術中普通之美,皆此類也。後者則由一對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馭之範圍,或其形式大不利於吾人,而又覺其非人力所能抗,於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觀念外,而達觀其對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風、雷雨,藝術中偉大之宮室、悲慘之雕刻象、曆史畫、戲曲、小說等,皆是也。此二者,其可愛玩而不可利用也同。若夫所謂古雅者則何如?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則一切優美,皆存於形式之對稱變化及調和。至宏壯之對象,汗德雖謂之無形式,然以此種無形式之形式能喚起宏壯之情,故謂之形式之一種,無不可也。就美術之種類言之,則建築、雕刻、音樂之美之存於形式,固不俟論。即圖畫、詩歌之美之兼存於材質之意義者,亦以此等材質適於喚起美情故,故亦得視為一種之形式焉。釋迦與馬利亞莊嚴圓滿之相,吾人亦得離其材質之意義,而感無限之快樂,生無限之欽仰。戲曲、小說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對文章之方麵言之,則為材質;然對吾人之感情言之,則此等材質又為喚起美情之最適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屬於美之對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質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即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夫然,故古雅之致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以自然但經過第一形式,而藝術則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創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即同一形式也,其表之也各不同。同一曲也,而奏之者各異。同一雕刻、繪畫也,而真本與摹本大殊。詩歌亦然。“夜闌更炳燭,相對如夢寐”(杜甫《羌村》詩)之於“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鷓鴣天》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詩·衛風·伯兮》)之於“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歐陽修《蝶戀花》詞)其第一形式同,而前者溫厚、後者刻露者,其第二形式異也。一切藝術無不皆然。於是有所謂雅俗之區別起。優美及宏壯必與古雅合,然後得顯其固有之價值。不過,優美及宏壯之原質愈顯,則古雅之原質愈蔽。然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壯者,實以表出之之雅故,即以其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
雖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茅茨土階與夫自然中尋常瑣屑之景物,以吾人之肉眼觀之,舉無足與於優美若宏壯之數,然一經藝術家(繪畫若詩歌)之手,而遂覺有不可言之趣味。此等趣味,不自第一形式得之,而自第二形式得之無疑也。繪畫中之布置屬於第一形式,而使筆使墨則屬於第二形式。凡以筆墨見賞於吾人者,實賞其第二形式也。此以低度之美術(如法書等)為尤甚。三代之鍾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於第二形式。吾人愛石刻,不如愛真跡。又其於石刻中愛翻刻,不如愛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於雕刻、書畫之品評,曰神、曰韻、曰氣、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學亦然。古雅之價值,大抵存於第二形式。西漢之匡、劉,東京之崔、蔡,其文之優美宏壯,遠在賈、馬、班、張之下,而吾人之嗜之也,亦無遜於彼者,以雅故也。南豐之於文,不必工於蘇、王,薑夔之於詞,且遠遜於歐、秦,而後人亦嗜之者,以雅故也。由是觀之,則古雅之原質為優美及宏壯中不可缺之原質,且得離優美宏壯而有獨立之價值,則固一不可誣之事實也。然古雅之性質,有與優美及宏壯異者。古雅之但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既如上文所論矣,至判斷古雅之力,亦與判斷優美及宏壯之力不同。後者先天的,前者後天的、經驗的也。優美及宏壯之判斷之為先天的判斷,自汗德之《判斷力批評》後,殆無反對之者。此等判斷既為先天的,故亦普遍的、必然的也。易言以明之,即一藝術家所視為美者,一切藝術家亦必視為美。此汗德之所以於其美學中預想一公共之感官者也。若古雅之判斷則不然。由時之不同,而人之判斷之也各異。吾人所斷為古雅者,實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斷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於近世之製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故古雅之判斷,後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與近世大異,故吾人睹其遺跡,不覺有遺世之感隨之。然在當日,則不能若優美及宏壯,則固無此時間上之限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