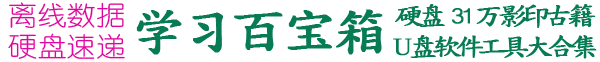在线文库
| 傳十五 ◄ | 東觀漢記 卷21 載記 |
► 散句 |
|
|
載記[1]
王常[2]
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問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范曄《後漢書》卷一五〈王常傳〉李賢注
以常行南陽太守事,[3]誅不從命,封拜有功。范曄《後漢書》卷一五〈王常傳〉李賢注
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4]《初學記》卷一七
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苗虛。[5]范曄《後漢書》卷一五〈王常傳〉李賢注
王常為橫野大將軍,[6]位次與諸將絕席。[7]《書鈔》卷一三三
山桑侯王常孫廣坐楚事,國除。[8]《御覽》卷二○一
- ↑ 「載記」,《史通.題目篇》云:「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
- ↑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范曄《後漢書》卷一五有傳。又見汪文臺輯司馬彪《續漢書》卷二。據范書《王常傳》載:「王莽末,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王常屬下江,在《東觀漢記》中當載在載記。
- ↑ 「以常行南陽太守事」,此句原無,范曄《後漢書.王常傳》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今據增補。
- ↑ 「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忠」字原誤作「中」,聚珍本作「忠」,《類聚》卷二0引同,今據改。此條《御覽》卷二四○、卷四一八亦引,文字大同小異。
- ↑ 「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苗虛」,范曄《後漢書.王常傳》云:建武五年,「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云:「《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本條即據此輯錄。
- ↑ 「王常為橫野大將軍」,此為建武七年事,見范曄《後漢書.王常傳》。
- ↑ 「絕席」,獨坐一席,以示地位尊顯。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此條《類聚》卷六九、《御覽》卷七○九亦引。
- ↑ 「國除」,事在永平十四年。
劉盆子[1]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2]聚珍本
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眾拜,[3]恐懼啼泣。[4]從劉俠卿居,為盆子制朱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5]盆子朝夕朝,俠卿禮之。數祠城陽景王,使盆子乘軍中鮮車大火馬,[6]至祠所,盆子時欲出從牧兒,俠卿怒止之。軍入左馮翊,至長安舍,盆子乘白蓋小車,有尚書一人,亦小車絳袍衣裳相隨,軍中皆笑。諸牧兒共呼車曰:「盆子在中。」時欲驅出,前車不肯避也。《書鈔》卷一三九
使盆子乘車入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拔庭中蘆菔根,[7]捕池魚而食之。[8]聚珍本
更始死后,赤眉轉從南山下,號稱百萬眾。盆子乘王者車,駕三馬,從數百騎,罷歌吹者廩食,[9]棄其數車道中,侍從者稍落。[10]《書鈔》卷一三九
劉盆子兄式侯旦請上曰:[11]「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君以不死耳。」《書鈔》卷一一九
劉盆子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12]奉高皇帝璽綬,[13]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甲兵弩矢矰,積城西門,[14]適與熊耳山等。[15]《書鈔》卷一一九
- ↑ 「劉盆子」,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范曄《後漢書》卷一一有傳。又見汪文臺輯司馬彪《續漢書》卷二、袁山松《後漢書》。
- ↑ 「三老等皆稱臣」,此條不知聚珍本從何書輯錄。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云: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與此大同小異。
- ↑ 「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眾拜」,原無上二句,「卒見眾拜」作「盆子見眾拜」,今據聚珍本和《御覽》卷三七三所引增改。此三句《御覽》卷四八八引作「劉盆子字于,季十五,被髮徒跣,卒見眾拜」,字有訛誤。「卒」,與「猝」字同。
- ↑ 「懼」,《御覽》卷三七三、卷四八八引作「怖」。
- ↑ 「為盆子」,聚珍本作「俠卿為」。
- ↑ 「使盆子乘軍中鮮車大火馬」,此句至「前車不肯避也」一段文字聚珍本無。
- ↑ 「拔」,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御覽》卷四八六引袁山松《後漢書》皆作「掘」。
- ↑ 「捕池魚而食之」,此條不知聚珍本從何書輯錄。字句與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微異。
- ↑ 「罷歌吹者廩食」,「吹」字下原有「之」字,係衍文,今去刪。
- ↑ 「侍從者稍落」,此條姚本、聚珍本皆未輯錄。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建武二年,……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可與此相參證。
- ↑ 「劉盆子兄式侯旦請上曰」,此句姚本、聚珍本作「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係據陳禹謨刻本《書鈔》輯錄,與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文字全同。「式侯」,劉恭,劉盆子兄,隨樊崇等降更始時,封為式侯。見范書《劉盆子傳》。
- ↑ 「劉盆子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原無「二十餘萬人詣宜陽」八字,《初學記》卷二二引云:「劉盆子與丞相已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御覽》卷三五五引云:「劉盆子與丞相二十萬人詣宜陽降。」今據增補。此句姚本作「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聚珍本同,惟刪「劉」字。
- ↑ 「奉高皇帝璽綬」,「帝」字下姚本、聚珍本有「傳國」二字,陳禹謨刻本《書鈔》卷一一九引同。
- ↑ 「賊皆輸鎧甲兵弩矢矰,積城西門」,此二句姚本、聚珍本作「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陳禹謨刻本《書鈔》卷一一九引同,惟「仗」作「甲」。
- ↑ 「適」,姚本、聚珍本無此字,陳禹謨刻本《書鈔《卷一一九引同。《初學記》卷二二,《御覽》卷三三九、卷三五五皆引作「高」。《御覽》卷四二、《事類賦》卷七引作「積」。「等」,《初學記》卷二二,《御覽》卷四二、卷三三九、卷三五五引同。姚本、聚珍本作「齊」,陳禹謨刻本《書鈔》卷一一九引亦作「齊」。
樊崇
樊崇,[1]字細君。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劉盆子傳〉李賢注
崇同郡東莞人逄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稚,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4]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劉盆子傳〉李賢注
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文選》卷一○潘岳〈西征賦〉李善注
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士多凍死。[5]《書鈔》卷一五二
光武作飛虻箭以攻赤眉。[6]《文選》卷一六潘岳〈閑居賦〉李善注
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7]《御覽》卷八四一
- ↑ 「樊崇」,琅邪人,其事見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劉盆子傳〉。
- ↑ 「王莽天鳳五年」,此句聚珍本未輯錄。
- ↑ 「樊崇起兵於莒」,此句下尚有「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赤眉」三句,因與下複出,今刪去。
- ↑ 「復引從崇」,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李賢注云:「《東觀記》曰逄,音龐。徐宣字驕稚,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此條即據李賢注,又酌取范書文句輯錄。《通鑑》卷三九胡三省引「《東觀記》曰逄,音龐」二句作注。王應麟《急就篇》補注引「《東觀記》:徐宣字驕稚」二句作注。《四庫全書》考證云:「考前《漢書.王莽傳》,赤眉力子都、樊崇等起於琅邪,本書不載子都名,當是闕佚。」
- ↑ 「士多凍死」,「士」字下聚珍本有「卒」字,陳禹謨刻本《書鈔》同。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云:赤眉「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與此為同一事。
- ↑ 「光武作飛虻箭以攻赤眉」,此條《玉海》卷一五○亦引,僅無「以」字。「飛虻」,箭名。《文選》卷一六潘岳〈閑居賦〉李善注引《方言》云:「凡箭三鎌,謂之羊頭。三鎌六尺,謂之飛虻。」
- ↑ 「升」,聚珍本作「斗」。袁宏《後漢紀》卷四建武三年云:「豪傑往往屯聚,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百姓飢餓,黃金一斤五斗穀。」則「升」字當作「斗」。
呂母
海曲有呂母者,[1]子為縣吏,[2]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貰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裘,[3]不問多少。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相聚得數十百人,[4]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以祭其子冢也。[5]《御覽》卷四八一
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6]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劉盆子傳〉李賢注
- ↑ 「呂母」,其事見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劉盆子傳〉。
- ↑ 「子為縣吏」,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李賢注引《續漢書》云:「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
- ↑ 「裘」,姚本、聚珍本作「裝」,《類聚》卷三三引同。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作「裳」。
- ↑ 「數十百人」,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同。姚本、聚珍本作「數百人」,《類聚》卷三三引亦作「數百人」。
- ↑ 「以祭其子冢也」,此條姚本、聚珍本係據《類聚》卷三三所引輯錄,字句較此簡略。
- ↑ 「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范曄《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呂母欲為子報仇,「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其下李賢引此句作注。李賢注又云:「搤,音於責反,力可搤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搤』與『猛』相類也。」
隗囂
隗囂既立,[3]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4]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5]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6]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7]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御覽》卷四六一
以王莽篡逆,[8]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9]祝畢,有司穿坎於庭,割牲而盟。《御覽》卷四八○
光武與隗囂書曰:[10]「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11]托驥之尾,得以絕群。」《御覽》卷九四四
隗囂將王元說囂曰:[12]「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13]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14]《類聚》卷二五
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15]范曄《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李賢注
隗囂,故宰相府掾吏,[16]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之也。[17]《書鈔》卷一○三
光武賜隗囂書曰:[18]「吾年已三十餘,[19]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20]《文選》卷四二魏文帝〈與吳質書〉李善注
漢圍隗囂,[21]囂窮因。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22]「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御覽》卷四三八
時民饑饉,乃噉弩煮履。[23]聚珍本
建武九年正月,[24]隗囂病餓,[25]出城餐糗糒,[26]腹脹恚憤而死。《書鈔》卷一四七
隗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27]《御覽》卷四八○
- ↑ 「隗囂」,范曄《後漢書》卷一三有傳。又見汪文臺輯司馬彪《續漢書》卷二。
- ↑ 「天水人也」,此句下尚有「以王莽篡逆,復漢之祚」云云數句,已按敘事先後移至下文。
- ↑ 「隗囂既立」,謂囂為上將軍。范曄《後漢書.隗囂傳》載:「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
- ↑ 「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便」字姚本、聚珍本作「使」,《類聚》卷二五引同。「師」字原作「帥」,姚本、聚珍本作「師」,《類聚》卷二五引同,今據改。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 ↑ 「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起今」二字原誤倒作「今起」,姚本、聚珍本作「起今」,《類聚》卷二五引同,今據乙正。
- ↑ 「神道設教」,《易.觀卦彖辭》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 ↑ 「以致其肅敬」,此句上原有「陛下」二字,係衍文。囂時為上將軍,方望不得以「陛下」相稱。上文稱「足下」,與囂身份相埒。聚珍本無此二字,范曄《後漢書.隗囂傳》同,今據刪。
- ↑ 「以王莽篡逆」,此當與上條連讀,所敘事相承。
- ↑ 「史奉璧而告」,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囂從方望之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李賢注云:「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 ↑ 「光武與隗囂書」,建武三年,囂上書詣闕,光武以殊禮相待。當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相通,擊三輔。囂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呂鮪敗走,光武帝即報以手書。見范曄《後漢書.隗囂傳》。
- ↑ 「三數步」,聚珍本同,《記纂淵海》卷一○○引作「十步」,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作「數步」。
- ↑ 「隗囂將王元說囂」,建武五年,光武帝遣來歙勸囂遣子入侍,於是囂遣長子恂隨歙詣闕。而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事漢,故說囂「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事見范曄《後漢書.隗囂傳》。
- ↑ 「完」,原誤作「見」,姚本、聚珍本作「完」,《御覽》卷四六一引同,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亦作「完」,今據改正。
- ↑ 「囂然其計」,此條《初學記》卷七、《類聚》卷六、《六帖》卷九、《御覽》卷七四、《記纂淵海》卷四三、《合璧事類》卷八亦引,字句較簡略。
- ↑ 「東詣京師」,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其下李賢引此條文字作注。
- ↑ 「故宰相府掾吏」,姚本、聚珍本無「相」字,《類聚》卷五八引同。
- ↑ 「士大夫莫不諷誦之也」,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云:建武「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與此條所述略有不同。
- ↑ 「光武賜隗囂書」,建武六年,公孫述攻南郡,光武帝詔囂從天水伐蜀,囂不從命,而使王元侵三輔。光武帝遂使來歙賜隗囂書。事詳范曄《後漢書.隗囂傳》。
- ↑ 「吾年已三十餘」,此句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作「吾年垂四十」。
- ↑ 「厭浮語虛辭耳」,此句下聚珍本有如下一條文字:「岑彭與吳漢圍囂於西城,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為白。』」姚本《隗囂傳》亦收此條。按此條文字不當入《隗囂傳》,而應入《岑彭傳》,范曄《後漢書.岑彭傳》載光武帝敕彭書。
- ↑ 「漢圍隗囂」,建武八年,吳漢與岑彭圍隗囂於西城。范曄《後漢書.岑彭傳、《吳漢傳》、《隗囂傳》皆載此事。
- ↑ 「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據范曄《後漢書.隗囂傳》,當時隗囂大將王捷在戎丘。
- ↑ 「乃噉弩煮履」,此條不知聚珍本從何書輯錄。
- ↑ 「建武九年正月」,此句原無,聚珍本有,《御覽》卷四八六引亦有,今據增補。
- ↑ 「病餓」,姚本、聚珍本作「病且餓」,與陳禹謨刻本《書鈔》同。范曄《後漢書.隗囂傳》亦作「病且餓」。
- ↑ 「糗」,原無此字,姚本、聚珍本有,《御覽》卷四八六、卷八六○引亦有,今據增補。
- ↑ 「正君臣之義」,聚珍本注云:「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王元[1]
元,杜陵人。范曄《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李賢注
- ↑ 「王元」,范曄《後漢書》無傳。據范書《光武帝紀》和《隗囂傳》所載,元字惠孟,為隗囂大將軍。建武九年,隗囂死。十年,元奔蜀,為公孫述將。十一年,降漢。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公孫述
公孫述,[1]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范曄《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李賢注
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加秩為郎焉。范曄《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李賢注
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2]《書鈔》卷七八
初,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3]范曄《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李賢注
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4]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5]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為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6]《御覽》卷四六一
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為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御覽》卷四○○
公孫述,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稱尊號,改元曰龍興。《御覽》卷九二九
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御覽》卷一七六
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7]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御覽》卷三七○
光武與述書曰:[8]「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范曄《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李賢注
荊邯見東方漸平,[9]兵且西向,說公孫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10]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跡,立錐之地,於戰陣之中,[11]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踰於卻就於滅亡。[12]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13]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寸之柄,[14]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御覽》卷四六一
隗囂敗,公孫述懼,欲安其眾。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御覽》卷四九四
漢兵守成都,[15]公孫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16]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御覽》卷三四一
- ↑ 「公孫述」,范曄《後漢書》卷一三有傳。又見汪文臺輯司馬彪《續漢書》卷二。據范曄《後漢書.班固傳》、《史通古今.正史篇》記載,在《東觀漢記》中,公孫述列入載記。此下三句原無,聚珍本有,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同,據本書體例亦當有此三句,今據增補。
- ↑ 「使兼治五縣政」,此條姚本、聚珍本皆未輯錄。「兼」,原誤作「廉」,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今據校改。
- ↑ 「自稱輔漢將軍」,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其下李賢引此條文字作注。此句下姚本、聚珍本有「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三句,係括取范書大意增補。
- ↑ 「屠」,原誤作「屬」,聚珍本作「屠」,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同,今據改正。
- ↑ 「則」,此字原脫,聚珍本有此字,《類聚》卷二五引同,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亦有此字,今據增補。補「則」字,方與下句文例一致。
- ↑ 「述遂自立為天子」按敘事順序,此句當在下文「公孫述,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稱尊號」諸句之下。
- ↑ 「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 ↑ 「光武與述書」,此與上條所載光武帝賜述書當為同一事。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述亦好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引《錄運法》云:『廢昌帝,立公孫。』……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其下李賢引「光武與述書曰」云云作注。
- ↑ 「荊邯見東方漸平」,原脫「見」字。此句聚珍本作「平陵人荊邯以東方漸平」,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作「述騎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今據補「見」字。
- ↑ 「古今所不能廢也」,「所」字下原有「有」字,係衍文,聚珍本無,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亦無此字,今據刪。
- ↑ 「於戰陣之中」,「於」字上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有「起」字,於義較長。
- ↑ 「踰於卻就於滅亡」,此句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同,聚珍本作「愈於坐而滅亡」。
- ↑ 「堅守」,聚珍本作「守堅」。按「堅守」二字義長,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作「堅守」。
- ↑ 「今東帝無尺寸之柄」,此句以下一段文字原無,聚珍本有,今據增補。此段文字不知聚珍本輯自何書,字句與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全同。「今東帝無尺寸之柄」云云,與上荊邯說公孫述之言並非一時。據范書所載,「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遂說公孫述擊漢。公孫述徵求群臣意見,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於是荊邯對以「今東帝無尺寸之柄」云云。
- ↑ 「漢兵守成都」,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云:建武十二年「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
- ↑ 「市橋」,范曄《後漢書.公孫述傳》李賢注云:「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
延岑[1]
築陽縣人。范曄《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李賢注
延岑上光武皮襜褕,[2]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御覽》卷六九三
田戎
田戎,[1]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2]范曄《後漢書》卷一七〈岑彭傳〉李賢注
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3]范曄《後漢書》卷一七〈岑彭傳〉李賢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