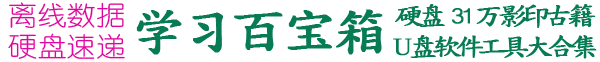丛部 > 台湾文献丛刊140 续修台湾县志 > 弁言
這本「續修臺灣縣志」,計有下列各種稿本與板本:
(一)初稿:即謝金鑾、鄭兼才纂修的原稿。
(二)薛刻本:即薛志亮的初刻本,刊於清嘉慶十二年。據「藝文(三)」薛志亮族人薛約「臺灣竹枝詞二十首」序,雲廬(薛志亮字。一作耘廬)續修臺灣縣志成,郵歸付梓;薛約因檢舊作「竹枝詞」,附入末卷。又據「補刻本」(見下)卷末按語:『薛君約「竹枝詞」二十首,摘存五首,為此志鋟板姑蘇之證』。由此可知「薛刻本」是郵歸姑蘇出版的(「後跋」亦提及)。照理,「薛刻本」應屬「初稿」,但因薛約的加入「竹枝詞」,已與「初稿」有別。
(三)訂稿:即謝金鑾就「初稿」改訂的,故稱「訂稿」,又稱「訂本」。
(四)補刻本:即鄭兼才根據「薛刻本」及「訂稿」增刪的板本,刊於道光元年。「補刻本」增刪的情形,鄭兼才除以「後跋」說明外,並在書中分別加有「按語」。其出入較多者,則為「外編」「叢談」刪去「檳榔閒話」與「識小錄」八條及「藝文(三)」刪去「在局」諸詩詞。末卷「按語」有云:『至同局詩,謝君來書謂:「名志、佳志必不收現在詩。……」云云;茲已鋟成,刪補俱難,盡照「訂稿」;惟在局諸詩,悉如來書,不論「初稿」所收及未收添入者,一概刪去』。
按本書曾列為「臺灣研究叢刊」第六一種印行,當時是完全根據「補刻本」的;現在我們為保存史料起見,凡「薛刻本」「外編」與「藝文(三)」被刪去的部份,仍行補入。這在「義例」上,也許不盡妥當;但我們編印「文獻叢刊」的目的是在提供史料,「義例」不是我們所重視的。(周憲文)
(一)初稿:即謝金鑾、鄭兼才纂修的原稿。
(二)薛刻本:即薛志亮的初刻本,刊於清嘉慶十二年。據「藝文(三)」薛志亮族人薛約「臺灣竹枝詞二十首」序,雲廬(薛志亮字。一作耘廬)續修臺灣縣志成,郵歸付梓;薛約因檢舊作「竹枝詞」,附入末卷。又據「補刻本」(見下)卷末按語:『薛君約「竹枝詞」二十首,摘存五首,為此志鋟板姑蘇之證』。由此可知「薛刻本」是郵歸姑蘇出版的(「後跋」亦提及)。照理,「薛刻本」應屬「初稿」,但因薛約的加入「竹枝詞」,已與「初稿」有別。
(三)訂稿:即謝金鑾就「初稿」改訂的,故稱「訂稿」,又稱「訂本」。
(四)補刻本:即鄭兼才根據「薛刻本」及「訂稿」增刪的板本,刊於道光元年。「補刻本」增刪的情形,鄭兼才除以「後跋」說明外,並在書中分別加有「按語」。其出入較多者,則為「外編」「叢談」刪去「檳榔閒話」與「識小錄」八條及「藝文(三)」刪去「在局」諸詩詞。末卷「按語」有云:『至同局詩,謝君來書謂:「名志、佳志必不收現在詩。……」云云;茲已鋟成,刪補俱難,盡照「訂稿」;惟在局諸詩,悉如來書,不論「初稿」所收及未收添入者,一概刪去』。
按本書曾列為「臺灣研究叢刊」第六一種印行,當時是完全根據「補刻本」的;現在我們為保存史料起見,凡「薛刻本」「外編」與「藝文(三)」被刪去的部份,仍行補入。這在「義例」上,也許不盡妥當;但我們編印「文獻叢刊」的目的是在提供史料,「義例」不是我們所重視的。(周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