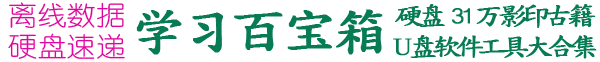在完成了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之后,前八十回贾雨村就不再正式出场了,而是通过别人的口介绍,他如何在坏男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官却越做越大,其秘诀就是巴结贾府这种显赫人家。最主要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三十二回贾宝玉正和史湘云、袭人等说话,下人来说,贾政让宝玉去见贾雨村。贾宝玉非常讨厌这个家伙,说他“回回定要见我”。可想而知已经由地方官成为京官的贾雨村不但常跑贾府,而且知道光讨好贾政还不够,还要在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身上下功夫。套用一句现在的话,贾雨村讨好贾宝玉,是在做期货呢!四十八回还通过平儿的叙述写到,贾雨村与贾府结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最新一件是,贾赦看中了石呆子收藏的20把古扇,千方百计要弄到手,石呆子誓死不卖。结果是贾雨村“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五十三回提到贾雨村升了大司马(相当于兵部尚书),而且协理军机,参赞朝政,那就位列中枢了。后来他有降有升,直到肩上枷锁扛。总之,《红楼梦》通过贾雨村一生的经历,写出了封建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某一类知识分子生涯的全过程:苦读、赶考、高中、为官、升官、革职、复出、高升、获罪。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就在贾雨村为官时期。一个才华出众、胸怀大志、颇有骨气、本来完全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好事的文人,逐渐被黑暗的官场腐蚀成为一个徇私枉法、人性泯灭、恩将仇报的大坏蛋。这样,贾雨村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人物本身,而是突出了这个被曹雪芹反复称为“末世”的社会的罪恶。社会环境腐蚀了好人,保护和得志的是坏人,那么结论就只能是:这个社会环境必须改变!这个被称为“盛世”而实际上是“末世”的社会必须灭亡!
因此《红楼梦》反映的社会是,一方面它不允许贾宝玉这样的优秀分子发展,另一方面它腐蚀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贾雨村这样的人,而使得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人如鱼得水。老一代不能为下一代楷模(贾赦和贾琏、贾珍和贾蓉);相反,老一代还以自己的丑恶行为毒害腐蚀着下一代,那么,当然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的社会自然应该灭亡。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坏男人的描写,主要并不在于批判这些个人,矛头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为“盛世”的末世。
后记周思源看红楼后记十年前的此时,当我正准备“改邪归正”,回去继续弄现当代文艺研究与评论,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的张庆善(现任会长)着急地说:“你可别!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处于上升时期。”他告诉我,这次邀请我去参加五月底的福建南平会议,是冯其庸先生点的名,李希凡先生也去。而我的不少观点和冯先生、李先生等前辈与时贤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1994年我才第一次参加红学界的学术会议(山东莱阳),南平会议是第二次,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写了《红楼锁钥话“受享”》一文。我的观点,至少大会主席、时任红学会秘书长、红学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杜景华先生是完全不赞成的,但在南平会议上景华先生不仅让我“受享”发言不受时间限制,而且让我主持了两个小时的大会。文稿在下一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结果此文成为我第二部红学著作《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的开始。我衷心地感谢红学界的宽容,没有众多师友多年来的帮助、鼓励、抬爱与提携,多次为我创造条件,我决不可能沿着自己的路子继续走到今天。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不久,我就有幸和他们合作,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百家讲坛”有一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的年轻精干的团队,他们的诚信、敬业、好学,对节目精益求精,对演讲者的尊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特别感谢“百家讲坛”栏目的前任和现任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和万卫先生,以及孟庆吉、刘德华、张长虹、张嘉彬、高虹、马琳、魏学来、兰培胜等各位编导和其他工作人员。承他们青目,我这个红学界的票友才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荧屏演讲《红楼梦》,并夹塞讲了一些其他题目。“百家讲坛”在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之间的平衡点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我尤其要感谢丛丛慨允拨冗赐序。
我有三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傅光明研究员不但是节目的策划,而且是主持人。正是由于在这里演讲,使我对如何将学术问题讲得雅俗共赏做了一些尝试。如果没有“在文学馆听讲座”这个高雅而结实的桥梁,我和“百家讲坛”的联系有可能就中断了。对光明的帮助,我深表谢意。这本书会出版虽然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先生约稿之快仍然使我吃惊。他的谦和、热诚,专业知识的丰富,令人感动。我们只通了20分钟电话就敲定了一切。非常感谢他和中华书局的领导以及其他编辑决定此书迅速出版而且做得十分漂亮。
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稿子赶出来,而且居然还能够照样睡懒觉。
因此《红楼梦》反映的社会是,一方面它不允许贾宝玉这样的优秀分子发展,另一方面它腐蚀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贾雨村这样的人,而使得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人如鱼得水。老一代不能为下一代楷模(贾赦和贾琏、贾珍和贾蓉);相反,老一代还以自己的丑恶行为毒害腐蚀着下一代,那么,当然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的社会自然应该灭亡。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坏男人的描写,主要并不在于批判这些个人,矛头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为“盛世”的末世。
后记周思源看红楼后记十年前的此时,当我正准备“改邪归正”,回去继续弄现当代文艺研究与评论,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的张庆善(现任会长)着急地说:“你可别!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处于上升时期。”他告诉我,这次邀请我去参加五月底的福建南平会议,是冯其庸先生点的名,李希凡先生也去。而我的不少观点和冯先生、李先生等前辈与时贤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1994年我才第一次参加红学界的学术会议(山东莱阳),南平会议是第二次,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写了《红楼锁钥话“受享”》一文。我的观点,至少大会主席、时任红学会秘书长、红学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杜景华先生是完全不赞成的,但在南平会议上景华先生不仅让我“受享”发言不受时间限制,而且让我主持了两个小时的大会。文稿在下一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结果此文成为我第二部红学著作《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的开始。我衷心地感谢红学界的宽容,没有众多师友多年来的帮助、鼓励、抬爱与提携,多次为我创造条件,我决不可能沿着自己的路子继续走到今天。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不久,我就有幸和他们合作,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百家讲坛”有一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的年轻精干的团队,他们的诚信、敬业、好学,对节目精益求精,对演讲者的尊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特别感谢“百家讲坛”栏目的前任和现任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和万卫先生,以及孟庆吉、刘德华、张长虹、张嘉彬、高虹、马琳、魏学来、兰培胜等各位编导和其他工作人员。承他们青目,我这个红学界的票友才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荧屏演讲《红楼梦》,并夹塞讲了一些其他题目。“百家讲坛”在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之间的平衡点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我尤其要感谢丛丛慨允拨冗赐序。
我有三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傅光明研究员不但是节目的策划,而且是主持人。正是由于在这里演讲,使我对如何将学术问题讲得雅俗共赏做了一些尝试。如果没有“在文学馆听讲座”这个高雅而结实的桥梁,我和“百家讲坛”的联系有可能就中断了。对光明的帮助,我深表谢意。这本书会出版虽然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先生约稿之快仍然使我吃惊。他的谦和、热诚,专业知识的丰富,令人感动。我们只通了20分钟电话就敲定了一切。非常感谢他和中华书局的领导以及其他编辑决定此书迅速出版而且做得十分漂亮。
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稿子赶出来,而且居然还能够照样睡懒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