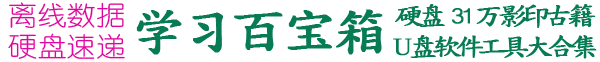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可笑今人动辄风生,借名公愤,不知激出多少事来。大则震撼朝廷,小则武断乡曲。这公愤可是当耍发得的?我以为愤而不公,仗着一股血气;公而不愤,何异脂粉妇人?若真正公愤,也博得个青史题名,口碑载道。
气节人人妄自矜,一朝遇事也风生。
身尔转念真堪惜,若个刚肠亘古今。 叵耐古今天下最可恼的,小人得令,乘权使势,威福生死,真是炙手可热。随有一伙呵脬捧腿的,也就狐假虎威,那小人气焰一发热腾腾当不得了。若是把守清谨的人,只是各行其道。我也不随波逐流,我也不吹毛求疵。如阳货欲见孔子,朱文公注得绝好,君子之待小人不恶而严也,恐疾之已甚,不免事外生事。这样说起来,趋和的趋和,养高的养高,终不然听凭小人煽虐天下,更有何事赖着轰轰烈烈丈夫表表奇男子。虽然这却大难,纲常胜事,气节快举,怎能够事到其间,利害不摇,生死不撼,把身子推作孤注,轻于一掷。况是以下不三不四的小民百姓,纲常气节与他有甚相干。正是: 当场个个奇男子,转眼乔妆妾妇行。
说只如此,气性到底人人有的。却怎么:
天启年间,魏阉作耗起来,势不可当。缙绅大夫,非惟没有力量救正剪除,反有作为鹰犬,遇着弹论他的。从而排挤下石,敲朴成招,衣冠体面,文章生气,一些都讲不起了。朝中文武,津要官员,大半抹落脸来,乞怜摇尾。其时做造假旨,校尉横出。无论当事官府,遭其荼毒;即标下士夫,借事蔓延,污蔑锻炼,也没有一夜得安枕的。 一日,忽然差出校尉数名,向苏州地方拿人。开读圣旨,自司道府县,个个怀着鬼胎,咬牙咇卟,外边又有人山人海,围绕打听。正是: 日间不干亏心事,半夜敲门也吃惊。
不料开读旨完,沸传要拿某人,要拿某人,彼时三三两两,即有为他叫冤叫屈的,道犹未了,昕得一片喊响,跳出一伙豪杰。时方天雨,也有拿着砖头的,也有拿着木屐的,也有钉靴乱踢的,也有伞柄肥鞭的,就是雨点雪片一般,俱向校尉乱打,不分太阳肋扇。各官各府,衙门人役, 晓得民变,乱呼乱叫,只好救护本官,那里还敢禁止。只见那些人:
凶眉倒豁,人人拼命争先;恶眼圆睁,个个舍生取义。如当公战,以挟私仇。 一拳复一拳,气断多时拳不歇;一脚又一脚,死已半日脚仍加。
可怜几个校尉,不消半个时辰,打做肉酱。官府慌了,随即安抚百姓,只叫认查个把做头的,再处其余,不得混拿。看官们,你说这些官府内中,不知多少魏阉亲人在内,但目击民变,恐怕此时雷厉风行,一发变生不测。但只是魏阉声势,便是他的鸡犬,热气也呵他一口不得。况又有些甚么圣旨在内,各官面面相觑,正没一个妥当局面。只见人声乱嚷嚷中,几个高声叫喊:“是我打死!是我打死!”劈条人路,跪在官府面前,共有五个。连不上十四五岁瘌痢荒荒一个小使也在里边。官府尚自分付,只要一名。那五人怒愤愤的争前认首,各将凶器口供。颜佩韦等端端正正五名即刻锁押收监。看官,你看校尉赍旨,要拿周顺昌等进京,其时两榜同年,当道长官,尚没一个出头痛恤,却与这般平民何干?做出这样轰轰烈烈,直到身正典刑,尚且谈笑自若。此事声震朝野,不知多少衣冠士夫,汗流浃背。如此节义,却让没有半点墨水的攘臂争光。这叫做:
衣冠不任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 看官们,当时魏阉煽毒,暗暗切齿的难道没有,那有明目张胆,这般痛快。然尚说道:眼见是非颠倒,皂白不分,一时血气,睛眼出火,做个舍手,传名千古燥脾的奇事。如今更有一件希罕的新文,却在魏阉相隔三四年,又从没要紧戏耍场中,冷灰爆出一个热栗来。一向人岂不闻,那知其中还有许多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层层折折的因由。犹如:
古镜尚蒙尘,奇人不遍闻。 开尘磨镜叟,演义胜丹青。
口口口口一朝晏驾,崇祯御极。把从前黑漆漆不由分说的陷人坑,一旦扒平。上朝下野,也该报他一个民和年丰了。不知甚么缘故,连年间或水或旱,百姓流离。若是守株待兔的,九个饿杀十个。有些薄技微长的,除非是东奔西走,方才过得日子。正是:
不将辛苦易,难赚世间财。
话表南京城内,有个太学,姓蒋名有筠,号淇修。年三十余,有子方才十岁。祖父甲科,族中叔伯弟兄,科甲贡监,不下十人。淇修援例,父兄要他进取捷径,省得零碎考试,小题分心,也不是团于兰一段真正白木头。兼他天资颖悟,苦志攻书,你说他是科甲两字肯不放在心坎儿上的。但只因他家事繁重,交际颇多。田地房产上的差徭粮税,见年里长,也讨个源源而来。读书身分,也毕竟吃些亏了。以此功名不得遂意。每有浪迹江湖,结识异人之志。却有一个总角同窗,八拜订盟的,姓沙名原,字尔澄。祖籍真回教。其父沙象坤,曾发乡榜,周旋世务,只得圆融出教。尔澄幼与淇修笔研有年,两人志同道合,吃尽灯窗滋味。却是: 埋头经史三冬足,不见青藜借火燃。 淇修京缘羁绊,不得尽兴交游。尔澄文事既不得意,孑身聊落,到处穷途,又是淇修接过家里。尔澄自愧年纪三十,不采一芹,但因家事凄凉,欲辞不得。却有一件胎里疾,不修边幅,任侠负气。每见人有恃势凌物,欺压良善的,也就奋不顾身,他便下老实不平起来。就是读着书史中冤抑的事,便击案而起,破涕牢骚。看到怨愤发雪田地,又仰天大笑,呼酒破闷,开怀歌唱。伏侍书童,说他是失心风的书呆。又怕他难捏鼻头的性儿,况是家主尚且周旋。以此要长要短,就似呼风唤雨的一般,并不敢半点的违拗。正是:
堂上绸缪朱履客,阶前若个不殷勤。
却说蒋家后园五间书楼,上上下下,有的是牙签万轴,锦帙千缃。尔澄涉猎之外,更有报房日送。却是朝中时事,随到随阅。淇修每到晚闻,必梯己与尔澄小酌,从他口里借看时局。
其时正是魏阉、客氏表里为奸,十件朝报,到有九件是拿问清官,酷拷名士。向淇修说着便咬牙切齿,悲愤填膺,不则一遭儿了。但其时这般炎势,钳口结舌,尚有飞文中伤,况蒋家是有几分身家,怎不怕事。又在南京城市,且是巡纠官府,密缉番子张着网儿捕人。淇修是个意气男子,话也相投,当不得他内里恐怕惹事,每每撺掇淇修,打发出门,远些祸祟,独是淇修不肯。白驹过隙,日月如梭。熹庙宾天,毅宗登驾。魏阉一伙凶人都倒灶了。此时尔澄就象嫡亲仇家一旦报雪,狂呼踊踊,乐不可言。忽一日告诉淇修,向为四方荆棘,志士杜门,今幸少少清宁,欲纵远游,以舒郁闷,淇修应道:“使得,使得。”说话的,前日蒋家内里要打发他出门,淇修独独不肯,今竟慨然,这是何意?看官哥,前日淇修见老沙动辄骚愤,块垒难平,怕他出去不合时宜,惹出身命不保的事来。今日与前不同,以此一口应承道:“弟有年伯张雪峨讳恒者,现起兵部职方司。今年值弟上元县御白解头,正欲自去交兑,便道修候,也讨他些寅僚面情,早发收批也好。兄今有兴,同往更妙。但此去必须粗细人事,倒有些东西京中所重,出在湖州,劳兄往彼一行,俱有主人代办。尽不费力。”尔澄应允。淇修即便交出置办帐,是湖绵湖笔,埭溪雨前,庙后秋芥,共银一百八十两,额外盘缠二十两。带些南京轿夫营鞋舄搭作人事。叫他到湖州府德清县下钟鸣村上,问着蔡平泉,是我家一向粮食主管,寻他料理,事毕同来。我要用他押运。我去冬先有字去约他的。诸事打点停当,三杯作别。老蒋对尔澄说道:“吾兄意气激昂,且不肯修边幅。就是昏色银子成色不甚鲜明,恐世途势利起来,兄便宁耐不定了。切戒闲气少惹,事完速归,候兄同往。其时二年正月尽了。”尔澄遂诺诺连声,便老老气气,迳出水西门,搭船到湖州。一路风景:
芊眠草色怯春寒,作客天涯兴未阑。 两岸敲残佳节鼓,河桥剔历又关山。
话说浙江绍兴府上虞县郭外百麻村,有个霜三八老,姓葛名俭,金山卫军籍。在先父亲是老乡塾,三八也读书识字,二十来岁学成缝皮手艺。为人遇事风生,轻身尚义。因崇祯元年,上虞大早,颗粒无收。平民百姓连麦粥粞包,日不两餐。老霜幸是孤身,又亏煞着这件一动手便动口的技艺,捱得个半饥半饱。三八算道:“守着一块所在,实为不妙。况且本处凶荒,家家户户口糊不来,那个还理论到脚上。”三八忙忙收拾一担行李,到大半是挣饭家伙。料道杭州城里必是用人马头,随即挑起行囊,搭船到了萧山。那:
西兴渡,船乍开,一水穿江省会来。年荒情急打盘旋。
家私一担动人哀,归来未审家何在?活身手艺难迁改,知穿线因缘甚日回。 ——啄木儿
三八乘着冬底,积得几钱盘缠,初二搭船到杭州。那知杭州省会之地,不知多少鞋店,又有散碎皮匠,穿街踏巷。况且大小人家,不论大人小厮,或布或绸,都是新鞋度岁。那一桩缝皮生意,是极冷淡。三八暴出笼儿,不知这些时势,火脚啾啾,正月初五跑到了杭州城里,只道大家都赤脚专等这个皮郎种。一肩行李挑在淳佑桥苏州河下,金汁行头冯肖溪家中。老冯因是同乡,又与三八族甥有表姨兄弟之亲。三八担儿落肩,略略扯淡。他一心要赶着初五发发利巿,把家伙忙忙整顿,就钻出去了。
新正街上并没半个皮郎,独有他高兴,荡来荡去。倒也是他时运,毕竟兜着两主生意。都是主跟,共来十二文。三八暗道:“不照,不照。”有心没想,脚高步低,抬头一看,却是一座巷头五圣,且是有人拜献不绝。三八进歇下担子,口列三牲,心点香烛,要问目下生意去向。打下三筊,是圣阴阴。经云:
湖水听鸣钟,身忙不落空。
相逢多意外,无初事有终。
迳取归路,细将筊经自解,大约有些光景,只少路头儿。连晚顺溜,淳佑桥猪行客人,钉鞋帮绽,要他缝缝,歇担动手,各通乡贯。客人说是湖州德清县下钟鸣地方,三八兜搭上心,便问:“贵乡多少人家,贱业可以糊口否?”客人见他出口妥贴,应道:“正少,正少。去春多雨,春花蚕麦,一概坏了。家家急迫,各色手艺营生,一齐散去。去冬晚稻倍收,新正人上还闲,家家要缉理些鞋儿脚手,年年是有生意的,到关蚕门才懈哩!”三八竟把四句筊经念了又念道,颇巧合鸣钟两字,决意要去。问他路数,并客人姓名居址,求他帮衬,那客人一力应承。钉鞋缝完,工钱也不肯接。正是:
共作天涯客,应怜萍梗人。 话说猪客姓穆,号敬萱,是湖州收猪牙人。倒怜三八没寻头路,便满口应承说:“船是便的,初八以准同行便了。”至日同船,竟到下钟鸣老穆家里,就留他暂寓。三八早出晚归,生活到做不及,连午饭也没工夫回来吃。
再说沙尔澄南京起身,走了九个日头,方到德清县,同到下钟鸣地方,那个乡村不大,都务桑麻。但见:
田塍曲曲,河港湾湾。曲曲田塍,豆瓣麦芽多鹭迹;湾湾河港,竹篱茅屋半鱼罾。
老农鼓腹,初晴量雨絮叨叨;村媪蓬头,浴茧哺蚕忙切切。 一似辋川景,桑绕桐箍;不则桃花源,松交柏荫。
这乡风烟景,小李怎不踌躇;那古渡斜阳,大痴也应搁笔。
那尔澄提着行李,玩着这乡风古淡,只见一个小小庵儿,上写“般若上因”,且是清幽雅静。尔澄进去息足。走出一个黄瘦老和尚,尔澄上前问讯道:“我来贵地要会蔡平泉老爹,可晓得么?”老僧说:“晓得,也是本庵檀越,年年来往南京,住在港西,说他灯节后就要出门。”尔澄听说,便将行李暂寄庵中,只向行囊中取书一封,鞋子二双,迳去寻老蔡了。
看官,你说沙尔澄好混帐人,行李别项不要说起,乾净纹银二百金光景,孤身闯进,就一并丢在庵里,并不照管。倒也亏他不修边幅,人不起眼。你看他:
头戴着盔洗毡巾,身披着折浆布服。尤墩袜,桶完底破;陈桥鞋,头翘跟低。
捻断黄须,落落胸中藏甚事;张开白眼,口口行径傍何人。
那和尚估定是个教书先生,见他取鞋二双,一定向东家去献土仪了。老沙问到蔡家,将书鞋送进。半晌走出一个老妇人来道:“南京蒋相公处来人,请坐便饭,行李可发进来。”尔澄便问:“平泉老爹在么?”妇人覆道:“家老爹因去冬蒋相公有字来请,正月十八起身,去里家大官县里催粮,明日方回。”尔澄道:“既如此,明日来会。”转到庵里,只见老和尚过来作揖,通了姓名。尔澄想道:“人生路不熟,天又将晚,不如权在庵中,明日到蔡家讨覆。”尔澄将这话说上,和尚虽住乡间,势利是在行的。眼见老沙行经淹润,没甚想头。巴不得把那上司明文,不许庵观寺院收留面生可疑之人,一气读将出来。又碍着蔡平泉是个本境施主,况口谈不甚长久,只得勉强应承,也淡淡扯些闲文。
年规二月十四,是德清县城隍生辰,各乡科敛钱米,或佛事庆赞,或演戏燕乐。下钟鸣地方是十二般戏预庆,却在本境土地庙前台上。那台高不四尺,紧对庙门周围空地,尽可撑篷张伞,安凳布席,斟茶饮酒,笑耍取乐。尔澄在庵歇宿,大早出门,忙忙到蔡家讨覆。却在这土地庙经过,正见众人打扫坛场,知是乡规。
走到蔡家,仍是昨日老妇出来,作谢完了说:“家大官昨夜回来,见过书了。但县中粮米约定十五出兑上船。相公书内事,二十头边回来效劳。留相公在家下住着。有一字留覆”上写:
鞋二双已收明,不知有寸数大的还要一双,奉价。此达,感感。 沙尔澄老爹收 不名 尔澄看了这字,倒也好笑。正经事不提起,只是还要买鞋。看官,乡村里原是人才难得,要像蔡一官这样识得字透的能有几个?他见与文字中有沙尔澄来湖置货,也不知为何等项人,故只疏疏数字,写个沙尔澄老爹收。连下处都相忘,家里人也没一个问起。_就是老妇人,也只看这顶瘪方巾分上叫做相公。尔澄道:“既官人无暇,我到二十来会。”那老妇人兀自留茶留饭,尔澄抽了字儿出门远了。想道:“左右无事,不如到演戏所在,混他一昼去。”举眼一望:人山人海,男男女女。却似:
蚂蚁扛着鲞骨,苍蝇琮了脓包。孝无常出头透气,黑脸鬼扒脚流涎。 花花粉面,踹着一对采莲船;簇簇针颔,披着半肩编棕伞。 背驼的,如猿独驮儿;怀抱的,似婆罗拖子。也有频摇着扇睁睁看,数撮粞团口口吞。
尔澄看光景还早,回到庵里。向盘缠包内摸出五钱多大一块松纹,包了送与长老说:“学生要在贵庵打搅,尚有三、四日子,先送饭金少许,容再总谢。”和尚笑谢道:“不消费心。”道人接着,仔细捏一捏,便向厨下洗锅抹灶起来。和尚进来商量:“如今待慢不得了。”两个栗栗碌碌足足忙了半日,拿出六碗新鲜现成素莱。尔澄等得不耐烦,讨不得快些,吃了去散闷。和尚偏有情没绪,左请右请,一饭将完,早已日过西了。别过长老出庵,未到土地庙前,听得锣鼓喧天,已上了三折,是魏太监新戏,叫做《飞龙记》。一班弋阳腔水磨到家的,扮魏监的戏子叫做秋三,是他出色长技。
老沙踱到,看戏的都挤紧定了。团圞走转,却好一个缝皮的身边,因他在那里,打掌主跟,人略松他一分儿。老沙站住脚,看正生却是杨涟,魏阉、客氏折折打点伏案。那三八一头缝皮,只是娘嬉长,娘嬉短,眼睛不瞧。听得魏监出场,雌声雌气,他便口里狠狠骂道:“杀个娘嬉,何等勿好!”那沙尔澄逐折看去,早把那抱不平的肚肠点得火着。
正没处发泄,见皮匠愤愤不休,尔澄赏鉴他倒也是个刚肠男子。不料看到魏监出场,分付大小官员要用非刑“大五花”醅拷杨、左、周、魏等官。不怕他不招赃认罪。那五件:
黄龙三转身,是铜蛇绕体,灌以滚油;
善财拜观音,是捆住双手,以滚沥青浇泼手上; 敲断玉钗,是铁锤锤去牙齿,使其含糊难辩;
相思线,是锋快铁索,穿过琵琶骨;
一刀齐,是钢利阔凿,凿去五个足趾。
只见那扮的魏监,尚指天画地用心水磨。谁料沙尔澄看到此处,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喊道:“再耐不得了!”提起皮郎切刀,三脚两步跳上台去。掀翻魂监,按颈一刀,早已红光乱冒,身首两处了。那时戏子只道强盗上来打劫行头,到一齐往戏房乱躲。台下人亦不知甚么事发,各各逃窜,捱挤践踏,,儿啼女哭,人住马不住了。三八倒着急,恐怕没了皮刀,飞风上台寻取,拾刀在手,并死尸也不看见。沙尔澄丢刀只不做声,溜落台来,也乱在众人里,呐声喊,没命的跑了。还有几个做头内中老成的,走将拢来。高叫:“不要乱跑,认拿凶身要紧!”说得快时,却也走得个七八。只见霜三八提着皮刀,还在那里叹息:“这个好汉奇得紧,杀得有趣。”众人已围住道:“不要寻了,凶身在这里!”三八本不杀人,心自凉的。正听得凶身有了,心里想着,有这样高兴的人,不知面貌上有多少义气。他即应声问道:“在那里?在那里?”众人道:“是你!是你!”正要辩时,众人倒恐他行凶,背后将绳子一套。三八还不着忙,当不得众人一拳两脚道:“害着地方怎处?”三八方才呆了。众人问道:“他与你有何冤仇,偏生杀在我们地方上?”一班戏子,将三八乱扯乱推到台上尸边,打打骂骂,问他姓名,只不肯语,鬻应。只见尸边一条纸儿,众人拾起一念。上写:
鞋二双已收明,不知有寸数大的还要一双,奉价。此达,感感。
沙尔澄老爹收
不名
众人听得道:“这是杀人真赃了!鞋子说话不是他本行买卖?原来叫做沙尔澄”。三八见众人问他名姓,死不肯说。赖他是沙尔澄,他才说我叫霜三八。众人不由分说,打点送官,将带血皮刀,着叠在楦头担内。却见一个荷叶包儿,打开一看,是包牛肉。众人大叫起来,不消说得,一法是他杀的了。尸边字儿上写着鞋子事情,不必说是缝皮的了。姓沙的都是回子,今担内又有牛肉。况且血淋淋的皮刀在手。无疑,无疑。
众人连晚带了三八并一副皮担,到县击鼓,登时传开,已拿住杀人的沙尔澄(霜三八)。倒是蔡一官、穆敬萱阿家躲得没影。沙尔澄飞风跑进庵里,喘息方定。自已想这节奇事,就是梦里一般。将皮匠拾刀行像仔细记着,但先自己走脱了。不晓得后面拾着字儿,搜出牛肉,他自供认叫做霜三八,不肯认沙尔澄的事情。因自想道:“杀人大事,可是吹得隐灯的?况蔡家知我姓沙,乘大家手乱脚忙,走为上着罢。”对道人说:“蔡家接我,我搬行李去了。多谢师太。”道人好不快活。尔澄一溜烟走到船埠头搭载,恐怕株连老蒋,不回南京,身边盘缠颇饶,竞改姓海,字口口,混到长安去了。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
却说下钟鸣一行人,到县已黄昏时分,擂鼓禀上。县官听得,事涉不经,收监再审。当晚先出里递收尸朱票。次日升堂,带出霜三八,并一班地方。众人细禀本末,如此这般。
那县官姓岑名苔,是按察司知事。署印德清,贡生出身,湖广辰州府溆浦县人。慕西湖山水,挈资从仕。年纪不上四十,吏事精明。审这节事,听众人禀的时节,却把霜三八冷冷瞧着,见三八或嬉笑自得,或愤懑不平。岑知县早早估定,是个侠客的替身。却寻着的是戏子,这又难解了。再不命到仇恨魏监,认戏作真。及至叫着沙尔澄,三八只不理。
县官叫众人问道:“这凶身可是哑子么?”只见众人扒起捺倒,鸦飞鹊乱,七嘴八丫叉的,沸做一堂,官府一字也听不出。岑知县喝道:“一节杀人重情,成招按律,少不得要个对头,着一个老成地方上来。”众人听得这句,好像曲蟮,个个倒缩。堂上堂下,寂静得就是黄昏古驿的一般。然后那霜三八不慌不忙禀道:“小的霜三八。”那知县到吃一惊。
三八口口籍贯来历后,禀:“本处年荒,到杭存身,到湖生理。及这日台边缝皮,别个杀人,我去收刀。若要冤小的杀人,小的也是恨魏监的,他杀就是我杀一般。若要冤小的是回子沙尔澄,小的死也不服。怎的小的当刑,倒把别人名姓冒个抱不平杀奸贼的美举!”县主听了,倒也口定目呆。天下古今,有这等认真透彻的男子。便叫为首递年戏子报名。比律拢招:
审得沙尔澄即霜三八也,与戏子秋三,必先构冤仇,凑秋三演戏,假扮缝皮,利其刃而杀之,痛哉!秋三出其不意,曾不得抵敌而剖白,致旁人无一解救。而其彼此构衅之由亦莫闻也。当堂研鞫,则曰夙怒阉人,一时愤杀,则真莫须有之案。词颇穷遁,人命儿戏至此乎!本县只据地方目击而可据者有五:杀人凶器切皮刀也;尸边字纸鞋寸尺也;字尾名氏沙尔澄也,沙非华姓,回子也,担有牛肉,回所食也。而况现提血刃,当时其获者乎!则霜三八者,固沙尔澄之乳名无疑也。三八供称军籍,按律:卫军死刑,倍调远卫充军例,收监候夺。
县官当堂,将审单读完。又将各里递分付,以后不许搭台演戏,生事扰民。众人散去不提。
却说蔡平泉到蒋家,淇修知尔澄会不着了。适上元县御白粮事,改了折色,只要出一人,帮押银鞘到天津交纳。淇修打发平泉去了。自家等着尔澄。谁知过了端阳,也没捎个字来。淇修等得不耐烦,寂寞不过。收了五百多两纱罗段匹,合了同伙,到京师出脱。私房带有金珠银两二千金,锁在个旧皮头巾盠内,要去乘便,干个通判行头。船出京口,一路平安。不料到宿迁地方,撞着大王的人了,将他的东西抢得如洗,连众人的共有万金。众人垂头落颈,各自散去。
淇修妄自念头,要去见他头目,讨这头巾盠子。众盗见他跟紧,说这呆子还要纳条性命。走了三五里,并没人烟,见一座高山,巨木参天,郁林蔽日,西边临着大泽,内结一个窝巢。众贼拥进一个为首的泗州人,姓丁名翼,绰号丁张飞。也是有胆力好汉,饿不过了,干此营生。那人生得: 撑着吊眼,满身突肉如拳。鹰眼虾须,遍体缠筋似炭。
不用三头罗刹,鬼见消魂,何必八臂哪吒,神当碎魄。 却说那大王坐下,众贼将这些货物,摊做一地。那皮盠也在,尚锁着的,喝声收好。看见老蒋面生,尚衣冠济楚,问左右道:“这汉子怎的说?”淇修答道:“我本书生,不图财利。因有亲在京,搭船去探。所有段匹,尽当贡献。但头巾皮盝,内有书信,哀恳见还。”那贼头听了说:“我等各有身家,因山东一带,吃白莲教扰害。可恨贪官污吏,将富足平民,埋陷株连,且弄到天荒地白,父东子西,冻饿无聊,逼到这条路上。我看你这娇怯行径,必定到京里谋官做的。但做官第一要诀是黑心,没阴骘,我劝你莫去罢。我这里有粮没兵,有兵没将。要做几件痛快的事,也不能够。敬屈贤者在此主盟。”说罢纳头便拜。慌得淇修回礼不迭。
淇修想道:“虽是绿林,话却正气。料我要去,那皮盝是没分的了,且只得再图机会。”遂各通名贯。淇修道:“既承招纳,当设盟誓。”即焚点香烛,折矢八拜。随出誓书示众:妇不上山,孤客竟放,商税加三,招安各散。丁翼笑道:“妙,妙,结末一句,更合吾意。但是过往赃坯全抄罢了。”大家又笑。只是淇修如坐针毡,那能忘怀。
再提沙尔澄迳到北京,寻了下处,安顿行李,即去刻位金字牌儿,上书“义士皮公之位”。酒肴香烛,誓终身不忘代死之恩。就去打听得兵部职方司张公,目下正该掌选了。尔澄做这奇事以后,一路与人打伙,造得十分唧溜。他便写副大礼,用通家晚生海源拜帖。门上传进,便请见留茶。张公道:“足下过爱口玉,学生到忘却是何亲谊,远来必有见教。”老沙见他兜收,便抿进去道:“南中上元,贵年侄蒋淇修,讳有筠者,晚生之姑表兄弟也。闻大人集思广益,葑菲不遗,特着晚生登龙恭谒。表兄押运御白,到即禀候。诚献一芹,恕乏手奏。”张公见话头温雅,卯眼又对。笑容可掬道:“足下才高年壮,肯觅封侯事乎?学生虚席以待。”一茶又茶,直送出门。点出礼帖,是口鞋二双,湖纱二端。尔澄即忙送进。
到九月初一,是张公掌选,便将尔澄新改名氏海源选了蓟州镇屯捕总司,驻扎蓟门。这个地方兵精粮足,是京师蔽翼。与司道敌体,兼理民词,放铳扯旗,好不威风。离京不远,即日领凭亲谢。张公说道:“略有机会,便当超迁。”尔澄千恩万谢,到任去了。正是:
丈夫会合须有时,燕壁秦关徒自苦。
话表霜三八,问了个车盖儿,一下不打,在监中就缝起皮来,且是热闹。众人道他是冤屈的义士,酒儿食儿,倒不绝口。岑公审定,申详上司,俱批依拟。恐防接县的驳招,即定调了保定镇杂站卫卫军。岑公怜他朦胧受罪,慷慨招承。嘱两个本分军牢,长行押解,每人倒赏十两盘缠,连霜三八也赏五两。三八堂上痛哭,誓必犬马报恩。两个解子,一个犯人,好不相知。把三八脚镣手铐,遣戍文书,装做一袋,各人一个行李包。搭船到苏州,趁着腌腊客人回北的船,货人已满,三人与船家商量,便在那火舱内捱着。行了好多日子,刚到了宿迁地界,船家苏苏拢岸。早有暗号手势,那客人也心照的,说道回此南货,倒是加一。只见几个狰狞大汉,尖帽翁鞋,逐舱跟估,说这水手停当,大家省力。次到梢上,见三人是南音,问船上是甚货,船上不知细底,只得含糊道:“想没货的。”那大汉估定是进京勾当,把行李褡裢一一提过,内一包沉重得紧,那知是三八皮郎家伙。大叫道:“大伙漏税!”将三人不由分说,拖猪拖狗扯去了。
捉到寨里,老丁、老蒋吆喝升堂。八个大汉将行李打散,见官封一件,递上老蒋。拆开一看,便大惊道:“沙尔澄在那里?快请相见!”霜三八听得抖抖衣服,立将起来说:“犯人有。”老蒋道:“胡说!沙尔澄是我同窗,他携资到湖,竟无音耗,原来这干奴才谋死,倒假冒他名氏。”两个解人慌了,霜三八是雪亮的,遂细细禀上:如此这般,害小的问罪充军,文书审招可据。老蒋遂细细看了道:“这人分明是老沙杀的,况且搬演魏监一发是了。”老丁听说,怜霜三八是替死鬼,劝老蒋杀了解人,放了三八罢。三八听了,磕头饶命。老蒋道:“岂有此理。”叫三八后堂分付道:“我明白了,我此时放你,有何难处。看你是义气的,决不肯害解人。不如且到衙所,再图后会。我叫做蒋淇修,南京监生,是上元人。”说了又说,三八牢牢记着。与了三人酒饭,收拾行李,着人护送一程。
却说三个拾得性命,星夜赶到保定。保定卫官接上文书,已是开拆过的,恐有倒换之弊,不肯发出回收。三人禀道:“遇着当官强盗,先查验过了。”卫官晓得是丁张飞的节掯,便与收批。 三八在衙,小心公事。空了仍旧缝皮,倒也糊得口来。一日保定屯局司文书下卫,是关会蓟州屯司比例开屯,是军足饷事。正该三八杂站值差,领了关文,三个日子走到蓟门。正是沙尔澄巡署,先日挂号,次日等他三通吹擂,三个大铳,吆喝开门。三八随着投文进去,却好结束,叫着三八。那沙尔澄眼尖,分付跪着,等领回关,将他面貌仔细模写,看了一回,想了一晌,暗道:“如何得到这里?”问道:“那赍关卫差报名。”三八应道:“沙尔澄。”惊得老沙遍身冷汗,有这般奇事。把头乱点,即叫掩门。叫三八到后堂,问三八道:“你不叫做沙尔澄,怎么到得这里?”三八即将别个杀人,将我抵罪根由,一五一十,细细说了。钞袋内摸出一张烂纸是县官审招底儿。沙尔澄一看,走下来纳头下拜:“义士,义士!”叫个不绝。三八倒惊呆了,不知甚么来头。尔澄即命备酒,两人共是一席。三八那里敢坐,尔澄道:“义士坐了,我好细细讲话。”把南京蒋淇修央我湖州德清下钟鸣置礼,那日看戏,一时愤杀魏阉,逃到京中,姓沙改海,如此这般。足下高义,日日想报。轩后现供着牌位儿,称你做“义士皮公”以志不忘。三八陡然听见南京蒋淇修,暗道又是奇事,也乱点头问道:“蒋公不是上元县监生么?”尔澄道:“正是,怎么晓得?”三八又将宿迁事情细说。将淇修临别“我叫做蒋淇修,南京监生,上元人”,说了又说,“像是偶然落草的”。尔澄叹息一回道:“即同你去救他。”叫书手打点回关,又写一私书与卫官,内封银十二两,与卫官雇军值日,要他发回三八。卫官看书,即叫三八将银子去雇人值日,收拾起身。
到蓟门衙里,尔澄即写一书,差官送张试选。内禀蒋淇修挟资来京,被劫落草,且宿迁系南北要津,宜作急招安,免得聚久凶穷,梗塞通道。张公会意,即转尔澄扬州操捕司,给与官凭。又有私书与尔澄,叫他便道散楚救他出劫。若差官招抚,把淇修上了纸笔做个贼头称呼,玷辱终身并子孙都不便了。尔澄接书叹道:“君子爱人,文人作用何等妥贴。”忙忙收拾起身,将到宿迁地界,早有豪杰拱候。是丁张飞分付过往官船,不照旧例,喝声“官船泊岸讲话。”三八心照,忙应道:“正要与丁爷一会,众位哥不劳动手,泊岸就是。”老沙瞧头便服出舱,分付:“水手泊岸,我去拜客就来”。那些好汉见话有路头,就不声势。一行人走到山寨去,两个头儿出来。尔澄一见淇修,抱头大哭。两边事情,三八也讲明一半。但淇修何以落草,三八何处口着尔澄,两个呜呜的细说。
老丁知老沙是现任官府了,及与丁翼周旋,老丁倒垂泪起来道:“山水有相逢,偏我老丁没个亲人来往。”大家安慰他一番,大开筵宴。老蒋心照老沙来意,先把丁翼无奈到此,只望朝廷招安的说话打动他。丁翼道:“我受招安,倒与官儿做饭,且出头露面过了,虽说自新,终久是有名的贼头,到底受人轻薄”。老沙便将兵部只要差一官,张选君不欲差官招安,深体老丈之意,高明所见略同。老丁快活得紧,指着老蒋道:“罢了,只听沙爷调停,难得知己如此,毕竟有个冠冕局面。”尔澄即问道:“有多少人马,有多少积聚?开一清数。”次日,尔澄与老丁、老蒋商量道:“人有二千,幸得资货颇饶,可使豪杰散去,不致失所。”即叫众人俱来听令:“我等异姓结义,胜于骨肉。初非得已,皆因白莲流毒,官府贪污,逼迫至此。今幸官府怜我无奈,朝廷许我自新。今日公分积聚,可以各归田里,勿踏前辙,笑我绿林中人,皆贪顽无耻。必取灭于锋镝也。”众人泣下,愿如所约,遂大列牛酒。明日各束行李,三五结队,东西南北,各寻生路。
老丁得力数人,收拾细软,俱要跟随老沙到任,将寨屋放火烧光,俱到老沙船里。不则一日,到了扬州,早有属官迎接。三八正名葛俭,做了中军。丁翼改作干羽,作个把总。老蒋令叫小船,别了老沙,忙到家里,举家见了,又喜又悲,悄悄把事情说了。把霜三八、沙尔澄两个生辰朔旦举家香烛拜谢。
看官们,老葛是个手艺中人,薄负义气,坎坷之中,累有奇烈。老沙的性命是他替的,老蒋的骨肉是他全的,老丁的落劫是他出的,南北的梗路是他通的。千古奇人,千古奇事。愧我笔拙,万不能表扬一二而已。
诗曰:
毅魄如虹吐,英风旷古无。
欣期荆聂共,不令郭朱孤。
热血浇寒剑,深情击唾壶。
堪垂金石永,莫笑画葫芦。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可笑今人动辄风生,借名公愤,不知激出多少事来。大则震撼朝廷,小则武断乡曲。这公愤可是当耍发得的?我以为愤而不公,仗着一股血气;公而不愤,何异脂粉妇人?若真正公愤,也博得个青史题名,口碑载道。
气节人人妄自矜,一朝遇事也风生。
身尔转念真堪惜,若个刚肠亘古今。 叵耐古今天下最可恼的,小人得令,乘权使势,威福生死,真是炙手可热。随有一伙呵脬捧腿的,也就狐假虎威,那小人气焰一发热腾腾当不得了。若是把守清谨的人,只是各行其道。我也不随波逐流,我也不吹毛求疵。如阳货欲见孔子,朱文公注得绝好,君子之待小人不恶而严也,恐疾之已甚,不免事外生事。这样说起来,趋和的趋和,养高的养高,终不然听凭小人煽虐天下,更有何事赖着轰轰烈烈丈夫表表奇男子。虽然这却大难,纲常胜事,气节快举,怎能够事到其间,利害不摇,生死不撼,把身子推作孤注,轻于一掷。况是以下不三不四的小民百姓,纲常气节与他有甚相干。正是: 当场个个奇男子,转眼乔妆妾妇行。
说只如此,气性到底人人有的。却怎么:
天启年间,魏阉作耗起来,势不可当。缙绅大夫,非惟没有力量救正剪除,反有作为鹰犬,遇着弹论他的。从而排挤下石,敲朴成招,衣冠体面,文章生气,一些都讲不起了。朝中文武,津要官员,大半抹落脸来,乞怜摇尾。其时做造假旨,校尉横出。无论当事官府,遭其荼毒;即标下士夫,借事蔓延,污蔑锻炼,也没有一夜得安枕的。 一日,忽然差出校尉数名,向苏州地方拿人。开读圣旨,自司道府县,个个怀着鬼胎,咬牙咇卟,外边又有人山人海,围绕打听。正是: 日间不干亏心事,半夜敲门也吃惊。
不料开读旨完,沸传要拿某人,要拿某人,彼时三三两两,即有为他叫冤叫屈的,道犹未了,昕得一片喊响,跳出一伙豪杰。时方天雨,也有拿着砖头的,也有拿着木屐的,也有钉靴乱踢的,也有伞柄肥鞭的,就是雨点雪片一般,俱向校尉乱打,不分太阳肋扇。各官各府,衙门人役, 晓得民变,乱呼乱叫,只好救护本官,那里还敢禁止。只见那些人:
凶眉倒豁,人人拼命争先;恶眼圆睁,个个舍生取义。如当公战,以挟私仇。 一拳复一拳,气断多时拳不歇;一脚又一脚,死已半日脚仍加。
可怜几个校尉,不消半个时辰,打做肉酱。官府慌了,随即安抚百姓,只叫认查个把做头的,再处其余,不得混拿。看官们,你说这些官府内中,不知多少魏阉亲人在内,但目击民变,恐怕此时雷厉风行,一发变生不测。但只是魏阉声势,便是他的鸡犬,热气也呵他一口不得。况又有些甚么圣旨在内,各官面面相觑,正没一个妥当局面。只见人声乱嚷嚷中,几个高声叫喊:“是我打死!是我打死!”劈条人路,跪在官府面前,共有五个。连不上十四五岁瘌痢荒荒一个小使也在里边。官府尚自分付,只要一名。那五人怒愤愤的争前认首,各将凶器口供。颜佩韦等端端正正五名即刻锁押收监。看官,你看校尉赍旨,要拿周顺昌等进京,其时两榜同年,当道长官,尚没一个出头痛恤,却与这般平民何干?做出这样轰轰烈烈,直到身正典刑,尚且谈笑自若。此事声震朝野,不知多少衣冠士夫,汗流浃背。如此节义,却让没有半点墨水的攘臂争光。这叫做:
衣冠不任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 看官们,当时魏阉煽毒,暗暗切齿的难道没有,那有明目张胆,这般痛快。然尚说道:眼见是非颠倒,皂白不分,一时血气,睛眼出火,做个舍手,传名千古燥脾的奇事。如今更有一件希罕的新文,却在魏阉相隔三四年,又从没要紧戏耍场中,冷灰爆出一个热栗来。一向人岂不闻,那知其中还有许多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层层折折的因由。犹如:
古镜尚蒙尘,奇人不遍闻。 开尘磨镜叟,演义胜丹青。
口口口口一朝晏驾,崇祯御极。把从前黑漆漆不由分说的陷人坑,一旦扒平。上朝下野,也该报他一个民和年丰了。不知甚么缘故,连年间或水或旱,百姓流离。若是守株待兔的,九个饿杀十个。有些薄技微长的,除非是东奔西走,方才过得日子。正是:
不将辛苦易,难赚世间财。
话表南京城内,有个太学,姓蒋名有筠,号淇修。年三十余,有子方才十岁。祖父甲科,族中叔伯弟兄,科甲贡监,不下十人。淇修援例,父兄要他进取捷径,省得零碎考试,小题分心,也不是团于兰一段真正白木头。兼他天资颖悟,苦志攻书,你说他是科甲两字肯不放在心坎儿上的。但只因他家事繁重,交际颇多。田地房产上的差徭粮税,见年里长,也讨个源源而来。读书身分,也毕竟吃些亏了。以此功名不得遂意。每有浪迹江湖,结识异人之志。却有一个总角同窗,八拜订盟的,姓沙名原,字尔澄。祖籍真回教。其父沙象坤,曾发乡榜,周旋世务,只得圆融出教。尔澄幼与淇修笔研有年,两人志同道合,吃尽灯窗滋味。却是: 埋头经史三冬足,不见青藜借火燃。 淇修京缘羁绊,不得尽兴交游。尔澄文事既不得意,孑身聊落,到处穷途,又是淇修接过家里。尔澄自愧年纪三十,不采一芹,但因家事凄凉,欲辞不得。却有一件胎里疾,不修边幅,任侠负气。每见人有恃势凌物,欺压良善的,也就奋不顾身,他便下老实不平起来。就是读着书史中冤抑的事,便击案而起,破涕牢骚。看到怨愤发雪田地,又仰天大笑,呼酒破闷,开怀歌唱。伏侍书童,说他是失心风的书呆。又怕他难捏鼻头的性儿,况是家主尚且周旋。以此要长要短,就似呼风唤雨的一般,并不敢半点的违拗。正是:
堂上绸缪朱履客,阶前若个不殷勤。
却说蒋家后园五间书楼,上上下下,有的是牙签万轴,锦帙千缃。尔澄涉猎之外,更有报房日送。却是朝中时事,随到随阅。淇修每到晚闻,必梯己与尔澄小酌,从他口里借看时局。
其时正是魏阉、客氏表里为奸,十件朝报,到有九件是拿问清官,酷拷名士。向淇修说着便咬牙切齿,悲愤填膺,不则一遭儿了。但其时这般炎势,钳口结舌,尚有飞文中伤,况蒋家是有几分身家,怎不怕事。又在南京城市,且是巡纠官府,密缉番子张着网儿捕人。淇修是个意气男子,话也相投,当不得他内里恐怕惹事,每每撺掇淇修,打发出门,远些祸祟,独是淇修不肯。白驹过隙,日月如梭。熹庙宾天,毅宗登驾。魏阉一伙凶人都倒灶了。此时尔澄就象嫡亲仇家一旦报雪,狂呼踊踊,乐不可言。忽一日告诉淇修,向为四方荆棘,志士杜门,今幸少少清宁,欲纵远游,以舒郁闷,淇修应道:“使得,使得。”说话的,前日蒋家内里要打发他出门,淇修独独不肯,今竟慨然,这是何意?看官哥,前日淇修见老沙动辄骚愤,块垒难平,怕他出去不合时宜,惹出身命不保的事来。今日与前不同,以此一口应承道:“弟有年伯张雪峨讳恒者,现起兵部职方司。今年值弟上元县御白解头,正欲自去交兑,便道修候,也讨他些寅僚面情,早发收批也好。兄今有兴,同往更妙。但此去必须粗细人事,倒有些东西京中所重,出在湖州,劳兄往彼一行,俱有主人代办。尽不费力。”尔澄应允。淇修即便交出置办帐,是湖绵湖笔,埭溪雨前,庙后秋芥,共银一百八十两,额外盘缠二十两。带些南京轿夫营鞋舄搭作人事。叫他到湖州府德清县下钟鸣村上,问着蔡平泉,是我家一向粮食主管,寻他料理,事毕同来。我要用他押运。我去冬先有字去约他的。诸事打点停当,三杯作别。老蒋对尔澄说道:“吾兄意气激昂,且不肯修边幅。就是昏色银子成色不甚鲜明,恐世途势利起来,兄便宁耐不定了。切戒闲气少惹,事完速归,候兄同往。其时二年正月尽了。”尔澄遂诺诺连声,便老老气气,迳出水西门,搭船到湖州。一路风景:
芊眠草色怯春寒,作客天涯兴未阑。 两岸敲残佳节鼓,河桥剔历又关山。
话说浙江绍兴府上虞县郭外百麻村,有个霜三八老,姓葛名俭,金山卫军籍。在先父亲是老乡塾,三八也读书识字,二十来岁学成缝皮手艺。为人遇事风生,轻身尚义。因崇祯元年,上虞大早,颗粒无收。平民百姓连麦粥粞包,日不两餐。老霜幸是孤身,又亏煞着这件一动手便动口的技艺,捱得个半饥半饱。三八算道:“守着一块所在,实为不妙。况且本处凶荒,家家户户口糊不来,那个还理论到脚上。”三八忙忙收拾一担行李,到大半是挣饭家伙。料道杭州城里必是用人马头,随即挑起行囊,搭船到了萧山。那:
西兴渡,船乍开,一水穿江省会来。年荒情急打盘旋。
家私一担动人哀,归来未审家何在?活身手艺难迁改,知穿线因缘甚日回。 ——啄木儿
三八乘着冬底,积得几钱盘缠,初二搭船到杭州。那知杭州省会之地,不知多少鞋店,又有散碎皮匠,穿街踏巷。况且大小人家,不论大人小厮,或布或绸,都是新鞋度岁。那一桩缝皮生意,是极冷淡。三八暴出笼儿,不知这些时势,火脚啾啾,正月初五跑到了杭州城里,只道大家都赤脚专等这个皮郎种。一肩行李挑在淳佑桥苏州河下,金汁行头冯肖溪家中。老冯因是同乡,又与三八族甥有表姨兄弟之亲。三八担儿落肩,略略扯淡。他一心要赶着初五发发利巿,把家伙忙忙整顿,就钻出去了。
新正街上并没半个皮郎,独有他高兴,荡来荡去。倒也是他时运,毕竟兜着两主生意。都是主跟,共来十二文。三八暗道:“不照,不照。”有心没想,脚高步低,抬头一看,却是一座巷头五圣,且是有人拜献不绝。三八进歇下担子,口列三牲,心点香烛,要问目下生意去向。打下三筊,是圣阴阴。经云:
湖水听鸣钟,身忙不落空。
相逢多意外,无初事有终。
迳取归路,细将筊经自解,大约有些光景,只少路头儿。连晚顺溜,淳佑桥猪行客人,钉鞋帮绽,要他缝缝,歇担动手,各通乡贯。客人说是湖州德清县下钟鸣地方,三八兜搭上心,便问:“贵乡多少人家,贱业可以糊口否?”客人见他出口妥贴,应道:“正少,正少。去春多雨,春花蚕麦,一概坏了。家家急迫,各色手艺营生,一齐散去。去冬晚稻倍收,新正人上还闲,家家要缉理些鞋儿脚手,年年是有生意的,到关蚕门才懈哩!”三八竟把四句筊经念了又念道,颇巧合鸣钟两字,决意要去。问他路数,并客人姓名居址,求他帮衬,那客人一力应承。钉鞋缝完,工钱也不肯接。正是:
共作天涯客,应怜萍梗人。 话说猪客姓穆,号敬萱,是湖州收猪牙人。倒怜三八没寻头路,便满口应承说:“船是便的,初八以准同行便了。”至日同船,竟到下钟鸣老穆家里,就留他暂寓。三八早出晚归,生活到做不及,连午饭也没工夫回来吃。
再说沙尔澄南京起身,走了九个日头,方到德清县,同到下钟鸣地方,那个乡村不大,都务桑麻。但见:
田塍曲曲,河港湾湾。曲曲田塍,豆瓣麦芽多鹭迹;湾湾河港,竹篱茅屋半鱼罾。
老农鼓腹,初晴量雨絮叨叨;村媪蓬头,浴茧哺蚕忙切切。 一似辋川景,桑绕桐箍;不则桃花源,松交柏荫。
这乡风烟景,小李怎不踌躇;那古渡斜阳,大痴也应搁笔。
那尔澄提着行李,玩着这乡风古淡,只见一个小小庵儿,上写“般若上因”,且是清幽雅静。尔澄进去息足。走出一个黄瘦老和尚,尔澄上前问讯道:“我来贵地要会蔡平泉老爹,可晓得么?”老僧说:“晓得,也是本庵檀越,年年来往南京,住在港西,说他灯节后就要出门。”尔澄听说,便将行李暂寄庵中,只向行囊中取书一封,鞋子二双,迳去寻老蔡了。
看官,你说沙尔澄好混帐人,行李别项不要说起,乾净纹银二百金光景,孤身闯进,就一并丢在庵里,并不照管。倒也亏他不修边幅,人不起眼。你看他:
头戴着盔洗毡巾,身披着折浆布服。尤墩袜,桶完底破;陈桥鞋,头翘跟低。
捻断黄须,落落胸中藏甚事;张开白眼,口口行径傍何人。
那和尚估定是个教书先生,见他取鞋二双,一定向东家去献土仪了。老沙问到蔡家,将书鞋送进。半晌走出一个老妇人来道:“南京蒋相公处来人,请坐便饭,行李可发进来。”尔澄便问:“平泉老爹在么?”妇人覆道:“家老爹因去冬蒋相公有字来请,正月十八起身,去里家大官县里催粮,明日方回。”尔澄道:“既如此,明日来会。”转到庵里,只见老和尚过来作揖,通了姓名。尔澄想道:“人生路不熟,天又将晚,不如权在庵中,明日到蔡家讨覆。”尔澄将这话说上,和尚虽住乡间,势利是在行的。眼见老沙行经淹润,没甚想头。巴不得把那上司明文,不许庵观寺院收留面生可疑之人,一气读将出来。又碍着蔡平泉是个本境施主,况口谈不甚长久,只得勉强应承,也淡淡扯些闲文。
年规二月十四,是德清县城隍生辰,各乡科敛钱米,或佛事庆赞,或演戏燕乐。下钟鸣地方是十二般戏预庆,却在本境土地庙前台上。那台高不四尺,紧对庙门周围空地,尽可撑篷张伞,安凳布席,斟茶饮酒,笑耍取乐。尔澄在庵歇宿,大早出门,忙忙到蔡家讨覆。却在这土地庙经过,正见众人打扫坛场,知是乡规。
走到蔡家,仍是昨日老妇出来,作谢完了说:“家大官昨夜回来,见过书了。但县中粮米约定十五出兑上船。相公书内事,二十头边回来效劳。留相公在家下住着。有一字留覆”上写:
鞋二双已收明,不知有寸数大的还要一双,奉价。此达,感感。 沙尔澄老爹收 不名 尔澄看了这字,倒也好笑。正经事不提起,只是还要买鞋。看官,乡村里原是人才难得,要像蔡一官这样识得字透的能有几个?他见与文字中有沙尔澄来湖置货,也不知为何等项人,故只疏疏数字,写个沙尔澄老爹收。连下处都相忘,家里人也没一个问起。_就是老妇人,也只看这顶瘪方巾分上叫做相公。尔澄道:“既官人无暇,我到二十来会。”那老妇人兀自留茶留饭,尔澄抽了字儿出门远了。想道:“左右无事,不如到演戏所在,混他一昼去。”举眼一望:人山人海,男男女女。却似:
蚂蚁扛着鲞骨,苍蝇琮了脓包。孝无常出头透气,黑脸鬼扒脚流涎。 花花粉面,踹着一对采莲船;簇簇针颔,披着半肩编棕伞。 背驼的,如猿独驮儿;怀抱的,似婆罗拖子。也有频摇着扇睁睁看,数撮粞团口口吞。
尔澄看光景还早,回到庵里。向盘缠包内摸出五钱多大一块松纹,包了送与长老说:“学生要在贵庵打搅,尚有三、四日子,先送饭金少许,容再总谢。”和尚笑谢道:“不消费心。”道人接着,仔细捏一捏,便向厨下洗锅抹灶起来。和尚进来商量:“如今待慢不得了。”两个栗栗碌碌足足忙了半日,拿出六碗新鲜现成素莱。尔澄等得不耐烦,讨不得快些,吃了去散闷。和尚偏有情没绪,左请右请,一饭将完,早已日过西了。别过长老出庵,未到土地庙前,听得锣鼓喧天,已上了三折,是魏太监新戏,叫做《飞龙记》。一班弋阳腔水磨到家的,扮魏监的戏子叫做秋三,是他出色长技。
老沙踱到,看戏的都挤紧定了。团圞走转,却好一个缝皮的身边,因他在那里,打掌主跟,人略松他一分儿。老沙站住脚,看正生却是杨涟,魏阉、客氏折折打点伏案。那三八一头缝皮,只是娘嬉长,娘嬉短,眼睛不瞧。听得魏监出场,雌声雌气,他便口里狠狠骂道:“杀个娘嬉,何等勿好!”那沙尔澄逐折看去,早把那抱不平的肚肠点得火着。
正没处发泄,见皮匠愤愤不休,尔澄赏鉴他倒也是个刚肠男子。不料看到魏监出场,分付大小官员要用非刑“大五花”醅拷杨、左、周、魏等官。不怕他不招赃认罪。那五件:
黄龙三转身,是铜蛇绕体,灌以滚油;
善财拜观音,是捆住双手,以滚沥青浇泼手上; 敲断玉钗,是铁锤锤去牙齿,使其含糊难辩;
相思线,是锋快铁索,穿过琵琶骨;
一刀齐,是钢利阔凿,凿去五个足趾。
只见那扮的魏监,尚指天画地用心水磨。谁料沙尔澄看到此处,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喊道:“再耐不得了!”提起皮郎切刀,三脚两步跳上台去。掀翻魂监,按颈一刀,早已红光乱冒,身首两处了。那时戏子只道强盗上来打劫行头,到一齐往戏房乱躲。台下人亦不知甚么事发,各各逃窜,捱挤践踏,,儿啼女哭,人住马不住了。三八倒着急,恐怕没了皮刀,飞风上台寻取,拾刀在手,并死尸也不看见。沙尔澄丢刀只不做声,溜落台来,也乱在众人里,呐声喊,没命的跑了。还有几个做头内中老成的,走将拢来。高叫:“不要乱跑,认拿凶身要紧!”说得快时,却也走得个七八。只见霜三八提着皮刀,还在那里叹息:“这个好汉奇得紧,杀得有趣。”众人已围住道:“不要寻了,凶身在这里!”三八本不杀人,心自凉的。正听得凶身有了,心里想着,有这样高兴的人,不知面貌上有多少义气。他即应声问道:“在那里?在那里?”众人道:“是你!是你!”正要辩时,众人倒恐他行凶,背后将绳子一套。三八还不着忙,当不得众人一拳两脚道:“害着地方怎处?”三八方才呆了。众人问道:“他与你有何冤仇,偏生杀在我们地方上?”一班戏子,将三八乱扯乱推到台上尸边,打打骂骂,问他姓名,只不肯语,鬻应。只见尸边一条纸儿,众人拾起一念。上写:
鞋二双已收明,不知有寸数大的还要一双,奉价。此达,感感。
沙尔澄老爹收
不名
众人听得道:“这是杀人真赃了!鞋子说话不是他本行买卖?原来叫做沙尔澄”。三八见众人问他名姓,死不肯说。赖他是沙尔澄,他才说我叫霜三八。众人不由分说,打点送官,将带血皮刀,着叠在楦头担内。却见一个荷叶包儿,打开一看,是包牛肉。众人大叫起来,不消说得,一法是他杀的了。尸边字儿上写着鞋子事情,不必说是缝皮的了。姓沙的都是回子,今担内又有牛肉。况且血淋淋的皮刀在手。无疑,无疑。
众人连晚带了三八并一副皮担,到县击鼓,登时传开,已拿住杀人的沙尔澄(霜三八)。倒是蔡一官、穆敬萱阿家躲得没影。沙尔澄飞风跑进庵里,喘息方定。自已想这节奇事,就是梦里一般。将皮匠拾刀行像仔细记着,但先自己走脱了。不晓得后面拾着字儿,搜出牛肉,他自供认叫做霜三八,不肯认沙尔澄的事情。因自想道:“杀人大事,可是吹得隐灯的?况蔡家知我姓沙,乘大家手乱脚忙,走为上着罢。”对道人说:“蔡家接我,我搬行李去了。多谢师太。”道人好不快活。尔澄一溜烟走到船埠头搭载,恐怕株连老蒋,不回南京,身边盘缠颇饶,竞改姓海,字口口,混到长安去了。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
却说下钟鸣一行人,到县已黄昏时分,擂鼓禀上。县官听得,事涉不经,收监再审。当晚先出里递收尸朱票。次日升堂,带出霜三八,并一班地方。众人细禀本末,如此这般。
那县官姓岑名苔,是按察司知事。署印德清,贡生出身,湖广辰州府溆浦县人。慕西湖山水,挈资从仕。年纪不上四十,吏事精明。审这节事,听众人禀的时节,却把霜三八冷冷瞧着,见三八或嬉笑自得,或愤懑不平。岑知县早早估定,是个侠客的替身。却寻着的是戏子,这又难解了。再不命到仇恨魏监,认戏作真。及至叫着沙尔澄,三八只不理。
县官叫众人问道:“这凶身可是哑子么?”只见众人扒起捺倒,鸦飞鹊乱,七嘴八丫叉的,沸做一堂,官府一字也听不出。岑知县喝道:“一节杀人重情,成招按律,少不得要个对头,着一个老成地方上来。”众人听得这句,好像曲蟮,个个倒缩。堂上堂下,寂静得就是黄昏古驿的一般。然后那霜三八不慌不忙禀道:“小的霜三八。”那知县到吃一惊。
三八口口籍贯来历后,禀:“本处年荒,到杭存身,到湖生理。及这日台边缝皮,别个杀人,我去收刀。若要冤小的杀人,小的也是恨魏监的,他杀就是我杀一般。若要冤小的是回子沙尔澄,小的死也不服。怎的小的当刑,倒把别人名姓冒个抱不平杀奸贼的美举!”县主听了,倒也口定目呆。天下古今,有这等认真透彻的男子。便叫为首递年戏子报名。比律拢招:
审得沙尔澄即霜三八也,与戏子秋三,必先构冤仇,凑秋三演戏,假扮缝皮,利其刃而杀之,痛哉!秋三出其不意,曾不得抵敌而剖白,致旁人无一解救。而其彼此构衅之由亦莫闻也。当堂研鞫,则曰夙怒阉人,一时愤杀,则真莫须有之案。词颇穷遁,人命儿戏至此乎!本县只据地方目击而可据者有五:杀人凶器切皮刀也;尸边字纸鞋寸尺也;字尾名氏沙尔澄也,沙非华姓,回子也,担有牛肉,回所食也。而况现提血刃,当时其获者乎!则霜三八者,固沙尔澄之乳名无疑也。三八供称军籍,按律:卫军死刑,倍调远卫充军例,收监候夺。
县官当堂,将审单读完。又将各里递分付,以后不许搭台演戏,生事扰民。众人散去不提。
却说蔡平泉到蒋家,淇修知尔澄会不着了。适上元县御白粮事,改了折色,只要出一人,帮押银鞘到天津交纳。淇修打发平泉去了。自家等着尔澄。谁知过了端阳,也没捎个字来。淇修等得不耐烦,寂寞不过。收了五百多两纱罗段匹,合了同伙,到京师出脱。私房带有金珠银两二千金,锁在个旧皮头巾盠内,要去乘便,干个通判行头。船出京口,一路平安。不料到宿迁地方,撞着大王的人了,将他的东西抢得如洗,连众人的共有万金。众人垂头落颈,各自散去。
淇修妄自念头,要去见他头目,讨这头巾盠子。众盗见他跟紧,说这呆子还要纳条性命。走了三五里,并没人烟,见一座高山,巨木参天,郁林蔽日,西边临着大泽,内结一个窝巢。众贼拥进一个为首的泗州人,姓丁名翼,绰号丁张飞。也是有胆力好汉,饿不过了,干此营生。那人生得: 撑着吊眼,满身突肉如拳。鹰眼虾须,遍体缠筋似炭。
不用三头罗刹,鬼见消魂,何必八臂哪吒,神当碎魄。 却说那大王坐下,众贼将这些货物,摊做一地。那皮盠也在,尚锁着的,喝声收好。看见老蒋面生,尚衣冠济楚,问左右道:“这汉子怎的说?”淇修答道:“我本书生,不图财利。因有亲在京,搭船去探。所有段匹,尽当贡献。但头巾皮盝,内有书信,哀恳见还。”那贼头听了说:“我等各有身家,因山东一带,吃白莲教扰害。可恨贪官污吏,将富足平民,埋陷株连,且弄到天荒地白,父东子西,冻饿无聊,逼到这条路上。我看你这娇怯行径,必定到京里谋官做的。但做官第一要诀是黑心,没阴骘,我劝你莫去罢。我这里有粮没兵,有兵没将。要做几件痛快的事,也不能够。敬屈贤者在此主盟。”说罢纳头便拜。慌得淇修回礼不迭。
淇修想道:“虽是绿林,话却正气。料我要去,那皮盝是没分的了,且只得再图机会。”遂各通名贯。淇修道:“既承招纳,当设盟誓。”即焚点香烛,折矢八拜。随出誓书示众:妇不上山,孤客竟放,商税加三,招安各散。丁翼笑道:“妙,妙,结末一句,更合吾意。但是过往赃坯全抄罢了。”大家又笑。只是淇修如坐针毡,那能忘怀。
再提沙尔澄迳到北京,寻了下处,安顿行李,即去刻位金字牌儿,上书“义士皮公之位”。酒肴香烛,誓终身不忘代死之恩。就去打听得兵部职方司张公,目下正该掌选了。尔澄做这奇事以后,一路与人打伙,造得十分唧溜。他便写副大礼,用通家晚生海源拜帖。门上传进,便请见留茶。张公道:“足下过爱口玉,学生到忘却是何亲谊,远来必有见教。”老沙见他兜收,便抿进去道:“南中上元,贵年侄蒋淇修,讳有筠者,晚生之姑表兄弟也。闻大人集思广益,葑菲不遗,特着晚生登龙恭谒。表兄押运御白,到即禀候。诚献一芹,恕乏手奏。”张公见话头温雅,卯眼又对。笑容可掬道:“足下才高年壮,肯觅封侯事乎?学生虚席以待。”一茶又茶,直送出门。点出礼帖,是口鞋二双,湖纱二端。尔澄即忙送进。
到九月初一,是张公掌选,便将尔澄新改名氏海源选了蓟州镇屯捕总司,驻扎蓟门。这个地方兵精粮足,是京师蔽翼。与司道敌体,兼理民词,放铳扯旗,好不威风。离京不远,即日领凭亲谢。张公说道:“略有机会,便当超迁。”尔澄千恩万谢,到任去了。正是:
丈夫会合须有时,燕壁秦关徒自苦。
话表霜三八,问了个车盖儿,一下不打,在监中就缝起皮来,且是热闹。众人道他是冤屈的义士,酒儿食儿,倒不绝口。岑公审定,申详上司,俱批依拟。恐防接县的驳招,即定调了保定镇杂站卫卫军。岑公怜他朦胧受罪,慷慨招承。嘱两个本分军牢,长行押解,每人倒赏十两盘缠,连霜三八也赏五两。三八堂上痛哭,誓必犬马报恩。两个解子,一个犯人,好不相知。把三八脚镣手铐,遣戍文书,装做一袋,各人一个行李包。搭船到苏州,趁着腌腊客人回北的船,货人已满,三人与船家商量,便在那火舱内捱着。行了好多日子,刚到了宿迁地界,船家苏苏拢岸。早有暗号手势,那客人也心照的,说道回此南货,倒是加一。只见几个狰狞大汉,尖帽翁鞋,逐舱跟估,说这水手停当,大家省力。次到梢上,见三人是南音,问船上是甚货,船上不知细底,只得含糊道:“想没货的。”那大汉估定是进京勾当,把行李褡裢一一提过,内一包沉重得紧,那知是三八皮郎家伙。大叫道:“大伙漏税!”将三人不由分说,拖猪拖狗扯去了。
捉到寨里,老丁、老蒋吆喝升堂。八个大汉将行李打散,见官封一件,递上老蒋。拆开一看,便大惊道:“沙尔澄在那里?快请相见!”霜三八听得抖抖衣服,立将起来说:“犯人有。”老蒋道:“胡说!沙尔澄是我同窗,他携资到湖,竟无音耗,原来这干奴才谋死,倒假冒他名氏。”两个解人慌了,霜三八是雪亮的,遂细细禀上:如此这般,害小的问罪充军,文书审招可据。老蒋遂细细看了道:“这人分明是老沙杀的,况且搬演魏监一发是了。”老丁听说,怜霜三八是替死鬼,劝老蒋杀了解人,放了三八罢。三八听了,磕头饶命。老蒋道:“岂有此理。”叫三八后堂分付道:“我明白了,我此时放你,有何难处。看你是义气的,决不肯害解人。不如且到衙所,再图后会。我叫做蒋淇修,南京监生,是上元人。”说了又说,三八牢牢记着。与了三人酒饭,收拾行李,着人护送一程。
却说三个拾得性命,星夜赶到保定。保定卫官接上文书,已是开拆过的,恐有倒换之弊,不肯发出回收。三人禀道:“遇着当官强盗,先查验过了。”卫官晓得是丁张飞的节掯,便与收批。 三八在衙,小心公事。空了仍旧缝皮,倒也糊得口来。一日保定屯局司文书下卫,是关会蓟州屯司比例开屯,是军足饷事。正该三八杂站值差,领了关文,三个日子走到蓟门。正是沙尔澄巡署,先日挂号,次日等他三通吹擂,三个大铳,吆喝开门。三八随着投文进去,却好结束,叫着三八。那沙尔澄眼尖,分付跪着,等领回关,将他面貌仔细模写,看了一回,想了一晌,暗道:“如何得到这里?”问道:“那赍关卫差报名。”三八应道:“沙尔澄。”惊得老沙遍身冷汗,有这般奇事。把头乱点,即叫掩门。叫三八到后堂,问三八道:“你不叫做沙尔澄,怎么到得这里?”三八即将别个杀人,将我抵罪根由,一五一十,细细说了。钞袋内摸出一张烂纸是县官审招底儿。沙尔澄一看,走下来纳头下拜:“义士,义士!”叫个不绝。三八倒惊呆了,不知甚么来头。尔澄即命备酒,两人共是一席。三八那里敢坐,尔澄道:“义士坐了,我好细细讲话。”把南京蒋淇修央我湖州德清下钟鸣置礼,那日看戏,一时愤杀魏阉,逃到京中,姓沙改海,如此这般。足下高义,日日想报。轩后现供着牌位儿,称你做“义士皮公”以志不忘。三八陡然听见南京蒋淇修,暗道又是奇事,也乱点头问道:“蒋公不是上元县监生么?”尔澄道:“正是,怎么晓得?”三八又将宿迁事情细说。将淇修临别“我叫做蒋淇修,南京监生,上元人”,说了又说,“像是偶然落草的”。尔澄叹息一回道:“即同你去救他。”叫书手打点回关,又写一私书与卫官,内封银十二两,与卫官雇军值日,要他发回三八。卫官看书,即叫三八将银子去雇人值日,收拾起身。
到蓟门衙里,尔澄即写一书,差官送张试选。内禀蒋淇修挟资来京,被劫落草,且宿迁系南北要津,宜作急招安,免得聚久凶穷,梗塞通道。张公会意,即转尔澄扬州操捕司,给与官凭。又有私书与尔澄,叫他便道散楚救他出劫。若差官招抚,把淇修上了纸笔做个贼头称呼,玷辱终身并子孙都不便了。尔澄接书叹道:“君子爱人,文人作用何等妥贴。”忙忙收拾起身,将到宿迁地界,早有豪杰拱候。是丁张飞分付过往官船,不照旧例,喝声“官船泊岸讲话。”三八心照,忙应道:“正要与丁爷一会,众位哥不劳动手,泊岸就是。”老沙瞧头便服出舱,分付:“水手泊岸,我去拜客就来”。那些好汉见话有路头,就不声势。一行人走到山寨去,两个头儿出来。尔澄一见淇修,抱头大哭。两边事情,三八也讲明一半。但淇修何以落草,三八何处口着尔澄,两个呜呜的细说。
老丁知老沙是现任官府了,及与丁翼周旋,老丁倒垂泪起来道:“山水有相逢,偏我老丁没个亲人来往。”大家安慰他一番,大开筵宴。老蒋心照老沙来意,先把丁翼无奈到此,只望朝廷招安的说话打动他。丁翼道:“我受招安,倒与官儿做饭,且出头露面过了,虽说自新,终久是有名的贼头,到底受人轻薄”。老沙便将兵部只要差一官,张选君不欲差官招安,深体老丈之意,高明所见略同。老丁快活得紧,指着老蒋道:“罢了,只听沙爷调停,难得知己如此,毕竟有个冠冕局面。”尔澄即问道:“有多少人马,有多少积聚?开一清数。”次日,尔澄与老丁、老蒋商量道:“人有二千,幸得资货颇饶,可使豪杰散去,不致失所。”即叫众人俱来听令:“我等异姓结义,胜于骨肉。初非得已,皆因白莲流毒,官府贪污,逼迫至此。今幸官府怜我无奈,朝廷许我自新。今日公分积聚,可以各归田里,勿踏前辙,笑我绿林中人,皆贪顽无耻。必取灭于锋镝也。”众人泣下,愿如所约,遂大列牛酒。明日各束行李,三五结队,东西南北,各寻生路。
老丁得力数人,收拾细软,俱要跟随老沙到任,将寨屋放火烧光,俱到老沙船里。不则一日,到了扬州,早有属官迎接。三八正名葛俭,做了中军。丁翼改作干羽,作个把总。老蒋令叫小船,别了老沙,忙到家里,举家见了,又喜又悲,悄悄把事情说了。把霜三八、沙尔澄两个生辰朔旦举家香烛拜谢。
看官们,老葛是个手艺中人,薄负义气,坎坷之中,累有奇烈。老沙的性命是他替的,老蒋的骨肉是他全的,老丁的落劫是他出的,南北的梗路是他通的。千古奇人,千古奇事。愧我笔拙,万不能表扬一二而已。
诗曰:
毅魄如虹吐,英风旷古无。
欣期荆聂共,不令郭朱孤。
热血浇寒剑,深情击唾壶。
堪垂金石永,莫笑画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