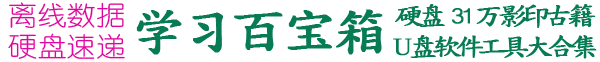休將懶惰負光陰,鐵杵勤磨變繡針。
盜法三番終到手,世間萬事怕堅心。
話說蛋子和尚暗想道:這小洞內必是袁公藏書之所。低著頭鑽進去時,只見裏面彎彎曲曲,或明或暗,或寬或窄,有好幾處像屋的所在。內有石床、石?、石椅、石桌之類,亦有石筆、石硯、石碗、石甕、諸般家伙,俱生成形像,拿不起的,並不見有甚麼書籍。再進去時,洞漸小了,地下低窪約有一二尺深的水,料是盡頭處了。覆身轉來再看一回,已知天書不在其內,鑽出洞來到前面石屋內,周圍細看,叫一聲:「阿也!」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兩邊石壁上鐫滿許多文字,不是天書,又是何物?只是一件,天生石壁掇又掇不去,要抄錄時,紙墨筆硯又不曾帶來,如何是好?且憑著自己記性背他幾條下肚,也不枉辛苦走這兩番。方才站定腳頭,抹一抹眼角,仔細從頭辨認那字腳,忽聞得一陣香氣撲鼻,走出屋外瞧時,白玉爐中早已煙起。慌得蛋子和尚不敢回頭,拽開兩腿,腳不點地一口氣直跑過了石橋。到了松棚裏面,打坐良久,喘息方定。自古道痛定還思痛,想著兩遍到白雲洞中,擔了多少驚怕,受了多少辛苦,不曾掏摸一些子在肚裏,不覺的放聲大哭。一連哭了三日三夜,兀自哀哀不止。只聽得外面大聲問道:「棚中何人,如此悲切?」蛋子和尚聽得人聲,抹乾眼淚,鑽出棚外。看時,卻是個白髮老者。怎生模樣?但見:
眉端抹雪,頦下垂絲。聲似洪鐘,形如瘦鶴。頭裹著一幅青絹巾,腦後橫披大片。身穿著四鑲黃布襖,腰間緊束細?。腳踹方舄,飄飄真欲凌雲。手執籐杖,步步真堪扶老。若非海底老龍,定是天邊太白。
蛋子和尚見他形容古怪,連忙向前打個問訊。那老者又道:「長老不多年紀,緣何獨自一個住在這荒山之中,有甚苦情,啼啼哭哭?試向老夫訴說則個。」蛋子和尚道:「好教長者得知,小僧從幼出家,並無親屬,只因一心好道,要學個驚天動地之術。聞知此山有個白雲洞,內藏著天書道法,因此不辭辛苦,欲求一見。誰知兩遍端午到得洞中,全沒用處。」便把第一遍尋不見天書,第二次見了又不能抄寫,備細說了一遍,說罷又哭起來。老者勸道:「長老不須過哀,聽老夫一言。這白雲洞,老夫少年也曾到過。」蛋子和尚轉悲為喜,忙問道:「長者既曾到過,必見天書,不知抄錄得多少?」老者道:「雖則看見,無計傳取,後來遇著方上一個全真道人,對老漢說此天庭秘法不比凡書可以抄寫。要傳法時,也不用筆臨,也不用墨刷,只用潔白淨紙,帶去到那白玉香爐前,誠心禱告,發個誓願替天行道,不敢為非。祈禱過了,便將素紙向石壁有字處摹去,若是道法有緣的,就摹得字來,若無緣時,一個字也沒有。」蛋子和尚道:「長者可曾摹得?」老者道:「老漢精力已衰,就摹得來也做不及了,故此不曾。」蛋子和尚道:「長者高居何處,若小僧摹得來時,好來請教。」老者道:「老漢離此不遠,閒時又來相探。」說罷策著一根籐杖,望東路一直去了。蛋子和尚似信不信的道:「一不做,二不休。拼得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再守他一年十二個月,好歹要掏摸些兒本事到手。終不然這秘法不許人傳,又鐫他在石壁上怎的?」從此息了念頭,又做著下年的指望。一連四五日內留心訪那老者住處,並無蹤跡,心腸又放慢了。這松棚中怎過得一年四季,少不得打疊個衣包,提一根防身短棍,仍向外方遊行化齋。
不一日來到辰州地方。是甚麼去處?
複嶺重岡,控溪扼洞。山有二酉五城之雄,水有黔江武溪之勝。羅公隱處,鳥鳴占雨無差。辛女化來,石立與人不異。明月洞,泉澄岩上。桃花山,春滿峰頭。齊天秀色每連雲,龍澗腥風常帶雨。
蛋子和尚在辰州往來遊食,非止一日,無事不題。卻說這日偶行至黔陽縣界上,到一個曠野所在高低不等,四望都是亂塚。此時八月下旬天氣,草深過膝,甚是荒涼。走了多時,沒處化一口齋飯吃,看看日色墜西,肚中飢餓。正沒擺佈處,忽見高岡上四五個樵夫挑著柴擔,忙忙而走。蛋子和尚趕上一步,扯住個老成的問道:「貧僧要到黔陽縣中,那一條路去近些?」樵夫指道:「向南只管走下了這岡子,便是羅家畈大路。那裏有幾家莊戶,你再問便了。天色已晚,咱們還要趕過界口去,沒工夫與你細講。」說罷,招呼一聲前面夥計慢走,挑著擔飛也似去了。蛋子和尚不好阻擋,遙問一句道:「這裏喚做甚麼地名?」聽得那邊答個「亂葬崗」三字。蛋子和尚點頭道:「怪得丘塚纍纍,原來是土人埋骨之所。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學些本事,做些功業,揚名於萬代之下,似此一坏黃土,誰別賢愚。」歎了一口氣,向南而行。又去了好多路,地勢漸平,見有幾處田畦禾黍,想是羅家畈了。只不見個居人,也有幾間零星草房,都封鎖著門,沒人住下。只得忍餓又走,看看日落天昏,望見隔溪一林樹木那裏,像有個人家。欲待渡溪而去,不知深淺,走近灘邊,把這防身短棍豎起,向水中一按,打個探子,誰知水深丈餘,那棍直到水底跳將起來,便半橫半豎的向下流溜去了。蛋子和尚打撈不著,只得捨了這棍。沿溪走去看時,約莫又是一箭之地,溪面稍狹,有兩根雜木將草繩捆著,橫倒水面做個浮橋。蛋子和尚性急,便把雙腳踹上,不提防草繩日久朽爛,這邊身勢去得太重,把兩根木頭一腳蹬開。好個莽和尚,收腳不迭,蹋地躺將下去。喜得是個淺處,剛剛淹到乳旁,並不曾吃半口水兒,只將衣包都打濕了。左腳陷在深沙裏面,掙得脫時,一隻麻鞋已失了。
當時無可奈何,不管三七二十一,拖泥帶水走過那一岸去。將濕布衫和那裙兒褲兒脫下,絞乾了水,依舊穿上。把右腳麻鞋一發脫了拋去。赤了雙腳,提了濕衣包,遙望著樹林而走。
約莫離那林子還有半里之遠,早見有數間茅舍。近前看時,卻也閉著門在那裏。門外茅簷邊側鋪著一窩亂草,一個頭陀盤著雙膝在上打坐,面前擺一卷經典,左首安放包裹,倚著一根兩頭鐵裹的齊眉短棒兒。蛋子和尚去向前叫聲:「老師父,貧僧是失水逃命的,求慈悲救護則個。」那頭陀垂著眼皮,全然不睬。蛋子和尚又叫道:「貧僧飢餓了,老師父帶得有乾糧,望布施些兒,見在功德。」那頭陀只是不睬。蛋子和尚道:「啐!是木的還是石的,只不開口。莫待纏他,我且去敲門,敲得開時,化碗熱湯來吃也好。」又猛然想道:「這屋內不知有人住沒人住,那頭陀同是佛門中出身,尚然如此,黑夜敲門打戶,知道人心喜怒如何。打煞也只一夜,且喜不是個寒天,這濕衣裳在身上暖過一夜,好歹也乾了,衣包便慢慢的整理也不打緊。」把搭膊將腰束緊,也來簷下向頭陀對面打坐。
那頭陀見這裏和尚坐下去時,便罵道:「死禿驢,這簷下是老爺要伸腰躺腳的,恁般不達時務,不管濕衣裳胡亂擠來,叫老爺怎得安穩。」蛋子和尚想道:「那裏有這樣的出家人,開口便罵,恁地粗莽。」沒奈何耐了氣,又對他說道:「貧僧走錯了路頭,一日沒討得口齋飯,又失腳落在溪中,渾身打濕了。夜晚沒處去,權借這簷下歇過一宵,明早就行,與老師父沒甚妨礙。望乞相容則個。」那頭陀愈加發狠罵道:「死禿驢你不認得老爺麼,老爺叫做石頭陀,異名石羅漢的便是。一生遊方,行也是獨行,臥也是獨臥,不慣與人合夥。你這禿驢知是好人歹人,來此混帳,走便走,不走時一棍就結果了你性命。」說罷,便站起身來,將手去摸那棍棒。蛋子和尚又餓又冷,身邊又沒有器械,只怕那頭陀了得,敵他不過,慌忙立起道:「老師父息怒,貧僧迴避便了。」那頭陀又罵道:「死禿驢,怕你不迴避,須是遠遠的與我閃開,若近在側時,老爺一眼瞧見休想恕饒。」
蛋子和尚連聲道:「不敢,不敢。」便提著衣包望屋後便走。黑暗中正不知那裏去好,信步走去到得樹林中間,只見一株大松亭亭直上約有百尺之高。心下想道:「這樹上到好棲身,只是怎得上去?」心生一計,將搭膊解下連衣包拴在腰裏,向那松樹旁一根小樹跨上去,一手攬著松枝,將身就勢越過那樹,又盤上幾層,揀個大大的丫杈中,似鳥鵲般做一堆兒蹭坐著。
方才安身得牢,忽聽得下面聲響。蛋子和尚眼快,在星光下仔細一看,只見那頭陀提著齊眉短棍在樹林左右行來步去,東張西望,口裏哼道:「死禿驢真個那裏去了。」穿過林子又去一段路才轉來,倒拖著棍棒,向舊路徐徐而去。
蛋子和尚看了叫聲慚愧,且喜不遭他毒手。只是一件:那頭陀獨自一個坐在人家門首,好不冷淡,得個人作伴也好,為何抵死不容。比及讓了他罷了,又來東尋西覓,只恐還在左近,放心不下。其中必有緣故。終不然要做打家劫舍的勾當,怕我礙眼。這個荒村草舍將有甚大財鄉,動了他火,好生難解。且莫管他,自己安息一時再處。方欲閉眼,不覺肚中餓得疼痛,腸鳴起來。蛋子和尚道:「這一夜好難過,就熬過今夜來朝怎得氣力跳下樹去?便跳下時跑走不動,倘遇了那賊頭陀,乾折個性命與他。聞得仙人餐松茹柏,我且學他一學。把松枝上嫩毛摘來試嘗,雖不可口,卻也清香。吃了些兒,引得性起,不論老的嫩的滿把的放在口中去,只管亂嚼嚥下了許多,也覺得腹中充實了些。
忽然一陣風,遠遠的聞得號呼哭泣之聲。蛋子和尚道:「奇怪,這裏又不是鬧熱村坊,此聲從何而來?」側耳再聽時,其聲哀急,又像婦女聲音,分明在前面茅屋那一搭兒。蛋子和尚猛省道:「是了,一定是那賊頭陀幹了不公不法的事出來。」欲待不理,心頭氣忿忿的怎忍得住!我且悄悄地去探個下落,也得放懷。當時解下腰間衣包,縛在樹上,重把搭膊拴緊了腰,分開松枝,望下踴身一跳。兩腳點地,毫無傷損。將身抖一抖,走出林子,照前路一步一步的捱去。
約莫茅屋相近,悄悄地舒頭去望那茅簷下,略無動靜。再走幾步,向前看時,已不見了頭陀。走上簷頭左右細看,端的不見了。側耳聽時,裏面哭聲也住了。蛋子和尚心下疑惑,輕輕的推那門兒,原來是兩扇舊白板門。這石頭陀在裏面用棍撐著,撐得不牢,初時推不開,以後用力一??雙,撲的一聲棍兒倒地,左一扇門兒早開。這茅房原來是小小三間開闊,兩進一披頭。一進兩邊安放些做屋的土磚木料,更有幾處粗重家伙,中間空個走路。第二進做個內室,左首披屋裏面安排鍋灶。石頭陀脫得上身赤膊,正在灶下燒火煮飯吃,聽得開門響,慌忙起身來看。
說時遲,那時快,蛋子和尚一腳踹進門來,正踹著棍兒,便曲腰下去綽棍在手。知道裏面有人出來,急向木料堆裏一閃,閃過。石頭陀黑暗裏急切不辨,見大門開著,便鑽出外去探望。蛋子和尚乘著披屋下有些燈光透出,到對著裏面天井一溜進去。這邊進去的還不曉得裏面詳細。那裏面暗處,有個老婆婆先已瞧見和尚,叫聲:「啊呀!又是一位羅漢來到,死也,死也!」蛋子和尚聽得聲音,情知有些蹊蹺,卻待進步盤問,只聽大門右扇開的一響,是那石頭陀作勢推開。蛋子和尚慌忙退出,仍伏在木料堆邊。只見那石頭陀踏進門內時,覆身向外,發狠的鬼叫道:「有誰大膽的,敢進來麼?」喊了一聲便坐身下去摸那地下的棍兒,誰知這棍落在蛋子和尚之手。和尚有了器械,早壯了三分膽氣,那時看得仔細,就他蹲下去時,做個水面撈衣勢,將棍可對著他屁股竭力向上一挑。那頭陀出其不意,精頭皮倒垂磕下,橫身臥地。蛋子和尚怕不了事,舉棍又打下去。那邊把右手來擋,正迎著棍兒去得重,只一聲響,打折了兩個指頭,連皮兒掛著。石頭陀負痛便叫:「好漢饒命!」蛋子和尚已知得了便宜,左手持棍,右手?開五指,一把抓去,連腰胯連肚皮做一堆兒提起,到天井裏面高高的向下一擲,那頭陀殺豬也似叫喊。蛋子和尚向前一步,將右腳劈胸踹定,捻起升籮般大的拳頭在他臉上晃一晃,喝道:「賊頭陀,你要死要活?」那頭陀方才認得就是落水的和尚,只叫:「師兄,是俺得罪了,饒命罷。」蛋子和尚罵道:「賊頭陀,我只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少林寺出尖的打手,原來恁般沒用的蠢東西。叫甚麼石羅漢,你便是鐵羅漢,我也會銷鎔你起來。迎暉寺前偌大一塊大搗衣石,我也只一拳打個粉碎。先前我再三讓你,是我出家人本等。你又到林子裏面來尋趁我,你實說在此做甚勾當,惹得他家啼啼哭哭。快快說來還有個商量,若半句含糊,我也不用棍打,只教把你做個搗衣石兒,試我拳頭一試。」
說罷,便把棍兒撇下,右手捻起拳頭待打。那頭陀心慌,又被蹬緊了胸脯好不自在,儘力叫道:「佛爺爺佛祖師,放俺起來,待俺細說。」蛋子和尚道:「賊頭陀,便放你起來,料你也不敢走。」卻待鬆腳放他,只聽得屋裏黑暗中有人叫道:「師父與我家伸冤則個!莫放鬆他。」蛋子和尚認得就是先前一般的聲音,定了腳看時,只見個白髮老婆婆,腰馱背曲,半蹲半走的摸將出來。到天井中,朝著蛋子和尚,連連的磕頭,只叫伸冤。蛋子和尚道:「老人家不要多禮,你有甚冤情,快說來,我與你做主。」老婆婆道:「這天殺的,壞了我家媳婦母子兩口的性命。」只這一句引得蛋子和尚心頭火起,將腳跟向那頭陀的心坎裏狠力的蹬上一下,那頭陀大叫一聲,口中鮮血直噴出來。有詩為證:
僧家淨業樂非常,何事芒鞋走十方。
做賊行淫遭惡報,分明好肉自剜瘡。
蛋子和尚方纔收起了腳,扯起老婆婆,問其緣由。老婆婆啼哭起來,指著披屋裏面,說道:「師父去看便知。」蛋子和尚還怕那頭陀奸詐,再要加他上幾拳,只見他直挺挺的不動,踢他一腳也不做聲了,方才放心。走到披屋裏去,把壁上的掛燈兒剔明,那鍋中兀自熱騰騰的氣出,揭開鍋蓋看時,噴香的一鍋熱飯,是那頭陀才煮下的。蛋子和尚正在要緊之中,便道:「我且吃他兩碗,卻又理會。」向灶前揀起一把茅柴點著,去找個碗兒來用,剛剛的在破廚櫃內取得一隻磁碗、一雙柳木筋兒,猛看見牆角頭又是一個人睡著,倒吃了一嚇。仔細打一照,原來是個婦人剝得赤條條的,死在血泊裏面。卻好老婆婆帶著哭也摸進來了。蛋子和尚問道:「這婦人是你甚麼人?為何而死?」老婆婆道:「一言難盡。」拖著凳子頭兒教師父請坐,「等老身慢慢的告訴。」蛋子和尚道:「你莫管我,儘你說,我都聽得。」便盛著飯一頭吃,一頭聽那老婆婆的說話。
老婆婆坐在門檻上,從頭至尾告訴道:「老身家姓邢,這死的是老身的媳婦。我的兒子叫做邢孝,在這羅家畈種田為生,因本縣縣令老爺貪財,責取里正要百來擔好丹砂。這丹砂雖說出在辰州,卻不是黔陽縣土產,卻在沅州老鴉井內,這井好不寬大,四圍生成的青石壁,須要積下乾柴放起火來,燒得那石壁迸開,方才有砂現出。這裏羅家畈莊戶種田空閒時,都慣做這行生意。里正科斂百姓的銀子,顧人去到那邊納了地頭錢,取丹砂奉承縣令。這畈裏幾家莊戶都接受得工錢,但是有老婆的都寄在親眷人家去了。只我家媳婦有了五個月身孕,出門不得,又是老身七十多歲兩口兒做伴,在這房子內看守。一月前邢孝還在家的時節,媳婦患個肚痛的症,急切沒個醫人。剛遇這頭陀上門化齋,兒子回他道:「現有病人在家,沒心緒齋得你。」他問是甚麼病,兒子不合回他說道:「媳婦有五個月身孕了,現今患肚痛,只怕小產。」那頭陀道:「我叫做石頭陀,石羅漢。不但會看經,也曉得些醫理。有個草頭方兒,依我吃了肚痛便止。又能安胎。」兒子也是沒奈何,只得憑他解開包裹,把幾味草頭藥煮來灌下,果然肚痛止了。當日請他一頓飽齋,又不要錢,竟自去了。只道他是好人。昨日又到這裏化齋,媳婦回他道:「男子漢不在家,改日來罷。」他不肯去,就把言語調戲我媳婦起來。媳婦閉了門進來了,不理他。他坐在門首唸經,只是不去。到深夜時分,老身睡了,媳婦還在中間績麻,那頭陀曉得家裏沒人,悄悄地把門弄開,竟走了進來。將媳婦抱住,恐嚇他道若聲喚就殺了你。當下被他強姦了,這還是小事。又教媳婦去燒下一鍋滾湯,我要洗個澡。媳婦只得與他燒水,又教傾一半在桶裏,那天殺的原來不要洗澡,把包裹打開取一丸白藥教媳婦吃了,後來易產。吃下便覺有些肚痛。他又解出兩隻新草鞋來浸在鍋內,對媳婦說道:「我要與你借件東西,合個長生不死之藥。藥成時送些與你吃了,大家升仙。」媳婦道:「借甚麼東西?」他道:「要你五個月的血胎。」媳婦慌急了,哭拜告饒。那天殺的雙手抱定,剝個寸絲不掛,將他綁住手腳,按在桶上,把熱湯揉他的肚皮,媳婦痛極了,再三哀告,只是不允。又將鍋內兩隻熱草鞋輪番在肚皮上揉擦,可憐血胎墜下,我媳婦當時血崩而死。老身嚇壞了伏在後面,不敢則聲。只聽那天殺的說道:「到是個男胎。」他又在布袋內取米造飯,只待吃了便走。不期遇著師父到來,奈何了他,正是天理昭彰,惡人自有惡人收。」
蛋子和尚問道:「他取下血胎在那裏?」老婆婆道:「想收拾在包裹裏面了。」因這老婆婆話長,蛋子和尚也不知吃了幾碗飯,把鍋內吃個罄盡,只剩個鍋底。和尚放下碗筷,向廚櫃上層尋著他的包裹,就在鍋蓋上打開看時,裏面又有小布包兒,解開來是一條布裙子,正裹著血團團的小廝和那胎衣在內。又是一包十多兩散碎銀子。又有一疋細白布包著一件裂火袈裟,也有件直裰子,及零星衣服。另有個布囊盛下二三升雜米。蛋子和尚觀看血胎,心下想道:「不知他那長生不死的方兒是真是假,配甚藥物,怎麼取用。可惜造下這罪孽,棄之無用了。」念聲阿彌陀佛,將血胎連布裙子遞與老婆婆。老婆婆看見了,重新哭起肉來。蛋子和尚開了銀包,揀幾塊大的,約莫倒有五六兩,把與老婆婆道:「這銀子你將去,斷送了媳婦。」其餘自家收拾起了。
此時天已漸明,走出天井,看那頭陀面皮發黃,已自沒氣。腳下穿的到好一雙青布僧鞋,蛋子和尚剝來穿下。將這根齊眉鐵包頭的棍兒挑了包裹,叫聲:「老人家,那賊頭陀已死了,太平無事,我去了也。」老婆婆道:「師父你去不得。」蛋子和尚真個住了腳,問道:「為何去不得?」老婆婆道:「你雖然替我除了這害,撇下了兩個死屍,教我如何擺布?」蛋子和尚道:「也說得是。我且把賊頭陀的屍首拋在荒郊,再作計較。」放下棍棒包裹,一手抓著那死頭陀的腰褲,恰似小雞兒一般提起屍首,出了門,直到林子裏面去。此時天已大明,認得夜來這株大松樹,正待撇下屍首,踛上去取那衣包。只聽得遠遠的有人喝道:「清平世界,那裏和尚殺了人,撇在這個地方。」蛋子和尚定睛看時,林子後面有七八個莊家,一個個背著包裹、跨口腰刀、提口朴刀,飛也似奔將來。蛋子和尚不慌不忙撇屍在地,早踛上樹去了,取得衣包在手。眾莊家把這株大松樹團團圍定,蛋子和尚在樹上叫道:「貧僧不是殺人的,是殺那殺人賊的。列位閃開,待貧僧下來相見。」說罷,便撲地一跳,跳出眾人圈外。眾莊家又把和尚圍住,盤詰來由。蛋子和尚道:「列位且說從那裏來?」眾莊家道:「我們奉縣令老爺差委,往沅州採取丹砂。昨晚到縣和里正交納,今早起個五更走到這裏。」蛋子和尚道:「列位中可有邢孝麼?貧僧要報個信兒與他。」眾人裏面走出個矮黑漢子,上前道:「在下便是邢孝。」蛋子和尚指著這死屍道:「這個賊頭陀便是你七世的對頭。」邢孝聽罷這句話,好似一千個榔槌在他心上亂敲,面色都變了,一把扯住和尚道:「對我說個明白。」蛋子和尚道:「如今我說了,你也不信。貴居去此不遠,列位休散了,大家去做個證見。」眾人道:「邢大哥莫慌。既然同到宅上,自然有個分曉。」當時眾人隨著和尚一路走,雖然腳尖兒同向前,腳跟兒同向後,卻有三種情況不同。蛋子和尚的心下欣欣喜喜,好像撐船的逆風收港,有個結束了;眾莊家心下疑疑惑惑,好像看把戲的,不知搬出甚故事來;只邢孝的心下驚驚恐恐,好像解察院的訪犯一般,有罰無賞。正是背人偷酒吃,冷暖自家知。
卻說老婆婆見和尚去了,心中害怕起來。勉強去舖上拽一條被單,將婦人的屍首就地蓋了。摸到門前,兩頭看著,又不知那一條是來路,東一張西一望,只等和尚到來區畫這事,夢裏也想不到兒子回來。這裏老眼模糊還未分明,邢孝先走一步,早已看見,叫道:「老娘,你緣何獨自一個在門外看誰?媳婦在那裏,不陪伴你?」老婆婆一見兒子,便扯住放聲大哭道:「我兒你早歸一日,也不見得好端端的媳婦被甚麼石頭陀石羅漢弄死了。」邢孝道:「怎麼說?」老婆婆哭道:「他死得好苦!」邢孝搶進門來看時,眾人隨後都到了,一擁上前,到把那老婆婆擠在後面。只見邢孝連被單抱起媳婦,放在後屋中間,對著搥胸大哭。眾莊家人人悽慘,問蛋子和尚道:「這事怎的樣?」蛋子和尚道:「等邢大哥哭過了,再問老娘便知。」邢孝道:「我娘年老之人,須是長老與我剖個明白。」蛋子和尚便把自家落水借宿直到打死了頭陀,後面你家老娘與我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備細述了一遍。邢孝止不住腮邊落淚。眾人無不咬牙切齒。老婆婆埋怨兒子道:「都是你聽信了那天殺的鬼話,吃什麼草頭方安胎藥,引得那賊頭陀上門上戶,弄出這事來。如今一命便是兩命,卻不是你自家害了妻兒一般?」眾莊家勸道:「老娘如今說也是無益了。且喜得遇著這位長老,報了冤仇,死者也得瞑目。只是如今林子裏躺著一個,家裏躺著一個,不是個道理,也該作速計較。家裏有米麼,可煮些飯來吃了,相煩長老同到縣令相公處首明。等他差官相驗,順便就帶口棺木下來盛殮,省得過些時被做公的看見林子內屍首,又造謠生事,在地方上做一場生意。」蛋子和尚道:「聞得縣令是個贓官,告許他怎的,要埋時,自家埋下便罷了。」邢孝道:「卻使不得。」
當下敲火煮飯,眾人各剝得有些乾菜,都將出來,等飯熟大家吃飽。老婆婆把銀子遞與邢孝,說其緣由,邢孝又向和尚叩謝。眾人道:「也要老娘去走一遭。」邢孝安排個羊頭小車,教老娘坐上,鎖了門,央一個相厚的莊戶同推著車兒。蛋子和尚提了棍,把兩個包裹打併做一個背著,眾人一擁到黔陽縣來,等不多時候,縣令正升晚堂,眾人將血胎一包當堂呈上,首告地方人命事。縣令把一干人逐一審過,錄了口詞,當交縣尉一員下鄉相驗。到次日晚堂回話無異,官批:
石頭陀係無籍遊僧,所犯雖重,已死不究其屍。責令地方埋訖。沈氏著邢孝自行殯葬,蛋子和尚因義忿殺傷免罪。餘人都發回家去。單留蛋子和尚在縣有話吩咐。
退堂之後,縣令喚和尚到了後堂書房中,屏去左右,誇獎了他幾句,次說道:「我有封緊要書信禮物,要寄到慶元府親戚那邊,路程遙遠,沒個可託之人。適才聞得你恁般義氣,又且英雄了得,肯與我幹這件功勞,回來之日重重酬謝。」蛋子和尚道:「貧僧遊方之人,那一處不去,既然相公尊委不敢有負。」縣令大喜,喚心腹吳孔目送長老到城隍廟居住,庫上支兩貫足錢發與道士,著他供給等候修書完日,標撥起身。不題縣令進衙收拾金珠銀兩,打?箱籠之事。
卻說蛋子和尚和吳孔目到城隍廟中,先有官身報知道士,迎進客堂坐下。蛋子和尚看見廟宇傾頹,房屋敝壞,道士也衣衫襤褸,因問道:「這神廟香火可盛麼?」道士道:「神道極靈,香火也不絕的。」蛋子和尚默然無語。茶罷,吳孔目將兩貫錢交付與道士,便起身吩咐好生管待。道士就把三百文錢送與吳孔目,折個東道,送他出門去了。道士問了蛋子和尚吃葷用酒,忙忙的吩咐廟祝買東買西,安排停當,擺設在臥房裏面,請他來坐。又把自己鋪蓋搬了出來,讓這房與和尚安歇。蛋子和尚飲酒中間,問起道:「既然神道又靈,香火又盛,為甚廟宇恁般狼狽?」道士嘆口氣道:「雖然如此,在小道卻有損無益。」蛋子和尚低聲問道:「莫非縣令難為你們?」道士紅了臉,不敢答應。蛋子和尚又道:「貧僧與這縣令素不相識,只今日要貧僧到慶元府走一番相留在此,貧僧一時應承了,不知是甚麼書信。聞得縣令是個貪官,刻剝百姓,足下必知其詳,你休疑慮著我,但說不妨。我們出家人,難道到與贓狗做一路不成?」道士見他言語出得至誠,便把兩指做個錢圈兒,說道:「縣令老爺愛的是那個東西。莫說別件,只這城隍廟裏,不論月大月小,要納還他香火錢十貫。不足數時,小道還要賠補,若布施得些米料在這裏,縣中便來取用去了。所以門內廊廡都無力修整。他戴了?頭,神道也是勢利他的。雖說威靈顯赫,只在小百姓上做工夫,撞著做官的全無報應。」蛋子和尚道:「他是那裏人氏,有甚親戚在慶元府,便一封書信打甚麼緊,何必用著貧僧。」道士道:「他正是慶元府慈谿人氏,姓侯雙名明宰,在此做過四年官了。每年積下若干贓物運至家中。恐有?虞,定要個有本事的護送將去。去年用人不當,到洞庭湖中被劫去了,聞得今番要走旱路,他留著禪師一定為此。他原是窮儒出身,只這任官,家中解庫也開過好幾個了,貪心兀自不止,禪師你道狠也不狠。」蛋子和尚道:「原來恁地。」道士道:「適才禪師盤問,小道多口了,路途中在他們管家或公差面前,是必休題。」蛋子和尚道:「不消吩咐。」當晚酒飯已罷,道士別去了。蛋子和尚在房中思想道:「這些詐人的錢財,到叫我替他送了去。這事不成,不成。」睡到五更,只推解手,取了包裹棍棒出了廟門,一溜煙走了。明日道士不見了和尚,慌了手腳,稟知縣令。縣令道:「早是不曾託他幹事,這遊方和尚全無信行。」也不責備道士,只追他這兩貫錢完庫,道士只得又去生錢借債,補完這項,倒折了三百文錢,一頓酒飯。後來侯縣令多用賄賂,得陞京職,自家建個生祠在縣中,去任後被眾百姓夜半時抬那祠中的土偶,折了腳,撇在糞坑裏面了。縣令在中途被馬驚墮地,折足而死。可見天道不爽,此是後話。有詩為證:
儘人吃著亦無多,苦苦貪求卻為何。
試看墨吏終當敗,縱免人誅有鬼訶。
卻說蛋子和尚那日出了黔陽縣,離了辰州,又往湖北荊南一路遊去。逢山看山,逢水看水,留連光景,不覺又過了一年。看看李白桃紅,又早梅黃杏紫,蛋子和尚切記著本等前程,預先買就一百張潔淨純綿大紙,帶歸雲夢山下草棚中來。將紙預先編個一二三四的號數,把石頭陀這疋細白布縫個袱包兒包著,又去清水潭中洗個淨浴。
到端午日,早起在地灶中煨飯吃飽,正待扎縛停當,只見雲暗山頭,下著一陣大雨。蛋子和尚道:「卻不是晦氣!這雨日日不下,偏是今日與我送行起來。」只得在松棚內望空磕頭禱告道:「某今日有緣得見天書之面,望乞斂雲收雨,速現紅輪。」看看捱到巳牌時分,雨已停止。和尚喜不自勝,取了綿紙,提了齊眉棍棒便走。此是第三遍了,路徑已熟。只山地濕,高下崎嶇,況且冒霧而行,只恐遲誤。忙忙的向前,比及霧氣將散,石橋也到了。蛋子和尚舉目看時,吃了一驚。原來這橋是天生成一條青石,經雨後,其滑如油。隨你節節小心,如何把得腳住。有人問道:「那三百六十日的濃霧,難道石橋沒些濕氣,直等這番大雨?」看官有所不知。但是尋常的霧,都是地氣上升,天氣不應,其氣氤氳迷亂而成,所以沾衣而濕,觸石則潤,久而不解。這白雲洞的霧,是霧幕中噴出來的,只是乾霧。分明是蜃樓海市,望之有形,就之無?。所以前兩遍石橋全無濕氣,今番雨後難行也。若是三尺四尺,不多步兒也還好處,這三丈多長哩!下面不測深淵,可是取笑得的。正是:
除非插翅飛將去,動腳之時必墮傾。
是這般說時,第三番又去空了。卻不道風急雨至,人急智生。畢竟用著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盜法三番終到手,世間萬事怕堅心。
話說蛋子和尚暗想道:這小洞內必是袁公藏書之所。低著頭鑽進去時,只見裏面彎彎曲曲,或明或暗,或寬或窄,有好幾處像屋的所在。內有石床、石?、石椅、石桌之類,亦有石筆、石硯、石碗、石甕、諸般家伙,俱生成形像,拿不起的,並不見有甚麼書籍。再進去時,洞漸小了,地下低窪約有一二尺深的水,料是盡頭處了。覆身轉來再看一回,已知天書不在其內,鑽出洞來到前面石屋內,周圍細看,叫一聲:「阿也!」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兩邊石壁上鐫滿許多文字,不是天書,又是何物?只是一件,天生石壁掇又掇不去,要抄錄時,紙墨筆硯又不曾帶來,如何是好?且憑著自己記性背他幾條下肚,也不枉辛苦走這兩番。方才站定腳頭,抹一抹眼角,仔細從頭辨認那字腳,忽聞得一陣香氣撲鼻,走出屋外瞧時,白玉爐中早已煙起。慌得蛋子和尚不敢回頭,拽開兩腿,腳不點地一口氣直跑過了石橋。到了松棚裏面,打坐良久,喘息方定。自古道痛定還思痛,想著兩遍到白雲洞中,擔了多少驚怕,受了多少辛苦,不曾掏摸一些子在肚裏,不覺的放聲大哭。一連哭了三日三夜,兀自哀哀不止。只聽得外面大聲問道:「棚中何人,如此悲切?」蛋子和尚聽得人聲,抹乾眼淚,鑽出棚外。看時,卻是個白髮老者。怎生模樣?但見:
眉端抹雪,頦下垂絲。聲似洪鐘,形如瘦鶴。頭裹著一幅青絹巾,腦後橫披大片。身穿著四鑲黃布襖,腰間緊束細?。腳踹方舄,飄飄真欲凌雲。手執籐杖,步步真堪扶老。若非海底老龍,定是天邊太白。
蛋子和尚見他形容古怪,連忙向前打個問訊。那老者又道:「長老不多年紀,緣何獨自一個住在這荒山之中,有甚苦情,啼啼哭哭?試向老夫訴說則個。」蛋子和尚道:「好教長者得知,小僧從幼出家,並無親屬,只因一心好道,要學個驚天動地之術。聞知此山有個白雲洞,內藏著天書道法,因此不辭辛苦,欲求一見。誰知兩遍端午到得洞中,全沒用處。」便把第一遍尋不見天書,第二次見了又不能抄寫,備細說了一遍,說罷又哭起來。老者勸道:「長老不須過哀,聽老夫一言。這白雲洞,老夫少年也曾到過。」蛋子和尚轉悲為喜,忙問道:「長者既曾到過,必見天書,不知抄錄得多少?」老者道:「雖則看見,無計傳取,後來遇著方上一個全真道人,對老漢說此天庭秘法不比凡書可以抄寫。要傳法時,也不用筆臨,也不用墨刷,只用潔白淨紙,帶去到那白玉香爐前,誠心禱告,發個誓願替天行道,不敢為非。祈禱過了,便將素紙向石壁有字處摹去,若是道法有緣的,就摹得字來,若無緣時,一個字也沒有。」蛋子和尚道:「長者可曾摹得?」老者道:「老漢精力已衰,就摹得來也做不及了,故此不曾。」蛋子和尚道:「長者高居何處,若小僧摹得來時,好來請教。」老者道:「老漢離此不遠,閒時又來相探。」說罷策著一根籐杖,望東路一直去了。蛋子和尚似信不信的道:「一不做,二不休。拼得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再守他一年十二個月,好歹要掏摸些兒本事到手。終不然這秘法不許人傳,又鐫他在石壁上怎的?」從此息了念頭,又做著下年的指望。一連四五日內留心訪那老者住處,並無蹤跡,心腸又放慢了。這松棚中怎過得一年四季,少不得打疊個衣包,提一根防身短棍,仍向外方遊行化齋。
不一日來到辰州地方。是甚麼去處?
複嶺重岡,控溪扼洞。山有二酉五城之雄,水有黔江武溪之勝。羅公隱處,鳥鳴占雨無差。辛女化來,石立與人不異。明月洞,泉澄岩上。桃花山,春滿峰頭。齊天秀色每連雲,龍澗腥風常帶雨。
蛋子和尚在辰州往來遊食,非止一日,無事不題。卻說這日偶行至黔陽縣界上,到一個曠野所在高低不等,四望都是亂塚。此時八月下旬天氣,草深過膝,甚是荒涼。走了多時,沒處化一口齋飯吃,看看日色墜西,肚中飢餓。正沒擺佈處,忽見高岡上四五個樵夫挑著柴擔,忙忙而走。蛋子和尚趕上一步,扯住個老成的問道:「貧僧要到黔陽縣中,那一條路去近些?」樵夫指道:「向南只管走下了這岡子,便是羅家畈大路。那裏有幾家莊戶,你再問便了。天色已晚,咱們還要趕過界口去,沒工夫與你細講。」說罷,招呼一聲前面夥計慢走,挑著擔飛也似去了。蛋子和尚不好阻擋,遙問一句道:「這裏喚做甚麼地名?」聽得那邊答個「亂葬崗」三字。蛋子和尚點頭道:「怪得丘塚纍纍,原來是土人埋骨之所。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學些本事,做些功業,揚名於萬代之下,似此一坏黃土,誰別賢愚。」歎了一口氣,向南而行。又去了好多路,地勢漸平,見有幾處田畦禾黍,想是羅家畈了。只不見個居人,也有幾間零星草房,都封鎖著門,沒人住下。只得忍餓又走,看看日落天昏,望見隔溪一林樹木那裏,像有個人家。欲待渡溪而去,不知深淺,走近灘邊,把這防身短棍豎起,向水中一按,打個探子,誰知水深丈餘,那棍直到水底跳將起來,便半橫半豎的向下流溜去了。蛋子和尚打撈不著,只得捨了這棍。沿溪走去看時,約莫又是一箭之地,溪面稍狹,有兩根雜木將草繩捆著,橫倒水面做個浮橋。蛋子和尚性急,便把雙腳踹上,不提防草繩日久朽爛,這邊身勢去得太重,把兩根木頭一腳蹬開。好個莽和尚,收腳不迭,蹋地躺將下去。喜得是個淺處,剛剛淹到乳旁,並不曾吃半口水兒,只將衣包都打濕了。左腳陷在深沙裏面,掙得脫時,一隻麻鞋已失了。
當時無可奈何,不管三七二十一,拖泥帶水走過那一岸去。將濕布衫和那裙兒褲兒脫下,絞乾了水,依舊穿上。把右腳麻鞋一發脫了拋去。赤了雙腳,提了濕衣包,遙望著樹林而走。
約莫離那林子還有半里之遠,早見有數間茅舍。近前看時,卻也閉著門在那裏。門外茅簷邊側鋪著一窩亂草,一個頭陀盤著雙膝在上打坐,面前擺一卷經典,左首安放包裹,倚著一根兩頭鐵裹的齊眉短棒兒。蛋子和尚去向前叫聲:「老師父,貧僧是失水逃命的,求慈悲救護則個。」那頭陀垂著眼皮,全然不睬。蛋子和尚又叫道:「貧僧飢餓了,老師父帶得有乾糧,望布施些兒,見在功德。」那頭陀只是不睬。蛋子和尚道:「啐!是木的還是石的,只不開口。莫待纏他,我且去敲門,敲得開時,化碗熱湯來吃也好。」又猛然想道:「這屋內不知有人住沒人住,那頭陀同是佛門中出身,尚然如此,黑夜敲門打戶,知道人心喜怒如何。打煞也只一夜,且喜不是個寒天,這濕衣裳在身上暖過一夜,好歹也乾了,衣包便慢慢的整理也不打緊。」把搭膊將腰束緊,也來簷下向頭陀對面打坐。
那頭陀見這裏和尚坐下去時,便罵道:「死禿驢,這簷下是老爺要伸腰躺腳的,恁般不達時務,不管濕衣裳胡亂擠來,叫老爺怎得安穩。」蛋子和尚想道:「那裏有這樣的出家人,開口便罵,恁地粗莽。」沒奈何耐了氣,又對他說道:「貧僧走錯了路頭,一日沒討得口齋飯,又失腳落在溪中,渾身打濕了。夜晚沒處去,權借這簷下歇過一宵,明早就行,與老師父沒甚妨礙。望乞相容則個。」那頭陀愈加發狠罵道:「死禿驢你不認得老爺麼,老爺叫做石頭陀,異名石羅漢的便是。一生遊方,行也是獨行,臥也是獨臥,不慣與人合夥。你這禿驢知是好人歹人,來此混帳,走便走,不走時一棍就結果了你性命。」說罷,便站起身來,將手去摸那棍棒。蛋子和尚又餓又冷,身邊又沒有器械,只怕那頭陀了得,敵他不過,慌忙立起道:「老師父息怒,貧僧迴避便了。」那頭陀又罵道:「死禿驢,怕你不迴避,須是遠遠的與我閃開,若近在側時,老爺一眼瞧見休想恕饒。」
蛋子和尚連聲道:「不敢,不敢。」便提著衣包望屋後便走。黑暗中正不知那裏去好,信步走去到得樹林中間,只見一株大松亭亭直上約有百尺之高。心下想道:「這樹上到好棲身,只是怎得上去?」心生一計,將搭膊解下連衣包拴在腰裏,向那松樹旁一根小樹跨上去,一手攬著松枝,將身就勢越過那樹,又盤上幾層,揀個大大的丫杈中,似鳥鵲般做一堆兒蹭坐著。
方才安身得牢,忽聽得下面聲響。蛋子和尚眼快,在星光下仔細一看,只見那頭陀提著齊眉短棍在樹林左右行來步去,東張西望,口裏哼道:「死禿驢真個那裏去了。」穿過林子又去一段路才轉來,倒拖著棍棒,向舊路徐徐而去。
蛋子和尚看了叫聲慚愧,且喜不遭他毒手。只是一件:那頭陀獨自一個坐在人家門首,好不冷淡,得個人作伴也好,為何抵死不容。比及讓了他罷了,又來東尋西覓,只恐還在左近,放心不下。其中必有緣故。終不然要做打家劫舍的勾當,怕我礙眼。這個荒村草舍將有甚大財鄉,動了他火,好生難解。且莫管他,自己安息一時再處。方欲閉眼,不覺肚中餓得疼痛,腸鳴起來。蛋子和尚道:「這一夜好難過,就熬過今夜來朝怎得氣力跳下樹去?便跳下時跑走不動,倘遇了那賊頭陀,乾折個性命與他。聞得仙人餐松茹柏,我且學他一學。把松枝上嫩毛摘來試嘗,雖不可口,卻也清香。吃了些兒,引得性起,不論老的嫩的滿把的放在口中去,只管亂嚼嚥下了許多,也覺得腹中充實了些。
忽然一陣風,遠遠的聞得號呼哭泣之聲。蛋子和尚道:「奇怪,這裏又不是鬧熱村坊,此聲從何而來?」側耳再聽時,其聲哀急,又像婦女聲音,分明在前面茅屋那一搭兒。蛋子和尚猛省道:「是了,一定是那賊頭陀幹了不公不法的事出來。」欲待不理,心頭氣忿忿的怎忍得住!我且悄悄地去探個下落,也得放懷。當時解下腰間衣包,縛在樹上,重把搭膊拴緊了腰,分開松枝,望下踴身一跳。兩腳點地,毫無傷損。將身抖一抖,走出林子,照前路一步一步的捱去。
約莫茅屋相近,悄悄地舒頭去望那茅簷下,略無動靜。再走幾步,向前看時,已不見了頭陀。走上簷頭左右細看,端的不見了。側耳聽時,裏面哭聲也住了。蛋子和尚心下疑惑,輕輕的推那門兒,原來是兩扇舊白板門。這石頭陀在裏面用棍撐著,撐得不牢,初時推不開,以後用力一??雙,撲的一聲棍兒倒地,左一扇門兒早開。這茅房原來是小小三間開闊,兩進一披頭。一進兩邊安放些做屋的土磚木料,更有幾處粗重家伙,中間空個走路。第二進做個內室,左首披屋裏面安排鍋灶。石頭陀脫得上身赤膊,正在灶下燒火煮飯吃,聽得開門響,慌忙起身來看。
說時遲,那時快,蛋子和尚一腳踹進門來,正踹著棍兒,便曲腰下去綽棍在手。知道裏面有人出來,急向木料堆裏一閃,閃過。石頭陀黑暗裏急切不辨,見大門開著,便鑽出外去探望。蛋子和尚乘著披屋下有些燈光透出,到對著裏面天井一溜進去。這邊進去的還不曉得裏面詳細。那裏面暗處,有個老婆婆先已瞧見和尚,叫聲:「啊呀!又是一位羅漢來到,死也,死也!」蛋子和尚聽得聲音,情知有些蹊蹺,卻待進步盤問,只聽大門右扇開的一響,是那石頭陀作勢推開。蛋子和尚慌忙退出,仍伏在木料堆邊。只見那石頭陀踏進門內時,覆身向外,發狠的鬼叫道:「有誰大膽的,敢進來麼?」喊了一聲便坐身下去摸那地下的棍兒,誰知這棍落在蛋子和尚之手。和尚有了器械,早壯了三分膽氣,那時看得仔細,就他蹲下去時,做個水面撈衣勢,將棍可對著他屁股竭力向上一挑。那頭陀出其不意,精頭皮倒垂磕下,橫身臥地。蛋子和尚怕不了事,舉棍又打下去。那邊把右手來擋,正迎著棍兒去得重,只一聲響,打折了兩個指頭,連皮兒掛著。石頭陀負痛便叫:「好漢饒命!」蛋子和尚已知得了便宜,左手持棍,右手?開五指,一把抓去,連腰胯連肚皮做一堆兒提起,到天井裏面高高的向下一擲,那頭陀殺豬也似叫喊。蛋子和尚向前一步,將右腳劈胸踹定,捻起升籮般大的拳頭在他臉上晃一晃,喝道:「賊頭陀,你要死要活?」那頭陀方才認得就是落水的和尚,只叫:「師兄,是俺得罪了,饒命罷。」蛋子和尚罵道:「賊頭陀,我只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少林寺出尖的打手,原來恁般沒用的蠢東西。叫甚麼石羅漢,你便是鐵羅漢,我也會銷鎔你起來。迎暉寺前偌大一塊大搗衣石,我也只一拳打個粉碎。先前我再三讓你,是我出家人本等。你又到林子裏面來尋趁我,你實說在此做甚勾當,惹得他家啼啼哭哭。快快說來還有個商量,若半句含糊,我也不用棍打,只教把你做個搗衣石兒,試我拳頭一試。」
說罷,便把棍兒撇下,右手捻起拳頭待打。那頭陀心慌,又被蹬緊了胸脯好不自在,儘力叫道:「佛爺爺佛祖師,放俺起來,待俺細說。」蛋子和尚道:「賊頭陀,便放你起來,料你也不敢走。」卻待鬆腳放他,只聽得屋裏黑暗中有人叫道:「師父與我家伸冤則個!莫放鬆他。」蛋子和尚認得就是先前一般的聲音,定了腳看時,只見個白髮老婆婆,腰馱背曲,半蹲半走的摸將出來。到天井中,朝著蛋子和尚,連連的磕頭,只叫伸冤。蛋子和尚道:「老人家不要多禮,你有甚冤情,快說來,我與你做主。」老婆婆道:「這天殺的,壞了我家媳婦母子兩口的性命。」只這一句引得蛋子和尚心頭火起,將腳跟向那頭陀的心坎裏狠力的蹬上一下,那頭陀大叫一聲,口中鮮血直噴出來。有詩為證:
僧家淨業樂非常,何事芒鞋走十方。
做賊行淫遭惡報,分明好肉自剜瘡。
蛋子和尚方纔收起了腳,扯起老婆婆,問其緣由。老婆婆啼哭起來,指著披屋裏面,說道:「師父去看便知。」蛋子和尚還怕那頭陀奸詐,再要加他上幾拳,只見他直挺挺的不動,踢他一腳也不做聲了,方才放心。走到披屋裏去,把壁上的掛燈兒剔明,那鍋中兀自熱騰騰的氣出,揭開鍋蓋看時,噴香的一鍋熱飯,是那頭陀才煮下的。蛋子和尚正在要緊之中,便道:「我且吃他兩碗,卻又理會。」向灶前揀起一把茅柴點著,去找個碗兒來用,剛剛的在破廚櫃內取得一隻磁碗、一雙柳木筋兒,猛看見牆角頭又是一個人睡著,倒吃了一嚇。仔細打一照,原來是個婦人剝得赤條條的,死在血泊裏面。卻好老婆婆帶著哭也摸進來了。蛋子和尚問道:「這婦人是你甚麼人?為何而死?」老婆婆道:「一言難盡。」拖著凳子頭兒教師父請坐,「等老身慢慢的告訴。」蛋子和尚道:「你莫管我,儘你說,我都聽得。」便盛著飯一頭吃,一頭聽那老婆婆的說話。
老婆婆坐在門檻上,從頭至尾告訴道:「老身家姓邢,這死的是老身的媳婦。我的兒子叫做邢孝,在這羅家畈種田為生,因本縣縣令老爺貪財,責取里正要百來擔好丹砂。這丹砂雖說出在辰州,卻不是黔陽縣土產,卻在沅州老鴉井內,這井好不寬大,四圍生成的青石壁,須要積下乾柴放起火來,燒得那石壁迸開,方才有砂現出。這裏羅家畈莊戶種田空閒時,都慣做這行生意。里正科斂百姓的銀子,顧人去到那邊納了地頭錢,取丹砂奉承縣令。這畈裏幾家莊戶都接受得工錢,但是有老婆的都寄在親眷人家去了。只我家媳婦有了五個月身孕,出門不得,又是老身七十多歲兩口兒做伴,在這房子內看守。一月前邢孝還在家的時節,媳婦患個肚痛的症,急切沒個醫人。剛遇這頭陀上門化齋,兒子回他道:「現有病人在家,沒心緒齋得你。」他問是甚麼病,兒子不合回他說道:「媳婦有五個月身孕了,現今患肚痛,只怕小產。」那頭陀道:「我叫做石頭陀,石羅漢。不但會看經,也曉得些醫理。有個草頭方兒,依我吃了肚痛便止。又能安胎。」兒子也是沒奈何,只得憑他解開包裹,把幾味草頭藥煮來灌下,果然肚痛止了。當日請他一頓飽齋,又不要錢,竟自去了。只道他是好人。昨日又到這裏化齋,媳婦回他道:「男子漢不在家,改日來罷。」他不肯去,就把言語調戲我媳婦起來。媳婦閉了門進來了,不理他。他坐在門首唸經,只是不去。到深夜時分,老身睡了,媳婦還在中間績麻,那頭陀曉得家裏沒人,悄悄地把門弄開,竟走了進來。將媳婦抱住,恐嚇他道若聲喚就殺了你。當下被他強姦了,這還是小事。又教媳婦去燒下一鍋滾湯,我要洗個澡。媳婦只得與他燒水,又教傾一半在桶裏,那天殺的原來不要洗澡,把包裹打開取一丸白藥教媳婦吃了,後來易產。吃下便覺有些肚痛。他又解出兩隻新草鞋來浸在鍋內,對媳婦說道:「我要與你借件東西,合個長生不死之藥。藥成時送些與你吃了,大家升仙。」媳婦道:「借甚麼東西?」他道:「要你五個月的血胎。」媳婦慌急了,哭拜告饒。那天殺的雙手抱定,剝個寸絲不掛,將他綁住手腳,按在桶上,把熱湯揉他的肚皮,媳婦痛極了,再三哀告,只是不允。又將鍋內兩隻熱草鞋輪番在肚皮上揉擦,可憐血胎墜下,我媳婦當時血崩而死。老身嚇壞了伏在後面,不敢則聲。只聽那天殺的說道:「到是個男胎。」他又在布袋內取米造飯,只待吃了便走。不期遇著師父到來,奈何了他,正是天理昭彰,惡人自有惡人收。」
蛋子和尚問道:「他取下血胎在那裏?」老婆婆道:「想收拾在包裹裏面了。」因這老婆婆話長,蛋子和尚也不知吃了幾碗飯,把鍋內吃個罄盡,只剩個鍋底。和尚放下碗筷,向廚櫃上層尋著他的包裹,就在鍋蓋上打開看時,裏面又有小布包兒,解開來是一條布裙子,正裹著血團團的小廝和那胎衣在內。又是一包十多兩散碎銀子。又有一疋細白布包著一件裂火袈裟,也有件直裰子,及零星衣服。另有個布囊盛下二三升雜米。蛋子和尚觀看血胎,心下想道:「不知他那長生不死的方兒是真是假,配甚藥物,怎麼取用。可惜造下這罪孽,棄之無用了。」念聲阿彌陀佛,將血胎連布裙子遞與老婆婆。老婆婆看見了,重新哭起肉來。蛋子和尚開了銀包,揀幾塊大的,約莫倒有五六兩,把與老婆婆道:「這銀子你將去,斷送了媳婦。」其餘自家收拾起了。
此時天已漸明,走出天井,看那頭陀面皮發黃,已自沒氣。腳下穿的到好一雙青布僧鞋,蛋子和尚剝來穿下。將這根齊眉鐵包頭的棍兒挑了包裹,叫聲:「老人家,那賊頭陀已死了,太平無事,我去了也。」老婆婆道:「師父你去不得。」蛋子和尚真個住了腳,問道:「為何去不得?」老婆婆道:「你雖然替我除了這害,撇下了兩個死屍,教我如何擺布?」蛋子和尚道:「也說得是。我且把賊頭陀的屍首拋在荒郊,再作計較。」放下棍棒包裹,一手抓著那死頭陀的腰褲,恰似小雞兒一般提起屍首,出了門,直到林子裏面去。此時天已大明,認得夜來這株大松樹,正待撇下屍首,踛上去取那衣包。只聽得遠遠的有人喝道:「清平世界,那裏和尚殺了人,撇在這個地方。」蛋子和尚定睛看時,林子後面有七八個莊家,一個個背著包裹、跨口腰刀、提口朴刀,飛也似奔將來。蛋子和尚不慌不忙撇屍在地,早踛上樹去了,取得衣包在手。眾莊家把這株大松樹團團圍定,蛋子和尚在樹上叫道:「貧僧不是殺人的,是殺那殺人賊的。列位閃開,待貧僧下來相見。」說罷,便撲地一跳,跳出眾人圈外。眾莊家又把和尚圍住,盤詰來由。蛋子和尚道:「列位且說從那裏來?」眾莊家道:「我們奉縣令老爺差委,往沅州採取丹砂。昨晚到縣和里正交納,今早起個五更走到這裏。」蛋子和尚道:「列位中可有邢孝麼?貧僧要報個信兒與他。」眾人裏面走出個矮黑漢子,上前道:「在下便是邢孝。」蛋子和尚指著這死屍道:「這個賊頭陀便是你七世的對頭。」邢孝聽罷這句話,好似一千個榔槌在他心上亂敲,面色都變了,一把扯住和尚道:「對我說個明白。」蛋子和尚道:「如今我說了,你也不信。貴居去此不遠,列位休散了,大家去做個證見。」眾人道:「邢大哥莫慌。既然同到宅上,自然有個分曉。」當時眾人隨著和尚一路走,雖然腳尖兒同向前,腳跟兒同向後,卻有三種情況不同。蛋子和尚的心下欣欣喜喜,好像撐船的逆風收港,有個結束了;眾莊家心下疑疑惑惑,好像看把戲的,不知搬出甚故事來;只邢孝的心下驚驚恐恐,好像解察院的訪犯一般,有罰無賞。正是背人偷酒吃,冷暖自家知。
卻說老婆婆見和尚去了,心中害怕起來。勉強去舖上拽一條被單,將婦人的屍首就地蓋了。摸到門前,兩頭看著,又不知那一條是來路,東一張西一望,只等和尚到來區畫這事,夢裏也想不到兒子回來。這裏老眼模糊還未分明,邢孝先走一步,早已看見,叫道:「老娘,你緣何獨自一個在門外看誰?媳婦在那裏,不陪伴你?」老婆婆一見兒子,便扯住放聲大哭道:「我兒你早歸一日,也不見得好端端的媳婦被甚麼石頭陀石羅漢弄死了。」邢孝道:「怎麼說?」老婆婆哭道:「他死得好苦!」邢孝搶進門來看時,眾人隨後都到了,一擁上前,到把那老婆婆擠在後面。只見邢孝連被單抱起媳婦,放在後屋中間,對著搥胸大哭。眾莊家人人悽慘,問蛋子和尚道:「這事怎的樣?」蛋子和尚道:「等邢大哥哭過了,再問老娘便知。」邢孝道:「我娘年老之人,須是長老與我剖個明白。」蛋子和尚便把自家落水借宿直到打死了頭陀,後面你家老娘與我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備細述了一遍。邢孝止不住腮邊落淚。眾人無不咬牙切齒。老婆婆埋怨兒子道:「都是你聽信了那天殺的鬼話,吃什麼草頭方安胎藥,引得那賊頭陀上門上戶,弄出這事來。如今一命便是兩命,卻不是你自家害了妻兒一般?」眾莊家勸道:「老娘如今說也是無益了。且喜得遇著這位長老,報了冤仇,死者也得瞑目。只是如今林子裏躺著一個,家裏躺著一個,不是個道理,也該作速計較。家裏有米麼,可煮些飯來吃了,相煩長老同到縣令相公處首明。等他差官相驗,順便就帶口棺木下來盛殮,省得過些時被做公的看見林子內屍首,又造謠生事,在地方上做一場生意。」蛋子和尚道:「聞得縣令是個贓官,告許他怎的,要埋時,自家埋下便罷了。」邢孝道:「卻使不得。」
當下敲火煮飯,眾人各剝得有些乾菜,都將出來,等飯熟大家吃飽。老婆婆把銀子遞與邢孝,說其緣由,邢孝又向和尚叩謝。眾人道:「也要老娘去走一遭。」邢孝安排個羊頭小車,教老娘坐上,鎖了門,央一個相厚的莊戶同推著車兒。蛋子和尚提了棍,把兩個包裹打併做一個背著,眾人一擁到黔陽縣來,等不多時候,縣令正升晚堂,眾人將血胎一包當堂呈上,首告地方人命事。縣令把一干人逐一審過,錄了口詞,當交縣尉一員下鄉相驗。到次日晚堂回話無異,官批:
石頭陀係無籍遊僧,所犯雖重,已死不究其屍。責令地方埋訖。沈氏著邢孝自行殯葬,蛋子和尚因義忿殺傷免罪。餘人都發回家去。單留蛋子和尚在縣有話吩咐。
退堂之後,縣令喚和尚到了後堂書房中,屏去左右,誇獎了他幾句,次說道:「我有封緊要書信禮物,要寄到慶元府親戚那邊,路程遙遠,沒個可託之人。適才聞得你恁般義氣,又且英雄了得,肯與我幹這件功勞,回來之日重重酬謝。」蛋子和尚道:「貧僧遊方之人,那一處不去,既然相公尊委不敢有負。」縣令大喜,喚心腹吳孔目送長老到城隍廟居住,庫上支兩貫足錢發與道士,著他供給等候修書完日,標撥起身。不題縣令進衙收拾金珠銀兩,打?箱籠之事。
卻說蛋子和尚和吳孔目到城隍廟中,先有官身報知道士,迎進客堂坐下。蛋子和尚看見廟宇傾頹,房屋敝壞,道士也衣衫襤褸,因問道:「這神廟香火可盛麼?」道士道:「神道極靈,香火也不絕的。」蛋子和尚默然無語。茶罷,吳孔目將兩貫錢交付與道士,便起身吩咐好生管待。道士就把三百文錢送與吳孔目,折個東道,送他出門去了。道士問了蛋子和尚吃葷用酒,忙忙的吩咐廟祝買東買西,安排停當,擺設在臥房裏面,請他來坐。又把自己鋪蓋搬了出來,讓這房與和尚安歇。蛋子和尚飲酒中間,問起道:「既然神道又靈,香火又盛,為甚廟宇恁般狼狽?」道士嘆口氣道:「雖然如此,在小道卻有損無益。」蛋子和尚低聲問道:「莫非縣令難為你們?」道士紅了臉,不敢答應。蛋子和尚又道:「貧僧與這縣令素不相識,只今日要貧僧到慶元府走一番相留在此,貧僧一時應承了,不知是甚麼書信。聞得縣令是個貪官,刻剝百姓,足下必知其詳,你休疑慮著我,但說不妨。我們出家人,難道到與贓狗做一路不成?」道士見他言語出得至誠,便把兩指做個錢圈兒,說道:「縣令老爺愛的是那個東西。莫說別件,只這城隍廟裏,不論月大月小,要納還他香火錢十貫。不足數時,小道還要賠補,若布施得些米料在這裏,縣中便來取用去了。所以門內廊廡都無力修整。他戴了?頭,神道也是勢利他的。雖說威靈顯赫,只在小百姓上做工夫,撞著做官的全無報應。」蛋子和尚道:「他是那裏人氏,有甚親戚在慶元府,便一封書信打甚麼緊,何必用著貧僧。」道士道:「他正是慶元府慈谿人氏,姓侯雙名明宰,在此做過四年官了。每年積下若干贓物運至家中。恐有?虞,定要個有本事的護送將去。去年用人不當,到洞庭湖中被劫去了,聞得今番要走旱路,他留著禪師一定為此。他原是窮儒出身,只這任官,家中解庫也開過好幾個了,貪心兀自不止,禪師你道狠也不狠。」蛋子和尚道:「原來恁地。」道士道:「適才禪師盤問,小道多口了,路途中在他們管家或公差面前,是必休題。」蛋子和尚道:「不消吩咐。」當晚酒飯已罷,道士別去了。蛋子和尚在房中思想道:「這些詐人的錢財,到叫我替他送了去。這事不成,不成。」睡到五更,只推解手,取了包裹棍棒出了廟門,一溜煙走了。明日道士不見了和尚,慌了手腳,稟知縣令。縣令道:「早是不曾託他幹事,這遊方和尚全無信行。」也不責備道士,只追他這兩貫錢完庫,道士只得又去生錢借債,補完這項,倒折了三百文錢,一頓酒飯。後來侯縣令多用賄賂,得陞京職,自家建個生祠在縣中,去任後被眾百姓夜半時抬那祠中的土偶,折了腳,撇在糞坑裏面了。縣令在中途被馬驚墮地,折足而死。可見天道不爽,此是後話。有詩為證:
儘人吃著亦無多,苦苦貪求卻為何。
試看墨吏終當敗,縱免人誅有鬼訶。
卻說蛋子和尚那日出了黔陽縣,離了辰州,又往湖北荊南一路遊去。逢山看山,逢水看水,留連光景,不覺又過了一年。看看李白桃紅,又早梅黃杏紫,蛋子和尚切記著本等前程,預先買就一百張潔淨純綿大紙,帶歸雲夢山下草棚中來。將紙預先編個一二三四的號數,把石頭陀這疋細白布縫個袱包兒包著,又去清水潭中洗個淨浴。
到端午日,早起在地灶中煨飯吃飽,正待扎縛停當,只見雲暗山頭,下著一陣大雨。蛋子和尚道:「卻不是晦氣!這雨日日不下,偏是今日與我送行起來。」只得在松棚內望空磕頭禱告道:「某今日有緣得見天書之面,望乞斂雲收雨,速現紅輪。」看看捱到巳牌時分,雨已停止。和尚喜不自勝,取了綿紙,提了齊眉棍棒便走。此是第三遍了,路徑已熟。只山地濕,高下崎嶇,況且冒霧而行,只恐遲誤。忙忙的向前,比及霧氣將散,石橋也到了。蛋子和尚舉目看時,吃了一驚。原來這橋是天生成一條青石,經雨後,其滑如油。隨你節節小心,如何把得腳住。有人問道:「那三百六十日的濃霧,難道石橋沒些濕氣,直等這番大雨?」看官有所不知。但是尋常的霧,都是地氣上升,天氣不應,其氣氤氳迷亂而成,所以沾衣而濕,觸石則潤,久而不解。這白雲洞的霧,是霧幕中噴出來的,只是乾霧。分明是蜃樓海市,望之有形,就之無?。所以前兩遍石橋全無濕氣,今番雨後難行也。若是三尺四尺,不多步兒也還好處,這三丈多長哩!下面不測深淵,可是取笑得的。正是:
除非插翅飛將去,動腳之時必墮傾。
是這般說時,第三番又去空了。卻不道風急雨至,人急智生。畢竟用著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