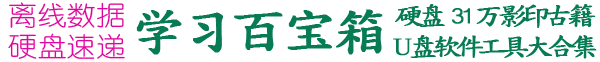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通州之缘
通州现名通县,大约是因后来行政区划只有市、县,而将州、府废掉。但老习惯还喜欢称州 ,比如赵州早亦改名“赵县”,可是没一个人说什么“赵县石桥”,只说“赵州石桥鲁班修 ”。再者,“州”字也难尽付禁条,“杭州”、“苏州”、“泉州”、“广州”……叫得蛮 响。此岂字的幸运乎?亦历史的韧性也。我与通州缘分不深。京津往返之路经此地,那不能算数。真“到”那儿,迄今实只两次。
一次是“文革”中一大群“黑分子”到通州永乐店去劳动。
记得好像是秋天,高爽宜人,做的当然都是庄稼活儿。因那是“集训”,每日两次“整队 ”听训。一次“工头”喊了“立正”口令,而总编级的原领导楼公适夷,还“八字步”撇脚 而立,被那头头着实地怒斥了一顿。
说实话“书生故习”极不易改造——就在那日月里我还是忘不了“考证”的功夫。
这回倒与 《红楼》不相干。我是对“永乐店”发生了“兴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在这儿住过一次“小店儿”不成?
我想,这怕是汉字语音在民间的音讹。
记得古代最大的几个沼泽之地,在南如云梦,在北即有雍奴。雍——永之变,不待多讲;“ 奴”是n u音,n与l的互转音讹,例不胜举(如蜀语奶奶说成lai lai,天津话“ 嫩 ”说作len……)。此理即明,则古名“雍奴淀”第二字初变为lu,lu的轻读就是l e(乐)了。故“永乐店”者,古名雍奴淀之遗音也。
这在“劳动改造”中过过“考证”瘾,自然没法找书本写论文。至今是否难以自信自“定” 。
但“淀”之变“店”,自信不错。北方的许多“店”,实皆“淀”也。淀乃浅水,世代一久 ,即为枯涸,淤为平川,民不复知,乃写作“店”耳。如大师顾亭林,作《京东考古录》, 谓昌平之“夏店”,即古之夏谦泽,此说极是。但他竟不悟那个“店”是“淀”的“记音” 。此亦鸿儒硕学的一个小小的遗漏。
在另文中,我叙及1962年通州发掘曹家大坟之事,惜未赶上车,故无“考证”可写,至今抱 憾。如今只好单讲1992——整整三十年后的事了。
1992年的7月31日晚间,忽接市文物局的电话,邀我次日上午到通州张家湾去看一件新发现 的有关曹雪芹的石头,开会鉴定一下,将派车到门同往。我听了心中欣喜,对此佳讯感到兴 奋,期望一个巨大的发现,打破多年来的沉寂局面。
次晨,果然车临舍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与提供的方便。到达后,进一平房大间屋子, 很简朴的,靠山墙一面摆一列桌作主席台,列坐的是区镇领导和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等人。正 中一大排拼桌,两侧列坐到会专家及石头发现者。靠墙坐的还有不少人,包括新闻界记者等 位。抬头看时,山墙上贴有黄纸大字,写着“曹雪芹墓碑鉴定会”的字样。
主持者到会后,先让大家观看这块宝物——名为“墓碑”者。
人们围上来。只见地上横卧一条通常叫做“条石”的粗石头。正面刻的是“曹公讳?nfda2 ?墓”五个字,左下角二字看上去像“王干”,解释者说是“壬午 ”,纪年干支也。那字极板硬僵死,活像火柴棍儿摆的。没有笔路锋芒转折,一般粗细。
看了实物,归座讨论。
我记得,我左侧是于杰,对面为赵迅,略偏对的是秦公。秦公旁是位赵先生,已忘其名(其 实以上所纪姓名也是会后询问明确的)。最远角上是发现人李氏兄弟。
发现者做了长篇大论的报告——发现详情细节,还有打印的书面。还有分发的地图,两份“ 证明书”。
发言开始了。
第一炮是秦公。我与他只见过一面,并不熟识。他说:这件东西很可疑,理由有三:一是品 质不合,这不是刻墓碑的石头;二是型制不合,墓碑无此种形状。从物体本身来考察,只 是 京郊民居常见的做盖房的墙基石或台阶石。再从石刻看,字的“笔画”槽内明显看出是胡乱 凿成的,像“?nfdb6? (cuò) 磨”(盘石)那样“?nfdb6?”的字,根本 不是刻碑的技术者所为。
秦公先生也指出了这石面也并无二百多年埋于土中的痕迹,是一件新物(对此,发现人解释 说他曾将石面“磨过一次”)。秦先生讲后,发言的是我。我说,我们应当重视石刻专家的 意见,深入探究,以定真伪;此外也要审断所刻文字的款式合不合乾隆时代的习俗规格。
秦先生身旁的赵先生,听我此言后便接着发言,他说:文字款式不合,从未有如此书碑之 例。比如墓碑一概是某某人“之墓”,无省“之”字的(那实际欠通)。再如左侧一行书写年 月,一律是顶格大书“皇清乾隆××年(或加岁次甲子、乙丑……干支)”,这是定例,哪会 只写干支“壬午”二字而且写在最低的下角处?这根本不可能。
会场一阵寂然。主席台上似乎感到情况出乎意外,言词有些不像开场那么兴致勃勃了。会上 没有出现反驳秦、赵两位意见的发言。
我注意到两份“证明”文件中,一份是退休的本镇的老支书,他主要表示:一,我不知“曹 园”这个地名;二,我当时不在那块地上,未见那块石头;三,我也不知道石头上写的什么 字。
这令我十分诧异:这哪儿是“证明”?老支书是位老实同志,不肯说假话——这其实是“反 证明”。
发现者还讲了很多“细节”,例如说那碑初现时是在土中“斜着的”,既非平卧,也非直立 。 他用心良苦,是想表明石本正立,年久倾斜了。但这儿破绽分明:若系直立,或需有石槽嵌 立,或下端字外有较长的空白石端深插入土,方能直立——而那块条石的“墓”字紧挨石 边,无一寸留埋之空石端,何也?
其实,既曰“墓碑”,是立于墓前,让后人知此为何人之坟茔,从无将碑埋入坟内之事—— 墓内的石刻,那叫“墓志”,字很多,有文有铭,有撰文人,有篆盖人,皆落款……
这个破绽弄得相信者不太好办了,于是不再称“墓碑”了——心裁独出,改称“墓石”了。
“墓石”之名,绝不见于文献典籍,是个杜撰的尴尬之名色。
离张家湾返京之路上,与秦公先生同车,这才“重新认识”。他表示了若干疑点,确言是一 块拙劣的伪造物。并云:“我只能举疑点,供研究;若是明言伪造,害怕有人拿刀子捅我! ”
事后,北京报端颇有文章讨论、争议。秦先生十分重视此事,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未见有 专家能逐一驳难他的论证。
市文物局不表态,内部个别接触,得知局方根本不以为真文物,只因碍着某少数几位专家的 面子,不愿公开表态,但不开会,不通报,不宣传——作为不表之表。
再事后,方有《北京日报》宗春启先生发表了重要文章(载《视角》杂志),引录了知情人的 投函揭露,证明年月、地点、当时“平地”的工作方式、分队分地,一切情况,无一能与“ 发现者”的言词有相符之点,全系捏谎编造。
一场闹剧,到此谢幕——也“谢墓”了。
意外一件事:会议结束招待午饭,从会场走向饭厅的路上,于杰先生与我(陪我的有女儿周 伦苓)说:患眼神经萎缩症,视力坏极了(与我同病相怜之叹)——而然后接云:正白旗的那 块墙皮上的字是我发现的——今知是假的,可是已不好再说明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雪芹的预言,英明极了。
诗曰:
墓碑墓石费称名,一块新镌动北京。
独有秦公存正义??,临风怀旧悼先生。
*秦公先生不久前因病辞世,不胜痛惜之情。
一次是“文革”中一大群“黑分子”到通州永乐店去劳动。
记得好像是秋天,高爽宜人,做的当然都是庄稼活儿。因那是“集训”,每日两次“整队 ”听训。一次“工头”喊了“立正”口令,而总编级的原领导楼公适夷,还“八字步”撇脚 而立,被那头头着实地怒斥了一顿。
说实话“书生故习”极不易改造——就在那日月里我还是忘不了“考证”的功夫。
这回倒与 《红楼》不相干。我是对“永乐店”发生了“兴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在这儿住过一次“小店儿”不成?
我想,这怕是汉字语音在民间的音讹。
记得古代最大的几个沼泽之地,在南如云梦,在北即有雍奴。雍——永之变,不待多讲;“ 奴”是n u音,n与l的互转音讹,例不胜举(如蜀语奶奶说成lai lai,天津话“ 嫩 ”说作len……)。此理即明,则古名“雍奴淀”第二字初变为lu,lu的轻读就是l e(乐)了。故“永乐店”者,古名雍奴淀之遗音也。
这在“劳动改造”中过过“考证”瘾,自然没法找书本写论文。至今是否难以自信自“定” 。
但“淀”之变“店”,自信不错。北方的许多“店”,实皆“淀”也。淀乃浅水,世代一久 ,即为枯涸,淤为平川,民不复知,乃写作“店”耳。如大师顾亭林,作《京东考古录》, 谓昌平之“夏店”,即古之夏谦泽,此说极是。但他竟不悟那个“店”是“淀”的“记音” 。此亦鸿儒硕学的一个小小的遗漏。
在另文中,我叙及1962年通州发掘曹家大坟之事,惜未赶上车,故无“考证”可写,至今抱 憾。如今只好单讲1992——整整三十年后的事了。
1992年的7月31日晚间,忽接市文物局的电话,邀我次日上午到通州张家湾去看一件新发现 的有关曹雪芹的石头,开会鉴定一下,将派车到门同往。我听了心中欣喜,对此佳讯感到兴 奋,期望一个巨大的发现,打破多年来的沉寂局面。
次晨,果然车临舍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与提供的方便。到达后,进一平房大间屋子, 很简朴的,靠山墙一面摆一列桌作主席台,列坐的是区镇领导和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等人。正 中一大排拼桌,两侧列坐到会专家及石头发现者。靠墙坐的还有不少人,包括新闻界记者等 位。抬头看时,山墙上贴有黄纸大字,写着“曹雪芹墓碑鉴定会”的字样。
主持者到会后,先让大家观看这块宝物——名为“墓碑”者。
人们围上来。只见地上横卧一条通常叫做“条石”的粗石头。正面刻的是“曹公讳?nfda2 ?墓”五个字,左下角二字看上去像“王干”,解释者说是“壬午 ”,纪年干支也。那字极板硬僵死,活像火柴棍儿摆的。没有笔路锋芒转折,一般粗细。
看了实物,归座讨论。
我记得,我左侧是于杰,对面为赵迅,略偏对的是秦公。秦公旁是位赵先生,已忘其名(其 实以上所纪姓名也是会后询问明确的)。最远角上是发现人李氏兄弟。
发现者做了长篇大论的报告——发现详情细节,还有打印的书面。还有分发的地图,两份“ 证明书”。
发言开始了。
第一炮是秦公。我与他只见过一面,并不熟识。他说:这件东西很可疑,理由有三:一是品 质不合,这不是刻墓碑的石头;二是型制不合,墓碑无此种形状。从物体本身来考察,只 是 京郊民居常见的做盖房的墙基石或台阶石。再从石刻看,字的“笔画”槽内明显看出是胡乱 凿成的,像“?nfdb6? (cuò) 磨”(盘石)那样“?nfdb6?”的字,根本 不是刻碑的技术者所为。
秦公先生也指出了这石面也并无二百多年埋于土中的痕迹,是一件新物(对此,发现人解释 说他曾将石面“磨过一次”)。秦先生讲后,发言的是我。我说,我们应当重视石刻专家的 意见,深入探究,以定真伪;此外也要审断所刻文字的款式合不合乾隆时代的习俗规格。
秦先生身旁的赵先生,听我此言后便接着发言,他说:文字款式不合,从未有如此书碑之 例。比如墓碑一概是某某人“之墓”,无省“之”字的(那实际欠通)。再如左侧一行书写年 月,一律是顶格大书“皇清乾隆××年(或加岁次甲子、乙丑……干支)”,这是定例,哪会 只写干支“壬午”二字而且写在最低的下角处?这根本不可能。
会场一阵寂然。主席台上似乎感到情况出乎意外,言词有些不像开场那么兴致勃勃了。会上 没有出现反驳秦、赵两位意见的发言。
我注意到两份“证明”文件中,一份是退休的本镇的老支书,他主要表示:一,我不知“曹 园”这个地名;二,我当时不在那块地上,未见那块石头;三,我也不知道石头上写的什么 字。
这令我十分诧异:这哪儿是“证明”?老支书是位老实同志,不肯说假话——这其实是“反 证明”。
发现者还讲了很多“细节”,例如说那碑初现时是在土中“斜着的”,既非平卧,也非直立 。 他用心良苦,是想表明石本正立,年久倾斜了。但这儿破绽分明:若系直立,或需有石槽嵌 立,或下端字外有较长的空白石端深插入土,方能直立——而那块条石的“墓”字紧挨石 边,无一寸留埋之空石端,何也?
其实,既曰“墓碑”,是立于墓前,让后人知此为何人之坟茔,从无将碑埋入坟内之事—— 墓内的石刻,那叫“墓志”,字很多,有文有铭,有撰文人,有篆盖人,皆落款……
这个破绽弄得相信者不太好办了,于是不再称“墓碑”了——心裁独出,改称“墓石”了。
“墓石”之名,绝不见于文献典籍,是个杜撰的尴尬之名色。
离张家湾返京之路上,与秦公先生同车,这才“重新认识”。他表示了若干疑点,确言是一 块拙劣的伪造物。并云:“我只能举疑点,供研究;若是明言伪造,害怕有人拿刀子捅我! ”
事后,北京报端颇有文章讨论、争议。秦先生十分重视此事,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未见有 专家能逐一驳难他的论证。
市文物局不表态,内部个别接触,得知局方根本不以为真文物,只因碍着某少数几位专家的 面子,不愿公开表态,但不开会,不通报,不宣传——作为不表之表。
再事后,方有《北京日报》宗春启先生发表了重要文章(载《视角》杂志),引录了知情人的 投函揭露,证明年月、地点、当时“平地”的工作方式、分队分地,一切情况,无一能与“ 发现者”的言词有相符之点,全系捏谎编造。
一场闹剧,到此谢幕——也“谢墓”了。
意外一件事:会议结束招待午饭,从会场走向饭厅的路上,于杰先生与我(陪我的有女儿周 伦苓)说:患眼神经萎缩症,视力坏极了(与我同病相怜之叹)——而然后接云:正白旗的那 块墙皮上的字是我发现的——今知是假的,可是已不好再说明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雪芹的预言,英明极了。
诗曰:
墓碑墓石费称名,一块新镌动北京。
独有秦公存正义??,临风怀旧悼先生。
*秦公先生不久前因病辞世,不胜痛惜之情。